150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整理 | 實習記者 李雨桐
一邊喝酒,一邊聽一流大學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學者談他們在做的研究——上海正在流行一種很新的酒吧。
作為一種社交方式,SciBar(學術酒吧)在海外其實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了,我在曼切斯特大學官網的「社會責任」頁面上看到,英國科學協會(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在英國多座城市舉辦學術酒吧活動。所謂的學術酒吧,指的是在酒吧裏組織的非正式學術討論,活動的具體形式是,由一位科學家展示TA的研究並組織討論。這些學術酒吧在英國很受歡迎,每次活動吸引的觀眾30-90人不等,他們對科學感興趣但不一定有相關學術背景。
上海是一座對最新文化潮流吸收很快的城市,學術酒吧在上海出現並不奇怪,然而,「酒吧+學術」這一乍看之下很不搭調的組合招致了一些吐槽和嘲諷。有微博網友吐槽稱,上海某學術酒吧透過問卷篩選觀眾,且入選名額非常有限,讓人不禁感嘆「去酒吧都落選了」。也有人認為,學術酒吧有把「學術當成一種淺顯的符號資本和時尚單品來消費」的嫌疑。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學術酒吧興起於一個學術圈本身正在越來越內卷、人們開始懷疑學歷過剩的時間點:俗稱「青椒」的青年教師遭遇非升即走困境、難以獲得長期教職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與此同時,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也愈發不確定。作為一種城市青年文化現象,學術酒吧折射出年輕人的哪些訴求呢?
01 學術酒吧:非正式學術研討新去處
徐魯青: 我參加的學術酒吧是最近很火的一家,應該也是第一個開展學術酒吧活動的。在做學術酒吧之前,這個酒吧也聚集了很多的左翼青年,他們會討論一些政治和公共性較強的話題,而不只是生活的閑聊。我去那喝酒主要是覺得顧客聊的東西還挺有意思的。店裏餐巾紙上會寫一些破冰聊天的問題,內容類似於普魯斯特問卷,大概有20個問題,類似「你是否支持死刑」。
我是周末去的,嘉賓是飲食人類學家曹雨,他做過很多關於食物和廚房的研究,出版過【中國食辣史】。他討論的題目很有意思,叫「廚房末日啟示錄」:廚房是不是一個可以被替代的空間?是誰要消滅廚房?除了食物,我們還能從烹飪中獲取什麽?當時有很多人去聽,互動也很多,每個人都能講一兩句。嘉賓就在吧台後面借助ppt和大家討論分享,沒有什麽距離感和高高在上的感覺。
我之前還去過位於北京五道口的706青年空間,那是一個很大的房間,主辦方經常邀請旁邊學校的一些學者老師去主持一些講座和沙龍活動,和學術酒吧有點相似。我參加這種活動主要是因為對特定講座話題感興趣。

林子人: 我雖然沒參加過學術酒吧的活動,但仔細想來,是參加過這種性質的非正式學術研討會的。讀碩士期間,我們系經常會舉辦午餐研討會,雖然像我這樣的窮留學生去參加這些研討會的主要動機是去蹭免費午餐吃,但其實很多時候也會聽到一些我覺得很有趣、對我很有啟發的分享。午餐研討會的形式通常是,本校或外校的一位年輕學者來分享他們正在做的研究,他們會先做一個演講,然後在午餐的放松氛圍裏,聽眾會向這位演講者提問。
我覺得這種分享會有一種很強烈的構建學術共同體的氛圍,我們在讀譯介成中文的海外學術著作的時候,不是經常會在正文前看到作者列出非常多的致謝的人名麽,比如說感謝某某某提出的寶貴意見。很有可能這個寶貴意見就是在這樣的非正式場合中激發的。我們知道,做學術是一件非常孤獨的事情,來自同行的提問和建議很多時候能夠緩和這種孤獨感,並且化為養分幫助你精進自己的研究。
尹清露: 我比較同意子人說的這類非正式學術研討有很強烈的構建學術共同體的氛圍。我讀研是在疫情期間,周圍沒有什麽人,平時也去不了學校,找同類的期望會比較強烈一些。當時我跟幾個朋友一起組織線上讀書會,讀一些平時自己啃不下去的很難讀的文獻。我和幾個來自法學專業還有其他人文社科專業的同學一起讀福柯那本特別晦澀的【詞與物】,讀書會流程其實跟上課做Pre很像,每個人分配到一章,這章是你來講,下一章我來講。但因為它沒有任何的外部約束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當時還認識了在美國讀人類學的關系很好的朋友,也一起約好每周固定讀一篇文獻,但最後也沒有堅持下去。
不過,我覺得這種非正式學術探討提供的是一種情緒價值,讓我感受到了大家的情誼。而且這種情誼是建立在所謂智識交流、觀點分享基礎之上的,有一種誌同道合的感覺。不過我也隱隱感覺到,這種形式背後好像也有一種優越感在裏面。
董子琪: 我也覺得非正式學術對話非常重要。一位名為皮埃爾·阿多的法國哲學家將非正式學術對話溯源到古希臘時期,他說現代大學裏面,大家會認為老師對學生的教導根據大綱來進行,個人化的、群體化的關系理應消失。但是古希臘的傳承並不是這樣的,古希臘哲學的對話和交流不是在交流一些觀念的抽象關系,而是人們的生活。
蘇格拉底是哲學家不是因為他能做講座,更多是因為他會和朋友聊天和生活。生活是學術很重要的一個部份,我覺得做講座並沒有多麽厲害,會做研討會讓大家一起討論才是最厲害。
02 學術酒吧中的性別:男性討論,女性傾聽
潘文捷: 【走進酒吧的年輕女性】一書談到,在傳統酒吧中,女性是生產力,男性是消費力。作者把女性分為女客服、氣氛組、免費入場的美女和自己掏錢的女性這四種。其中女客服和氣氛組主要是酒吧自己僱用的,負責陪喝陪玩,賣酒賣小東西。免費入場的美女其實並不「免費」,她們是用自己的存在付錢的。酒吧的銷售會引導免費入場的美女和男生拼桌,把她們變成一種籠絡男顧客的手段。還有一種是願意自己買單的女性,她們要為溢價很高的酒水花錢。
酒吧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性別化場所,男性要透過穿著很貴的衣服,帶很貴的表,開很貴的車來展現自己的經濟資源,女性則是展現自己的身體資源,男性和女性互為景觀。依靠這種高度的性別化,酒吧得以透過高溢價的酒水牟取高額利潤。在傳統酒吧的場域下,女性要麽是迎合父權成為生產力,要麽是迎合資本成為消費力。一方面她們好像是在為自己的快樂買單,但另一方面可能會因為商家的行為,或者是一些無意識行為讓自己處於被凝視和被評價的位置。

黃燕華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4-2
我大概十多年前過706空間,那裏經常討論的一套自由主義話語是男本位的話語,自由、民主的啟蒙都是在女性解放之前。雖然大家在那個空間裏對很多社會議題大談特談,但對女性的關註其實遠遠不夠。而且後來爆出了很多有關706空間性騷擾的事情,很多之前活躍於706的男性公知也深陷其中。我覺得對於那個時代在這種青年空間的女性來說,她們還是沒有真正擺脫第二性的位置。
尹清露: 文捷說的性別視角讓我想到疫情時很火的Clubhouse,這是一個線上語音交流APP,有很多不同主題的房間,也有許多學術主題的房間,每個「房間」有一名主持人負責組織聽眾輪流發言。當時有很多留著長發的歐陸哲學男發言時間很長,不停地高談闊論但言之無物。
03 當學術酒吧開始篩人: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歧是必然嗎?
林子人: 我註意到,在關於學術酒吧的討論裏,有一點是讓很多網友感到冒犯的,就是事先用調查問卷來篩選觀眾。這裏出現的某種消費者和商家的權力倒轉——不是由消費者來挑選商家,而是由商家來挑選消費者——讓一些人感到不適。這可能也是學術酒吧最有爭議性的一點,即在一個消費場景下,用智識水平來篩選觀眾和饑餓行銷有什麽區別?
另外,篩選行為暗示了參加學術酒吧是有智識門檻的,這也很容易引發長遠以來主流大眾對知識分子以及由知識分子主導的活動的偏見,就是他們用知識當作拔高自己、貶低他人的工具,更何況在很多情況下,知識分子不過是更擅長運用學術黑話來講一些不接地氣的東西。
董子琪: 酒吧是處於街頭的,每個人都能進去,但學術又有相當的精英性,所以學術酒吧是介於街頭和精英之間的一種產物。歷史學家王笛在【街頭文化】中綜述了前人學者的一些觀點,就是在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之路的過程中,要註意到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歧,研究公共活動時應該註意儒家傳統的精英文化與大多數宗教以敬鬼神、安撫靈魂為中心的大眾文化是分離的,精英文學和大眾說唱評書也是分離的。原來勾欄瓦社裏面流行的說唱表現形式才是街頭文化的主流,大家看著主要為了圖個樂,和現在酒吧裏面高談闊論人類學、民族誌、文化應該有比較大的不同。長期以來街頭文化的主體,庶民文化是統治者眼中的「危險階級」。他們在街頭尋求生計和娛樂,可能是無產者或者是沒有那麽多「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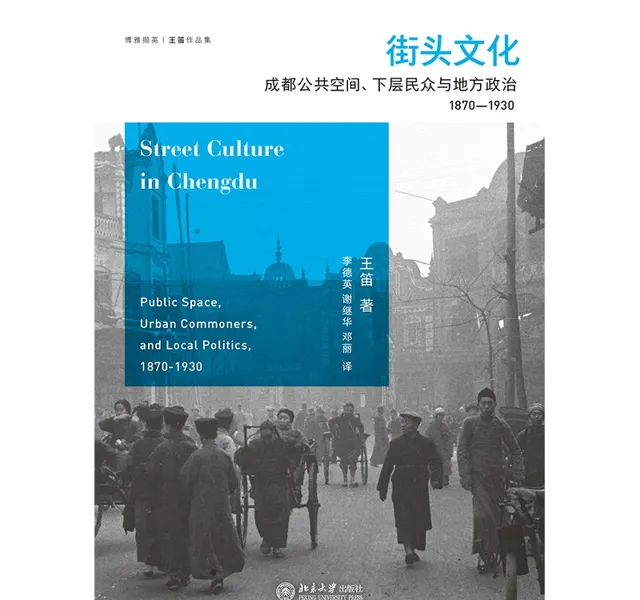
王笛 著 李德英 謝繼華 鄧麗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3-6
近代以來很多精英不再能透過科舉進入國家體制,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轉向大眾傳播。比如李伯元創辦【遊戲報】的宗旨就是「娛人娛己」,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非常低,不求仕途通達,只是為了先「娛樂自己,再娛樂別人」,其中有一個文人身份的轉化。
在學術酒吧發表演說,也可能會有身份的轉化。一方面,他可能是想要作為一個主持去招待、娛樂大家,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想作為一個學者去啟蒙民眾。在酒吧發表演講的,除了體制內「在朝」的學者,可能也有一些「在野」的自由研究者。「在朝」和「在野」的區分和矛盾也許也會影響發言的角度。
徐魯青: 【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有一段談到了兒童教育。很多城市的街道只是為了讓行人快速透過,到達一個目的地。但作者簡·雅格布斯認為,街道應該是讓大家來停留和玩耍的,而不只是一個透過的工具。她還說到,小孩子接受教育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在學校課堂裏,而是在街道玩耍、和人交流的時候。
尹清露: 法國哲學家 朗西埃在【無知的教師】中提到,一個教師無意中做了一次教學實驗,他沒有透過講座教授學生知識,而是透過讓學生自己摸索著看書這種別樣的對話方式完成了教學,而且效果非常好。
朗西埃認為,這次實驗印證了大學教育的某種荒謬之處: 我們總覺得必須要透過教師的講解才能夠理解知識。講解這個動作看似承諾了一種平等,即「等你擁有了跟老師一樣的知識,你就變得平等了」,其實它反而隱藏了一種不平等的劃分: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有能者和無能者,以及博學的理性心智和無知的感性心智。 朗西埃認為這種劃分其實是一種虛構,因為所有人都擁有同等的智力。他還寫了一段話,大概是說我們現在生活在兩種分化的邏輯之下,一種是強硬的不平等邏輯,它來自國家資本或軍閥;另外一種是緩和的不平等邏輯,它用一所大型學校的模式來理解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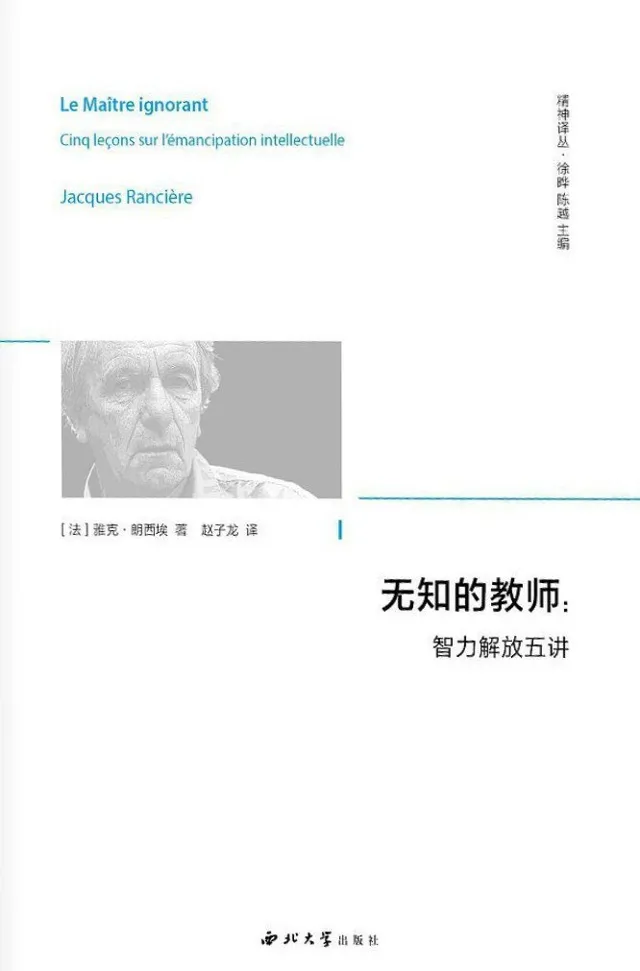
[法]雅各·朗西埃 著 趙子龍 譯
西北大學出版社 2020-1
讀到這裏,我想到 大家對學術酒吧的嘲諷/自嘲其實隱含著對於這種虛構的隱隱懷疑:難道必須要透過講解這個模式,我才能夠成為有身份有智力的人嗎?在酒吧這種「應該平等」的地方,這種不平等的矛盾就會格外顯現。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這樣的,在讀書之前或者進入學術體系訓練之前,我們都是一樣的人,但好像讀完幾年書,你的身份和作為人的本質都隨之改變了,好像一夜之間你就是個「聰明人」了。很多學術酒吧請的也是高校在讀博士這樣的高學歷人群,我會覺得學術訓練有點像一個成人儀式或者過渡儀式,人透過這個儀式就變得聰明了,背後的邏輯也挺荒謬的。
董子琪: 何兆武的【上學記】裏面提到,人類的關系有兩種:一種是權威的關系,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還有一種是聖潔的關系,比如夫妻之間沒有什麽你統治我、我統治你的關系,是屬於聖潔的關系。可是中國人的事情總是權威的成分多,聖潔的成分少。我覺得學術酒吧如果是要傳播知識,那應該是屬於聖潔的關系,但問卷篩選就把這種聖潔的關系變成了一個我要來考察選拔你的權威關系,有點自相矛盾。
潘文捷: 我覺得從最字面的意義上,學術酒吧要篩選聽眾說明這個機會是供不應求的,酒吧的位子有限,但想要來的人太多,所以需要限制人數。因為它的定位是學術酒吧,所以用學術的方式來篩選。
學術酒吧雖然是探討學術,但它更多是借由學術來探討現實。其實中國人有很強烈的論政傳統,對政治和現實的表達欲望很強。比如說中年男人喝完酒、出租司機和顧客聊天,都愛說一些國內國外大事件。但又沒有足夠多的平台讓我們去探討這些東西。
我們在網上經常能看到一些在娛樂事件中探討政治話題的例子,比如說汪小菲這個事情看起來是有錢富商跟女明星之間的愛恨情仇,但是人們會抓緊時間去表達他們對兩岸關系的看法。又比如說大家在談論張本智和這位桌球運動員的時候,也會抓緊時間去探討中日之間的關系。大家好像是很願意探討政治的,但有的時候這種探討會以娛樂的面目、八卦的面目出現,甚至是學術的面目出現。
04 社會科學「硬不硬核」:科學是唯一合法的思考方式嗎?
林子人: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我們錄制這期節目的前一天,上海最有名的那家學術酒吧官宣了最新一期活動預告,這期活動將回顧他們做過的工作,順帶回應「一些流傳較廣但離真實較遠的評論」。他們要聊的其中一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註意:社會科學是什麽?它真的不如自然科學「硬核」嗎?這樣的刻板印象從何而來?我雖然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但我想他們之所以會想要在最新的一期活動裏回應這個問題,肯定是因為之前他們舉辦過不少社科主題的分享,因此引發了一些爭議。
我們國家一直存在重理輕文的現象,出現這樣的質疑倒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但有意思的地方是,如果學術酒吧真的是一個舶來品,它原本確實是以科學領域的分享為主,而在上海的學術酒吧,分享的內容更加五花八門,特別是多了很多社科、人文向的內容。這的確也會引發一個長久的偏見,就是科學比人文社科的門檻更高,更不容易讓外行人明白。
這個話題讓我想到幾年前出版的【時髦的空話:後現代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濫用】,兩位作者都是物理學家,其中一位是艾倫·索卡爾,他在1996年做了一個惡作劇:給【社會文本】期刊投稿,在文章中模仿當代社科理論家,胡亂參照與科學有關卻晦澀難懂的術語,所以整篇文章完全是惡搞,但【社會文本】真的刊發了那篇文章。這件事情在學術界引發了廣泛激烈的討論。【時髦的空話】其實是這一事件的後續,索卡爾和另一位物理學家讓·布瑞克蒙在書中揭露了數位法國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著作中存在對科學概念濫用的情況,包括一些名字如雷貫耳的大咖,比如雅各·拉康、讓·鮑德裏亞和吉爾·德勒茲。【時髦的空話】讓讀者突然意識到,我們覺得這些大家巨著晦澀難懂,可能不是我們水平不行,而是他們可能都不完全確定自己在寫什麽。
以德勒茲為例,他被譽為最重要的當代法國思想家,寫過二十多本哲學著作。【時髦的空話】分析了他與加塔利合著的一本暢銷書【什麽是哲學?】,兩位作者發現,這本書中有科學名詞的密集運用,抽離語境、沒有任何明顯的邏輯,甚至也沒有以一般的科學意義來說明這些名詞,包括哥德爾定理、超限基數論、黎曼幾何、量子力學。但不熟悉這些主題的讀者是沒法從德勒茲的論述中增加任何對這些主題的理解的,而更專業的讀者則會發現,這些參照不是沒有意義,就是被用來包裝陳詞濫調。

[美]艾倫·索卡爾 [比]讓·布瑞克蒙 著 蔡佩君 譯
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2-2
因為直接點名指出了這些大咖的謬誤,【時髦的空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特別是在法國。我想不少本就對人文社科領域有偏見的人可能會加強他們的信念,就是人文社科不夠「硬」,只有「闡釋」,沒有「事實」。但兩位作者表示,他們寫作本書的目的不是攻擊人文社科,而只是反對毫無理論根據的挪用科學觀念,在非科學家的讀者面前濫用科學術語。
人文社科領域濫用科學術語的現象也流露出了一種科學主義的心態,即把科學當作唯一合法的思考方式。社會科學這個名稱本身其實就很科學主義,它試圖把對人類社會的研究變成一種科學,強調了其中的客觀性和某種真理的存在。所以【時髦的空話】也可以讓我們反思,人文社科領域的人對科學的曖昧情結,一方面抵制科學的霸權,一方面又把科學當作價值標尺來衡量自身。
尹清露: 我想到上次參加劉禾教授的講座,她提到如果我們讀不懂【賽伯格宣言】作者唐娜·哈拉維寫的東西是很正常的,因為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麽。哈拉維本身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人文和科學的跨界學者,也衍生出來一些概念,比如用克蘇魯的觀念去闡釋科學跟文化的雜交。
人文社會學科對於科學的復雜態度確實非常有意思,好像一方面我們不得不用科學的語言才能夠跟他們進行對話,但他們不需要去學習我們的語言,但另一方面這些社科學者其實也非常想要打破這兩者之間的通路,比如德勒茲和拉圖爾的做法。這些闡釋雖然在自然科學領域那裏看起來沒什麽意義,但對於解釋這兩者的通路是有意義的。他們的意圖並不是「用看似高大上的科學術語來解釋人文社科現象」,而是從根本上質疑「科學」與「人文」的劃分。
董子琪: 歷史學家王汎森說過,中國的傳統學科,比如經學史學文學,在五四以後有一個科學化規整的過程,即所謂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但在科學化處理的過程中,中國的傳統學科也在遭受流失,這被他稱為消耗型的轉換,無法硬套上西式科學的框架。
05 酒吧與「第三空間」: 面對面交流在社交媒體時代仍然不可替代
林子人: 學術酒吧或許是一個很新的社交方式,但以促進公共討論為目的文化活動其實一直存在,比如沙龍和讀書會。在個體越來越原子化、我們似乎能在互聯網上滿足各種社交需求的時代,我們為何還需要線下的聯結?
學術酒吧讓我想到了非常久遠的俱樂部傳統: 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歐洲,咖啡館、茶館、俱樂部和沙龍開始出現,這些場所向能夠買得起一杯咖啡、茶或一份報紙的人開放(很多情況下是中產階級白人男性)。這些場所構成了哈貝馬斯所描述的新公共領域,也就是在現代早期的宮廷和家庭之間的場所。哈貝馬斯認為,這個公共領域為市民提供了一個自由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進而為民主政治當下了重要基礎。
之前我讀過一本傳記【重返昨日世界】,那本書以山繆·強森和詹姆士·鮑斯維爾為核心人物的俱樂部為切口,呈現了18世紀的英國的俱樂部文化。強森所在的俱樂部是由一個名叫約舒亞·雷諾茲的畫家提出設立的,1763年,他非常擔心朋友山繆·強森的身體狀況,因為當時強森飽受抑郁癥的困擾。雷諾茲就提出,既然他的好朋友強森那麽喜歡聊天,也非常喜歡酒館,可以每周一次邀請一些朋友去一家叫做土耳其人頭的酒館進行一次聚會。所以在每個星期五的晚上,強森和雷諾茲都會和他們的朋友一起在那家酒館的包間裏面吃飯喝酒,一直聊到深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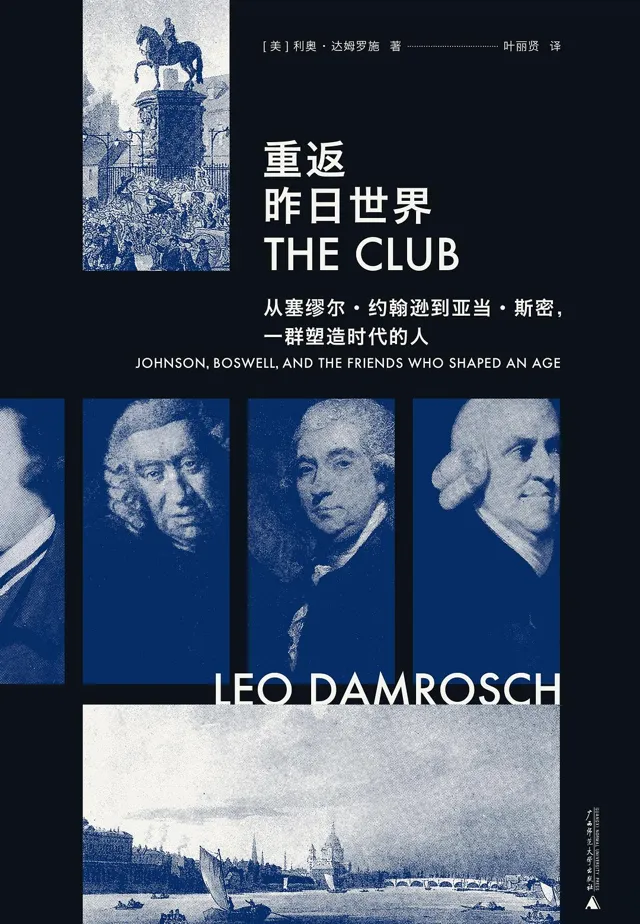
[美]利奧·達姆羅施 著 葉麗賢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6
這個俱樂部成員之間的碰面主要是為了社交、爭辯和相互學習,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領域,比如政治、法律、醫學、文學、藝術。隨著逐步發展,這個組織變得越來越有名氣,被公眾稱為文學俱樂部,在英國的文化史當中也是一段佳話。所以學術酒吧其實在18世紀的歐洲就已經存在了,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現在不過是在接續這個傳統罷了。
徐魯青: 哈貝馬斯說的公共領域還有一個說法,叫「第三空間」。城市裏面的第三空間的典型就是咖啡館、酒吧,是一種介於工作場所、私人空間,以及像廣場這樣最公共場所之間的更加松散的空間。人和人之間會在這個地方發生交往,認識新的朋友,聊一些介於公共和私人話題之間的事情。
虹口區有一家內山書店,在上世紀30年代,這家書店的主要功用是上海左翼作家的俱樂部。內山書店不僅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提供借書和出版的幫助,還為一些逃難的作家提供庇護,慢慢成為一個據點。有這樣一個空間把同好聚集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林子人: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後疫情時代,剛剛走出疫情這種非常封閉、大家極度缺少線下見面交流的時期。所以當下很多年輕人,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經歷過封閉大學生活的年輕人,迫切希望能夠在某種公共空間裏面去和別人交流任何事情。
徐魯青: 我現在還會有後疫情時期想要報復性見人的感覺,很抗拒線上做一些事情。不管是讀書會、跟人討論還是開會,我都希望能面對面見到人。不管有什麽樣的交鋒或意見不合,只要能面對一個具體的人,交流的感覺會更安心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