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侵即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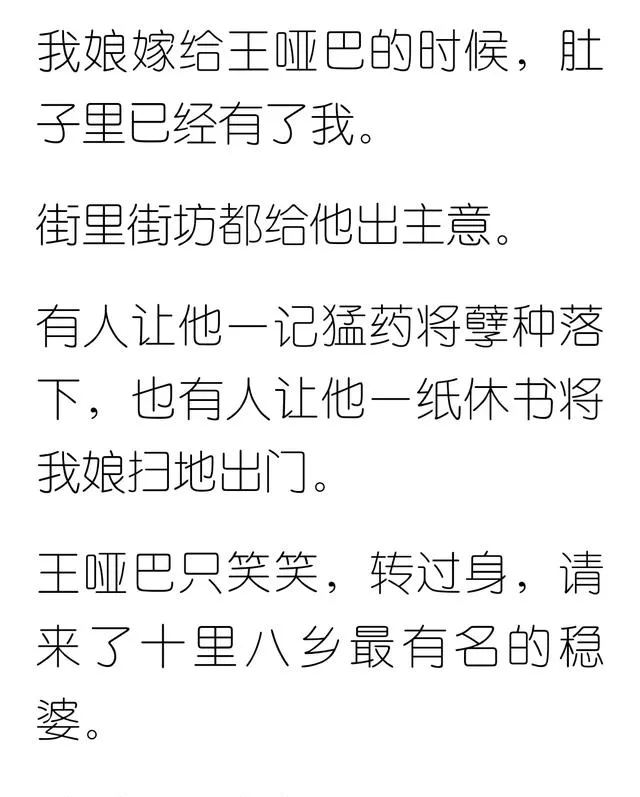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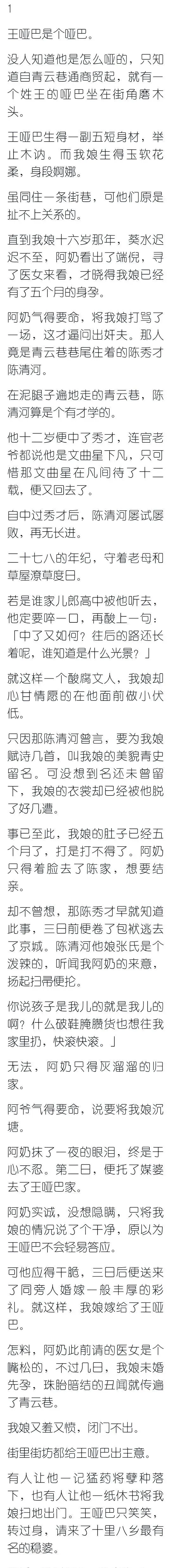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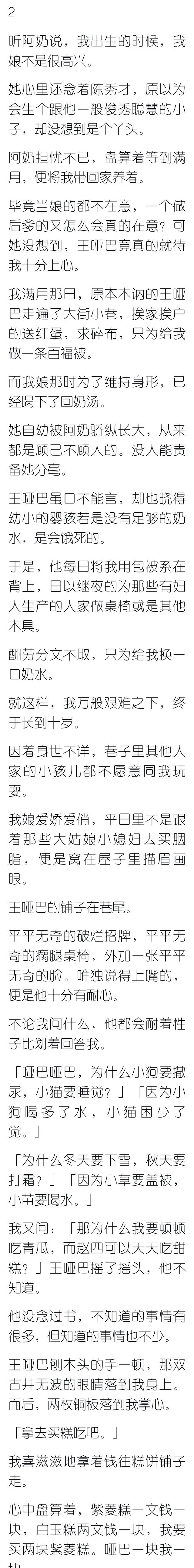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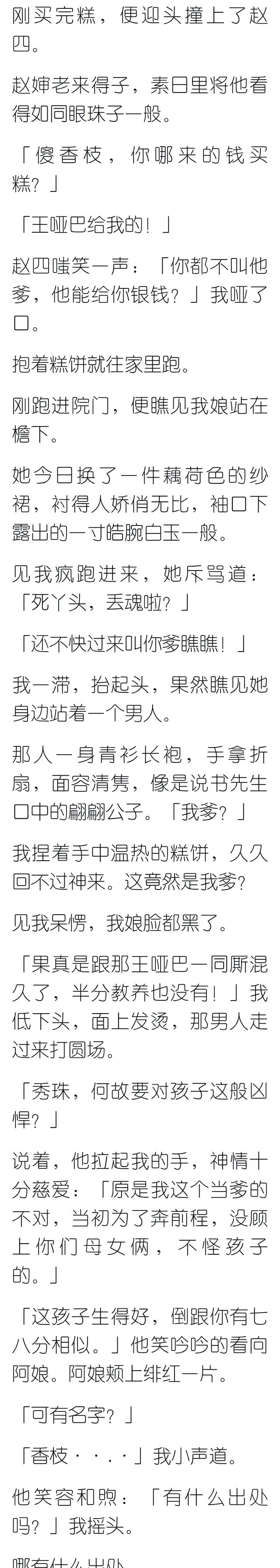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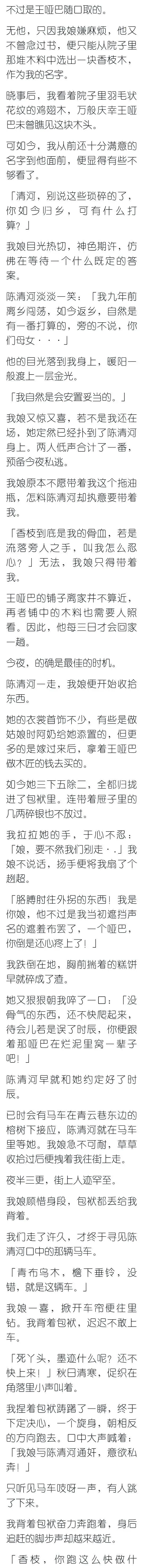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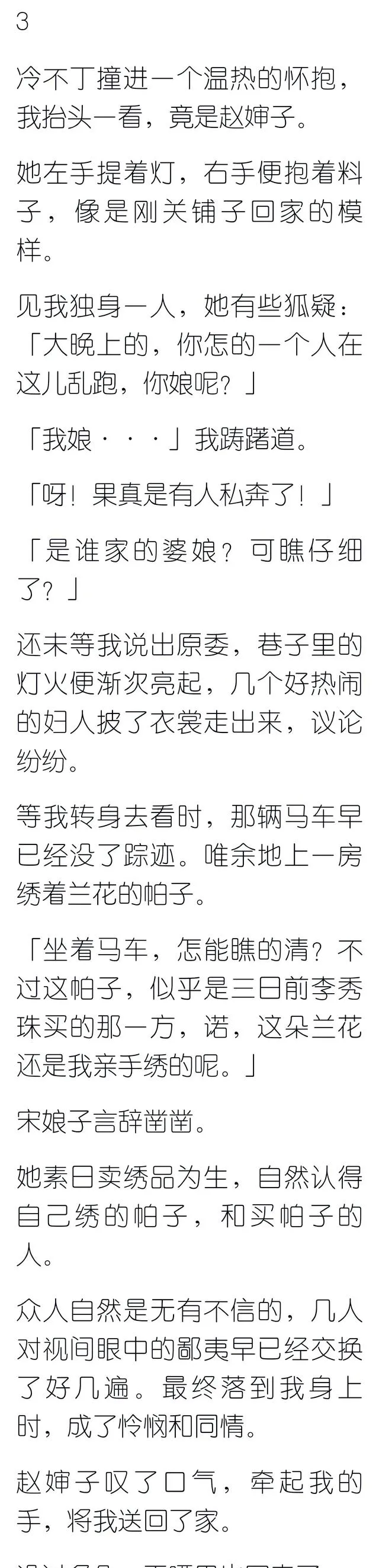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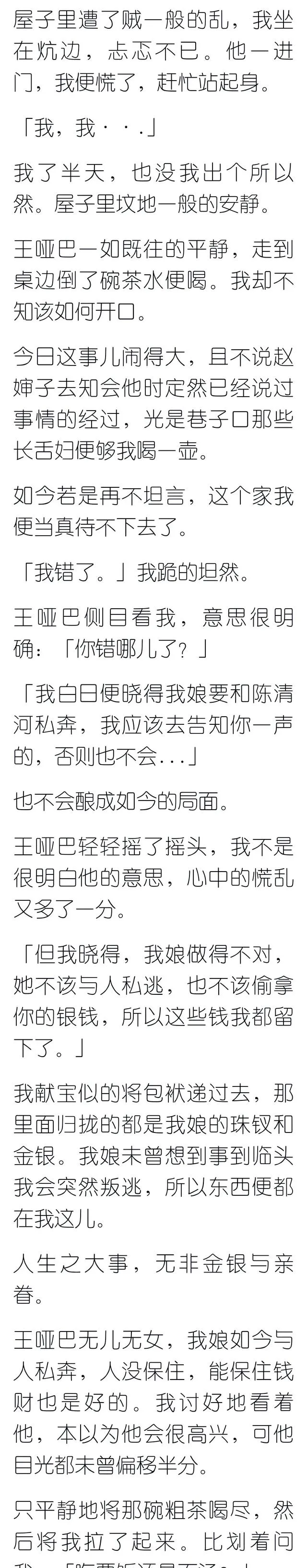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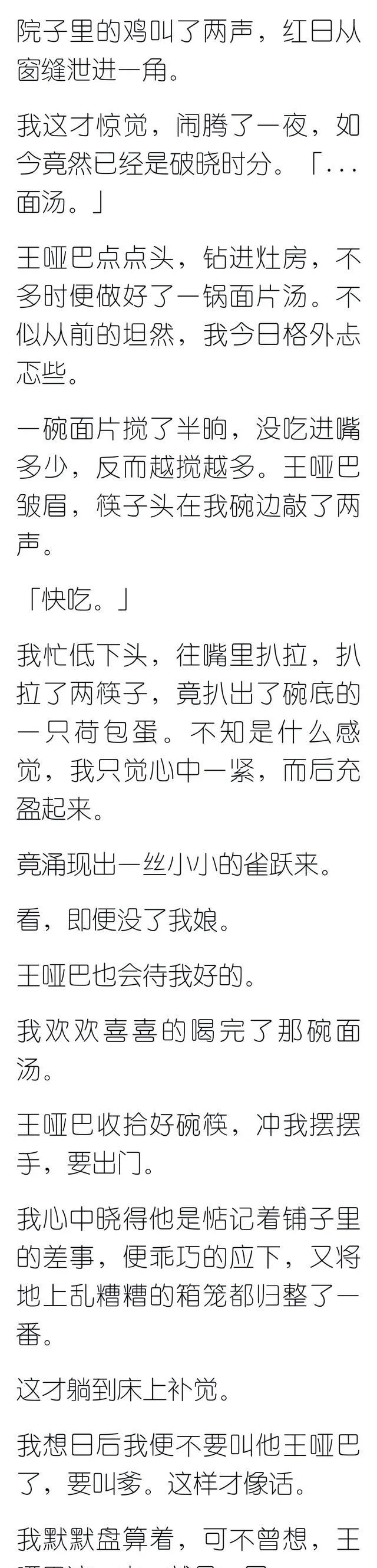
啞巴這一走,就是三日。
4
每過一日,我心中就慌亂一分。
包袱裏的金銀早已沒了蹤跡,只剩下兩吊銅板。
我也曾去鋪子裏尋過,可臨街的掌櫃都說王啞巴已經好幾日沒開門做生意了
也就是說,三日前,王啞巴便帶著家中全數的金銀走了。他去哪兒了呢?
沒人知道。
街頭巷尾的流言愈演愈烈。
有人說我娘與陳清河私奔時,原就是不願意帶上我的,是我自己卷了包袱非要跟著,眼看上不了馬車,這才大喊大叫。
人人都說,我小小年紀,心機手段卻不淺。
「都說聾子眼睛亮,瞎子耳朵靈,那王啞巴雖糊塗了一回,如今卻看清了,什麽瓜下什麽籽,這娘倆都不是好東西!」
一時之間,那些從前憐憫的目光都變成譏笑,刀子似的將我剮成片。第四日,王啞巴還是沒回來。
趙嬸子看不下去了,關了半日鋪子,將我領去了阿奶家。
路上她拉著我的手,一邊說我娘不知好歹,眼皮子淺,又一邊說王啞巴處事不正,便是不要我也該說一聲,哪有默不作聲便走掉的道理?
巷子七彎八拐,很快便到了,趙嬸子將我托付給阿奶,便回鋪子裏了。阿爺見了我,眉毛打成結,手中的旱煙在門檻上用力敲了敲。
險些讓進門的我崴了腳。
阿奶看了我一眼,便鉆進了竈房。
阿奶的家很小,院子很小,堂屋很小,就連裝粟飯的碗也很小。一碗粟飯,還要刮上兩勺才會遞到我手中。
飯桌上,阿奶沈著臉問我:「你娘當初既然要與人私奔,你怎的不勸阻一二,反而任由她跟著那姓陳的走了?」
我該說什麽呢?
說阿娘獨斷專行,不會聽我的,還是說我已經勸過了,她扇了我一巴掌?若是阿奶信我,便不會將這樣的問題拋給我一個十歲的孩童。
可若是不信,說什麽都沒用。
我不說話,恨不得也變成啞巴。那碗粟飯到底也沒吃完。
夜裏我睡在堆滿雜物的廂房,蓋著死魚般冷硬的棉被,忽然就有些想王啞巴了。
王啞巴不會說話,但他會讓我住寬敞的屋子,也會讓我睡松軟的床榻。王啞巴對我好,但我娘對他不好。
所以王啞巴理應對我不好。
從前那些好,是他寬容施舍,並非是為人本分。我該明白的。
我包著一眶眼淚,正要沈沈睡去。月色和冷言從墻縫鉆入:
這丫頭當真不留下嗎?到底也是秀珠的孩子,我們這樣會不會太·.·.·.」阿奶嘆了口氣,阿爺卻低聲喝道:
「那王啞巴都不要的貨色,你揀回來養著做什麽?雖說她是秀珠生的,可那也是陳清河的種!有這樣一個背信棄義,縮頭烏龜的一般的生父,她的品效能好到哪裏去?」
「好好好,都聽你的,那我明日就··」
些許破碎的話語被吹散進風裏,我沒聽太真切。
卻也明白,阿爺和阿奶之所以不喜歡我,是因為陳清河。第二日一早,我起身時,阿奶已經換了一副模樣。
她笑吟吟的替我紮發髻,又煮了兩只蛋給我當早飯。
「香枝啊,阿奶不願讓你受委屈,給你尋了個好去處,你可願意去?」我捏著雞蛋,心中警鈴大作。
「去哪兒?」 「城西張家。」
「啪」地一聲,雞蛋落到地上摔得粉碎。我的心也跟著裂開一條小縫。
青雲巷人人都曉得,城西張員外家的二公子在尋童養媳,尋了好幾年,都未曾有人將自己女兒送去。
不是因為他們愛女如命,而是因為那二公子天生患有癆病,活不長久,若是將女兒送去,豈非活活斷送了後半生?
但凡有些臉面的人家,都不會如此行事。
阿奶,我不想去,我會洗衣會做飯,還會刨木頭,讓我留下成嗎?」
阿奶聞言臉色一邊:「不去?你會洗衣做飯又如何?家裏廂房這麽小,哪有地方給你住?」
「我住柴房,住雜屋,都成的。」
「柴房要堆柴火,雜屋要放物件,都沒有你的位置,你還是早去張家為好。」
她口口聲聲沒有我的位置,可分明我娘出嫁前的閨房還空著。
他們寧願落灰,也不願讓我住進去。
阿奶居高臨下的俯視我,眼中無半分慈愛之情,只有淡漠和不耐。與我娘素日瞧我的模樣如出一轍。
直到此刻,我才終於明白,我娘那骨子裏的淡薄冷漠師從何處。
你若是有些能耐,當初跟著你娘一同走了便也罷了,如今留下,王啞巴不要你,我們家也是留不得你的。」
阿奶一邊說著,一邊拉扯著我往外走。
我萬般不願,但一個十歲的孩子是沒有反抗的能力的。只能任由著她牽引著我往外走。
誰知剛走到巷口,路便被人攔住了。
一道熟悉的身影由暗轉明,依舊是那張平平無奇的臉,和那雙古井無波的眼。
王啞巴伸手將我拽了過去,看著阿奶,意思很明確—「這是要做什麽?」
5
阿奶當然不會說是要將我送去張家。這樣的話實在是太跌份了。
見王啞巴一副護犢子的模樣,阿奶慌張了一瞬,旋即道:「你去哪兒了?怎的如今才回來,我還以為你不要這孩子了呢。」
王啞巴不說話,握著我的手收攏了一分,我聞見他身上塵土的味道。像是剛趕路回來的模樣。
「那這孩子你還要嗎?」
王啞巴拉著我轉身,腳步平穩的走出巷子。這便是他給出的答案。
王啞巴帶我回了家。
一進門,隔壁的趙嬸子便沖了進來。
見我全須全尾,她拍拍胸口松了口氣。
我昨日將你送去時,原想著你阿娘雖走了,但你好歹算是李家的血脈,你阿爺阿奶不會不管你,可不曾想···
「幸好今日那老虔婆同張員外家的婆子說話時被我聽著了,否則指不定怎麽樣呢!」
趙嬸子快人快語,說話竹筒倒豆子一般。
趙四也在門口探頭探腦:「香枝,你阿奶要是真要賣你,不如賣到我家吧,我娘正好想要個女兒···」
話還沒說完,趙嬸子便狠狠剜了他一眼:「小兔崽子滾回去做你的課業去!」
王啞巴看了她一眼,從包袱中掏出一張紙。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字,像是張契紙。
趙四一溜煙竄過來,對著日頭草草看了兩眼,咧嘴笑了。
「李香枝,你爹要送你去念書啦!」
「小兔崽子胡說什麽?」
「娘,我沒胡說,你看,這還有書塾的私印呢!」趙嬸子湊過去一看,果然瞧見一方紅色的銘印。
她驚了一驚,問王啞巴:「你當真要送香枝去念書?」
王啞巴點了點頭,比劃著:「束脩已交,要念。」
我這才明白過來,原來王啞巴消失的這些天,是去給我奔走念書的事兒了。青雲巷曾出過一個從九品的筆帖式,雖只是個微末小官,但她家中箍桶為
生,這已經是再好不過的前程了。
所以十裏八鄉,女子讀書並不是什麽駭人聽聞的事情。
只不過升鬥小民果腹已然不易,極少會有人家將前程放置到女兒家的肩上。所以,巷子裏念書的姑娘家並不算多。
我隱在那些不念書的姑娘家裏,也不算打眼。
可我沒想到,王啞巴不聲不響的消失了好幾日,竟然去幹了這般大的一件事。
趙嬸子嘆了口氣,掰著手指頭算著:「一年束脩二兩銀子,饒是我開著間布料鋪子都有些吃力,你做一張木桌才掙二十枚銅板,怎麽供得起?」
王啞巴拂了拂衣角的塵土,比劃著:「人有手,便能吃飯。」趙嬸子不再多話。
那張紙上寫的入學期限是三日後,她便拉著我去鋪子裏做裝書用的箱籠。我看著那張契紙,一顆心怦怦跳個不停。
「趙嬸,王啞巴為何突然要送我去念書啊?」
剪刀劃過布料的聲音很利落,趙嬸子的聲音卻很低悶。
「原是我那日多嘴,說了句那陳清河在京中做了官,如今你娘跟了去,日後站穩了腳跟,怕是要回來尋你的麻煩,他這才動了心思。」
說著,趙嬸放下針線,將我的肩膀掰正,一字一句道:「他是要你好好念書,日後奔個前程,哪怕你那便宜爹娘上門尋仇,你也能應對得當。」
「這一番謀劃全然是為了你,香枝,他當得起你一聲爹。」
我抿抿唇,低下了頭。
6
第二日,我們啟程去縣裏。
其實並非是不能留在鎮上,而是那些婦人嘴太碎。
我娘與陳清河淫奔的事情傳遍了大街小巷,連帶著我也受了牽連,若是留在鎮上,怕是不得安穩。
所以王啞巴將鋪子盤了出去,又將那間小院子托付給了趙嬸,這才放心離家。
誰知剛坐上牛車,便聽見奚落的聲音:「這王啞巴當真是被豬油蒙了心吧?竟想著送個小丫頭片子去念書,偏生還是那淫婦的賤種。」
「可不是?若不是豬油蒙了心又怎麽會被李秀珠那種女人哄騙兩次?」
「我看啊,可不是騙,說不準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若不然,那王啞巴怎的到如今,連個親生骨肉都沒有?」
「怕不是不能生,當初才要個肚子裏有貨的吧哈哈哈哈···」王啞巴偏過頭,沒什麽表情。
可他向來是耳聰目明的,又怎麽會沒聽見?
我只呆楞了一瞬,便掏出包袱裏的木雕扔了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扔在那長舌婦的面門上。
我學著李秀珠的模樣,惡狠狠的啐了一口:「老東西,舌頭長,面杖一搟,當頭繩!」
那婦人尖聲叫了起來,剛反應過來,牛車已經緩緩啟程。王啞巴微微愕然。
我猶豫了一瞬,還是伸手拉了拉他。
「爹,你送我的木雕丟了,等去了縣裏,再給我做一個好不好?」從小到大,我從曾喚過王啞巴一聲爹。
換個稱呼不過是舌頭打個彎兒的事兒,可我卻怎麽都叫不出口。並非是我性子別扭。
而是我覺得,我口口聲聲喚著的娘從未將我當過親生骨肉,若是我叫了王啞巴爹,豈不是將他和我那生父陳清河混為一談了?
我年紀太小,是非對錯無從分辨,但我曉得,王啞巴罪不至此。可如今我想明白了。
我生來便無父無母,唯一愛護我的人,只有王啞巴。縱使隔著層血親,他也是我爹。
那只粗糙的手在我掌心顫抖了一下,而後他緩緩點了點頭。「好。」
束脩一交,他手中的銀錢便不多了。
統共不過二兩銀子,租賃了間小院子便花了半兩,余下的銀錢他還要在街上盤間小鋪子繼續做木匠生意。
由此一來,我們每日便只能喝些粟米粥果腹。但好在第二日,我便要到書院報到了。
雲蒙書院是縣裏最普通的一所書院。
無他,有名的書院束脩太貴,我爹交不起。但有書可念已經算是不錯了。
書院的父子姓賀,是個白胡子老頭。初見我時,他眉毛打成了個死結。
「是個丫頭?」
這話一出,我便曉得,他不喜歡我。
賀父子不喜女子讀書,但我爹已然交了束脩,書院便只能將我收下。
男女七歲不同席,縱使書院男女學生都收,但授課時,中間還是隔了一道屏風。
跟我一同坐在女席的姑娘姓陸,聽聞是通判府陸家的姑娘。
我不曉得通判是多大的官,但我曉得,這等官家小姐應當是不願意同我打交道的,所以我一直不敢貿然搭話。
直到賀夫子如常講課,其他學生都聽得津津有味,只有我聽得雲裏夢裏。我只得厚著臉皮去問陸姑娘:「敢問姑娘,夫子講的是哪一頁?」
陸姑娘順著我的目光看過來,一瞧見我手中的書,便「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你還未啟蒙吧?」
我點點頭,她身後的丫鬟便過來幫我將拿反的書翻正過來,又翻到了賀夫子正在講的那一頁。
只可惜我並不識字,依舊不曉得夫子在講些什麽。
但也不願讓人看輕,便坐直了身子,硬裝出好學的模樣。好容易結束一上午的課業,我便直奔飯堂。
誰知剛盛好一碗飯菜,便被人撞翻在地。
「這位同窗,實在抱歉。」
7
書院每日包兩頓餐食,可每日的飯食都是有定量的。我看著被打翻在地的飯菜,心中一股無名火升起。
擡眼望去,只瞧見一人沖我無辜的眨眼。
「一時失手,見諒。」
「想必你家中應當給你額外送了飯食吧?」那人語氣淡然,神態自若。
雲蒙書院雖普通,但招收的學生也有些富家子弟,因此每到飯點時,家中的小廝女使便會來送飯食。
唯獨我,是沒有的。
我看著他華貴的衣衫,拳頭握了又松。轉頭蹲下去撿地上的飯菜。
周圍響起一片驚呼:「她是乞丐嗎?都不嫌臟啊···」書院的地擦的幹凈,不算臟,能入口。
我不搭理,自顧自的撿,卻倏然被人攔住。
他輕咳兩聲,耳廓微紅:「··你別撿了,大不了,我把我的飯食給你吃。」
我欣然同意,利落的站起身。「在哪兒?」
有小廝上前來,遞上食盒,我開啟一看,口水差點沒淌到地上。蝦仁燴飯,松子雞丁,五香鴨脯,最下面甚至還有一碟糕餅。
這些我吃席時才能見著的菜式,就這麽輕而易舉的出現在了食盒裏。我沖他拱了拱手,坐下便吃了起來。
一邊吃,一邊聽見譏諷的聲音:「這人是不知羞嗎?不知道君子不食嗟來之食嗎?怎的這般沒臉···」
我的確不知道什麽叫做嗟來之食,但我知道餓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吃完全部的飯菜,我又將糕餅包了起來,預備回去給我爹吃。
下了學,我飛奔回小院。
我爹正在院子裏磨木頭,我將糕餅獻寶似的舉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卻並不接。
我急了:「這是同窗送的,不是我偷的!」
他拍了拍身上的木屑,接過那包糕餅,慢慢展開。
嘆了口氣,舉著那張宣紙,比劃著告訴我:「宣紙是用來寫字的,不是用來包餅的。」
我垂下頭,默不作聲。
不敢告訴他,我壓根就聽不懂夫子講課,他這二兩銀子怕是打了水漂。可下一瞬,那只粗糙的大手牽起我,帶著些許木屑的清香。
他拉著我進了屋子,翻出一本書。與其說是書,不如說是圖冊。
上面清晰的畫著做桌椅板凳,檀木花床的步驟。
我爹一頁一頁的翻給我看,這都是從前他拜師學藝後自己畫的,雖有些粗劣,但勝在精簡。
他比劃著告訴我:「飯要一口一口的吃,字也要一個一個的認,像是做桌椅一樣,急不得。」
我明白,他是想告訴我,我如今學得有些吃力,但若是就此放棄,或是生了厭倦之心,那才是真的不值。
我點了點頭,第二日下學後,便去了夫子的書房。
8
賀夫子見是我,眉頭又皺了幾分。「何事?」
我鼓起勇氣將昨日那包糕餅奉上,而後屈膝跪下:「學生尚未啟蒙,聽不懂夫子講課,還望夫子能指點一二。」
黑漆石的地面硌得膝蓋生疼,可我不敢表現分毫。
賀夫子挑眉:「既未曾啟蒙便先去啟蒙,我這兒是書院,不是私塾。」
「學生家中貧困,實在拿不出額外啟蒙的錢財。」
「這點錢都拿不出來,那你是因何要念書?」賀夫子冷哼一聲,聲音寒冰一般的刺骨。
我楞了一瞬,竟是答不出來。我究竟是因何要念書?
賀夫子將手中的茶盞丟回案桌上,泅出一小片暗影。
「我這書院雖不大,但來此讀書的,或是為了科舉仕途,或是為了讀書明理,必然都有自己的目的。自你之前書院不是未曾招收過女學生,可她們都是略識得幾個字後便退了學。」
「我且告訴你,我這裏只教四書五經,古言策論,不教婦德之守馭夫之道,你若是也同她們一般,趁著三日試學期還未過,早早找那賬房退了束脩另拜山門才是。」
一番話聽罷,我才終於明白,為何初見時,夫子會那般說。我不再猶豫,俯首又磕了個頭。
「學生念書不為嫁人。」
「那是為何?」
我想起李秀珠扇我的那個巴掌,想起阿奶盛的半碗粟飯,亦想起我爹那雙永遠粗糙的大手。
一字一句道:「為己為利,為家人,也為前程。」賀夫子未曾想到我會如此答,微微一滯。
下一瞬拿起那包糕餅,將白胡子扒拉開往嘴裏送了一塊。含糊道:「還算聰明。」
就這樣,賀夫子徹底認了我這個學生。
每日裏我照常像其他人一般聽課,下學後他在單獨為我啟蒙半個時辰。就這樣學了一個月,上課時我已然能勉強跟上進度。
陸家姑娘陸含貞驚詫不已:「怎的不過一個月,你就一日千裏了?」我只抿唇笑,不敢告訴她實情。
畢竟賀夫子收了我爹一副黃花梨木床,若是真論起來,這應當算是賄賂師長?
9
冬去春來,夏至秋敗。
我在雲蒙書院念書的第六個年頭,已然從墊底的拖油瓶變成了書院的魁首。六年前我大字不識,如今便是在課堂上,也敢鬥膽與賀夫子論上一論了。
那個六年前潑了我飯菜的紈絝子孟尋如今也成了我的小跟班,每日巴巴的跟在我身後,央著我同他講策論。
若不是為了每日不落的食盒,我當真是不願搭理他。
不久之後便是院試鄉試,賀夫子屬意我下場抖一抖文墨,看能不能撈回個秀我心中忐忑,原本想與有貞商議一番。
卻不曾想,她告假三日後便再未來過書院。無法,我只能尋去了通判府。
門房的小廝通傳了好一陣,才終於來了個丫鬟將我請進去。這是我頭一次進陸府,也是我頭一次見這樣大的宅子。
裏頭布景雅致,回廊曲折,連廊下懸掛的紅穗子都精巧無比。陸含貞的院子在最東邊。
我剛進門,她瞧見我,臉色發白:「香枝,你怎麽來了?」
「賀夫子說起今年院試,我想下場一試,所以來問問你,要不要同去?」陸含貞扯出一抹笑:「你苦學這些年,的確該試一試,至於我...·」
「還是算了罷。」 我不解:「為何?」
陸含貞低下頭,一雙素手絞著帕子,露出半邊柔婉的側臉。
「我年歲到了,父親說,還是嫁人為重,科舉仕途···到底不是女人家該做的事兒。」
我這才註意到,院子裏一片喜色,桌上放著繡了一半的蓋頭。原來她要嫁人了。
賀夫子當年的話,遲了六年,終於是釘在了我心上。我問:「那你可覺得有理?」
陸含貞沈默了一瞬,道:「道理自在人心,哪裏又是我能辯駁的?我不恨旁的,只恨老天將我生作了一副女兒身,叫我滿腹詩書卻也只能做個提線木偶。」
我低下頭,只覺得那滿目的紅有些刺眼。
氣氛瞬間凝滯下來,陸含貞揚起一個勉強的笑。
「不過也好,便是能去科考,我也不一定能中,你且看那朝堂中女官只有寥寥數人,便該曉得女子科舉之艱難,如今我安心待嫁,日後夫婦一心,家宅安寧,何嘗不是另一種圓滿?」
她故作輕松的安慰自己,可我明白,這些詞句中飽含多少不甘與心酸。這世道,從來都是如此艱難。
我說不出一個不字。
只道:「別怪我直言,若是你出嫁之後,未來郎婿待你不好呢?生的孩子也仕途無望呢?那時你是否會後悔如今未曾下場一搏?」
有貞,科舉的確不是人生唯一要走的路,可婚嫁也不是,這兩條路,並不相悖,你若是想,大可以先科考一番,再來談論婚嫁之事。」
「屆時你若是能高中做官,未來郎婿若是待你不好,你大可以挺直腰桿去教訓他一番,同樣是當朝為官,誰又比誰矮上一截?」
我言辭激蕩,目光懇切,並非是慫恿,而是不甘。
同窗六載,有貞贈過我筆墨紙硯,也曾將府中的木匠差事包攬給我爹,好讓我交得起束脩。
這樣和善聰慧的一個姑娘,實在是不該困在那逼仄宅院。
有貞擡起頭,頰邊滾下兩顆晶瑩的淚珠。
她慘然一笑:「有貞··有貞,我有時在想,為何父親要給我起這個名字,為何兩位兄長可以叫有睿,有明,為何落到女子頭上的,就非得是一個「貞」字?」
「我朝女子不可單獨立戶改籍,若是入朝為官,便可以。」
「香枝,我想明白了,便是為了這一樁小事,我也該去博一搏。」這哪裏是一樁小事呢?
這分明是,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將她困在陰濕角落的巨石。不過好在,她已經尋到紓解之法了。
10
三日後,有貞說服了陸大人,我們一同啟程入京科考。同行的,還有孟尋。
以他的水平,便是考官瞎了眼也中不了,可他還是著臉跟來了。
就算中不了,也算是科考過一場,日後旁人若是罵我紈絝,也該考量考量,這買賣不虧!」
我與有貞無奈,只得帶著他。
誰知剛入京沒幾日,在鋪子裏買筆墨紙硯時,便迎頭撞上了一個熟人—陳清河。
三年過去,他早已沒了當時的清雋之姿,衣衫襤褸,破為落魄。
那掌櫃的不住將他往外驅趕:「走走走!沒人要你的書畫,如今正要院試,別妨礙我做生意!」
陳清河面上掛不住,抱著書畫退了兩步,陰冷的目光落到我們身上。
他並未認出我,只啐了一口:「呸!幾個丫頭片子還想高中?做你們的春秋大夢去吧!」
孟尋是個愛惹事的主兒,擼起袖子便要上前,有貞將他攔住:「如今我們是來科考的,可不是玩耍的。」
孟尋這才退了回來。
等陳清河走出鋪子,我才小聲問那掌櫃:「這是哪家的學子嗎?」
那掌櫃的先是一笑,而後鄙夷道:「什麽學子?不過是西街一個潦倒秀才罷了,六年前僥幸攀上了尚書府家的小姐,以為能倒插門享富貴,卻不曉得那高門大戶哪裏有那麽好攀?」
「然後呢?」
那掌櫃笑了笑,不說話。
孟尋遞過去一塊銀子:「快說,少賣關子!」
「那小姐雖是個糊塗的,但尚書大人混跡官場,哪裏會看不出他的心思,不過兩三個月,便將那小姐許了人家嫁了出去,而這秀才也被絕了仕途。」
「打發了他便是,為何要絕了仕途?」孟尋不解。
那掌櫃神秘一笑,又小聲道:「當然是因為那秀才心思不純嘍!他不僅對那小姐甜言蜜語,還妄圖生米煮成熟飯,且還在外頭養了一房,這才惹惱了那尚書大人。」
我蹙眉:「養了一房?」
「是嘍,說來也怪,旁人養外室都養年輕嬌嫩的,偏生他養個半老徐娘,聽臨街賣胭脂的婆子說,那女子竟然還生養過,嘖嘖。」
「那他被絕了仕途,外室如何了?」我追問。
「一個無媒無聘的外室,自然是沒什麽出路的,每日裏跟著他吃糠咽菜便也罷了。」
「對了,姑娘毛筆是要羊毫的還是狼毫的?」
有貞隨意選了兩只,我低下頭,久久回不過神來。
我沒想到李秀珠當初拋下一切跟著陳清河來京城,過的竟然是這種日子。但人各有命,我只呆楞了一瞬,便低頭選起了毛筆。
11
院試的日子很快便到了。
我們三人備好了筆墨,預備試一試才學。
誰知剛走到貢院門口,便被攔住了去路。
「我這兒有帷帽,姑娘可要買一頂?」那婦人笑吟吟的問我。
我這才註意到,貢院外的姑娘們,大多蒙著面紗亦或是帷帽。
「考不上不打緊,可若是失了名節可就損失大了。」
要買嗎?」有頁問我。
我搖了搖頭:「既到了如今的地步,比得便是才學和定力,若是再戴一頂帷帽,是否會讓考官疑心舞弊我不知道,但決計會影響筆力。」
「我既站到了此處,如今最不在意的,便是名節。」
我看著那婦人,一字一句,而後頭也不回的進了貢院。考試結束的很快。
考完後,我精疲力盡,在客棧狠狠睡了一覺。
放榜要等到半月後,有貞沒心思在京中玩耍,孟尋也趕著回去鬥蟈蟈,而我也沒盤纏住店了。
於是商議一番,第二日便回了縣城。
我爹見著我第一面便說:「別怕考不上,大不了再試一回。」
我哭笑不得:「爹,都還未曾放榜呢,怎麽就曉得考不上了?你就這般不相信我這個做女兒的嗎?」
我爹忙去打嘴。
這次院試參試的學子不多,放榜也早了幾日。
偏巧那日我爹帶我回了青雲巷,想要拿幾塊木料。一下牛車,便迎面撞上了巷子裏的張婆子。
她不懷好意的笑:「喲,香枝都長這麽大了?聽你趙嬸說你還去參加院試了,可有考中秀才?」
她一個丫頭片子,哪有這麽大的能耐?無非就是拿著王啞巴的錢在書院釣郎婿,香枝,可曾釣中一個富家公子?」
幾人笑得促狹,我爹氣得發抖。
我不動聲色的冷哼一聲,旋即笑道:「考不考得上的,原也說不準,只是張阿婆,聽說你孫子這回也去考了一遭,可有把握?」
青雲街人人都曉得,她那孫子已經考了十來年,屢戰屢敗。
張婆子臉上掛不住,強笑道:「這我哪裏曉得?不過男人嘛,到底是比姑娘家要強些的。」
我淡笑低頭,不說話。
念書的這幾年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那便是與粗鄙者論道理只會得不償失。實在是不值。
我跟著我爹往巷子裏走,一行人還站在巷口吹噓聊天時,有快馬急停。而後是清脆的鑼鼓聲—
「青雲巷王姑娘高中,喜報——」
那報喜的小廝問道:「敢問王姑娘家在何處?」
眾人呆楞了片刻,誰都不知道哪裏還有個王姑娘。
直到有人驚詫出聲:「那王啞巴不就姓王嗎?莫非是···」狐疑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然後變成震驚。
「香枝那死丫頭當真中秀才了?!」
「你說話註意些,人家如今也是有功名在身了!」
「當真是歹竹出好筍,李秀珠那般的品性,也能生出這麽有出息的孩子。十四歲便中了秀才,比起陳清河當初,也差不到哪裏去啊。」
誰也沒想到,當初頂著私生子的名頭出生的王香枝,能有這般作為。一時之間,艷羨驚疑不定。
我無暇顧及,拉著爹回了小院。
晚上我爹親自下廚做了酒菜,邀了趙嬸母子同吃。一別數年,趙四已經長成了個身姿挺拔的少年。
見了我,話還未曾說出口,臉先紅了一半。
「香枝,恭喜你高中。」
我遙遙舉杯,盡數飲下。
趙嬸推搡了一把趙四:「你瞧瞧人家香枝,如今是秀才了,日後指不定有多大的出息,倒是你,十六七了還只知道舞刀弄槍。」
「文武本不相同,自是不能作比的。」
趙嬸點頭稱是,夾菜時,又不動聲色的將趙四往我這頭擠。
我爹抱著那卷報喜的卷軸,高興的喝了大半壺酒,直到醉到不省人事也不曾放開。
趙嬸一邊打發趙四將他搬去裏屋,一邊同我攀談。
「你爹苦了大半輩子,如今也算是熬到頭了。」
「說實話,那時你阿奶想要將李秀珠嫁給你爹時,鄉裏鄉親都覺著不公,縱使你爹家底不豐,又身有缺陷,也不該受這樣的折辱,可他卻應得幹脆,你可知為何?」
我收碗的手一頓:「為何?」
趙嬸嘆了口氣:「因為他的阿娘便是同李秀珠一般的處境,只不過他娘選擇一碗湯藥將孩子打去,卻不曾想,腹中的他已然足月,還是生了下來,卻因那碗湯藥成了個啞巴。」
「所以他娶你娘,不是為了旁的,只是為了你,他從一開始,就是只想做你爹,而並非是李秀珠的丈夫。」
我被澆築在原地,回不過神來。
從前我不是未曾想過這個問題,可我那時只以為是他良善,所以待我便格外好些。
如今想來,他的良善,比我所感受到的,還要多出十倍不止。這世上,竟真的有人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我而來。
胸腔裏的某一處似乎被填充的鼓了起來。
12
我中了秀才,有貞中了案首。
賀夫子說,若是要學業再精進一層,便該去白桐書院研學,那裏都是大儒名師。
我與有貞離開雲蒙書院那日,孟尋前來相送。他扭扭捏捏了半天,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看得急了,將他拽到有貞面前:「有話就說,如此扭捏作態,不像是個頂天立地的男人,倒像是書院裏那只縮頭縮腦的王八!」
孟尋「騰」地一下漲紅了臉,將袖中的簪子舉到有貞面前。
「有貞,我自知學識不如你,但日後一定會用功讀書,定不會叫你失望。」男未婚,女未嫁。
誰都知道送簪子是什麽意思。
有貞拿起那支簪子,孟尋一喜,可下一瞬,那只簪子又被遞回他手中。
「這簪子做工粗劣,不是買的吧?」
「是我···是我自己做的。」
有貞笑了笑:「你雖素日裏沒個正形,但好歹算是明白真心待人。」
「你既明白我的真心,又為何不收?」
「因為這世上有比真心更重要的東西。」「什麽?」
「我的前程,我的仕途。」有貞一字一句,目光如星。
「孟尋,我曉得你待我的真心,但我如今想要的不是這個。我想科舉順暢,我想青雲直上,我想青史留名,我雖是個女子,但心中的貪欲不比你們男人少。」
我想要的很多很多,但這其中並不包括情愛。「所以,你的真心先收好吧。」
孟尋有些氣餒:「你這算是拒絕我了嗎?」
有貞扶了扶發髻,像是在扶珠釵,又像是在扶那頂虛空的烏紗帽。
她道:「也不算,日後你若是能與我同朝為官,我也能考慮考慮。」
孟尋受了鼓舞一般,拱手行了個禮,便吭哧癟肚的往回跑,便跑還便嚷嚷著要挑燈夜讀。
白桐書院在宿州,需走水路。
我拉著有貞上了船,船夫剛將纖繩解開,縮在角落裏的趙四這才慌慌張張的跑了出來。
隔著一方碧波,他遙遙喊話:「香枝!你···你且安心去念書,我在青雲巷等你。」
簡簡單單的一句話,道盡了少年萬般羞澀。
我剛舉起手想要回應他,便被我爹摁了下去。他沈著一張臉,搖了搖頭。
不知是在說別理他,還是在說不要他。我笑了笑,一息之間船已經離了岸。
那少年站在岸邊,捧著一顆真心,等著我應答。
我終是不忍,回道:「別等任何人,有緣自會相見!」水波蕩漾,清風微寒。
他不知回了句什麽,被吹散在了風裏。但那都不重要了。
我自有我的前程要奔,他自有他的長路要趕。不過是
於道各努力,千裏自同風罷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