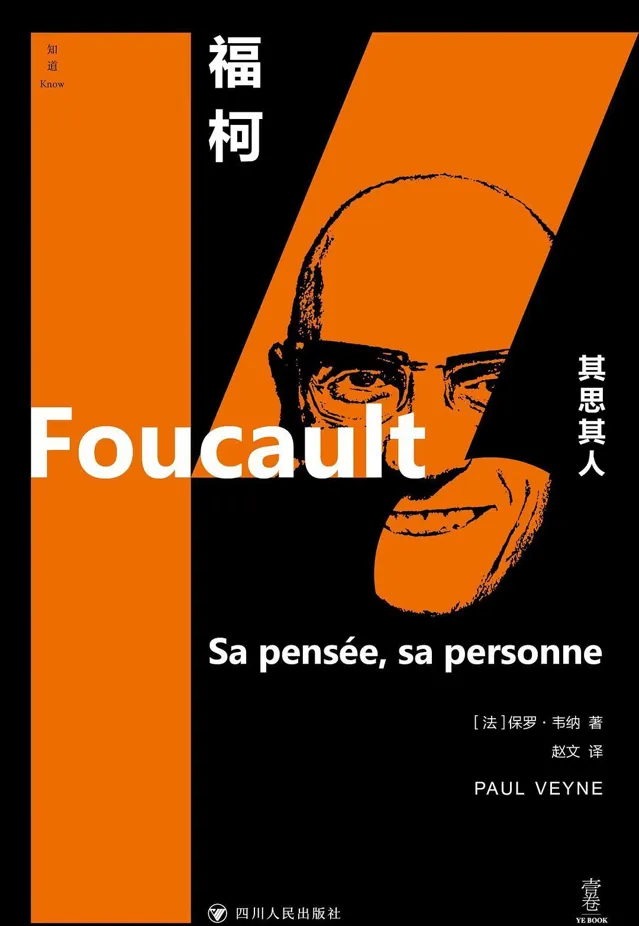
【福柯:其思其人】, [法]保羅·韋納著,趙文譯,四川人民出版社丨壹卷YeBook,2023年9月版,272頁,72.00元
關於法國思想家妙思·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學術界與思想界永遠有說不完的話題;而作為思想鬥士,他的思想形象更是一直活躍在反抗權力壓迫的前沿陣地。
哈貝馬斯曾經說過,在對我們的時代進行診斷的哲學家中間,福柯的精神影響是最為持久的。但是福柯的形象與影響一直以來又是出了名的難以歸類和定義,人們總是覺得很難說他「是」什麽,因此更多從他「不是」什麽來接近他、理解他。對於思想家而言,「不是」似乎比「是」更有思想與行動的誘惑力,更像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永遠特立獨行、雖然對其下一步行動總是難以捉摸但是你會放心與他並肩「搞怪」的小夥伴。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布羅薩(Alain Brossat)【福柯:危險哲學家】(羅惠珍譯,漓江出版社,2014年)的書評,布羅薩在前言裏站在哲學家的立場批評福柯視哲學作品為「工具箱」、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使用的觀點,但是我更認同的是福柯而不是布羅薩——在福柯看來,承載觀念的書籍就是「輕便工具箱」,在需要的時候開啟和使用;福柯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工具兜售者和武器的鑄造者,願意自己的書是像手術刀、燃燒瓶或地下坑道一樣可以被人們使用的東西,而且但願它們在被用過之後就像爆竹一樣燃為灰燼。這就是思想鬥士與哲學家的區別,很顯然時代更需要的是像福柯這樣的「危險哲學家」和武器兜售者。
法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福柯生前曾經的助手與摯友保羅·韋納(Paul Veyne)的專著【福柯:其思其人】 (原書名Foucault, sa pensée, sa personne,2008)就是以「不是」作為全書的開頭和結尾——「不,福柯不是結構主義思想家,也不是某種‘六八年思想’的結果;他既非相對主義者亦非歷史主義者,他更不會到處追蹤探查意識形態。」(導言,第1頁)「這位所謂的左翼,既非弗洛伊德主義者,亦非馬克思主義者;既非社會學家,亦非進步論者或第三世界主義者,當然,他也不是海德格爾主義者。」(最後一章「獨行俠的肖像」,249頁)出現在全書開頭和最後一章的這兩段否定句式的判斷話語不僅表明了作者力圖糾正世人關於福柯的不正確印象與歸類的急切用心,而且從保羅·韋納與福柯的關系以及其古典歷史學家的身份而言,他的「不是」之論不僅是一種知音者的判斷,而且更像是送出給思想界的一份證詞。
韋納接著肯定了福柯作為一位偉大的懷疑論思想家和真理思想家的卓越地位:「在今天,在這個時代,他之為人甚是稀有,他是一位懷疑論思想家,他所信仰的是真理,但又從來不是觀念的真理,而是存在於事實當中,存在於無以計數的歷史事實當中的真理——這種真理也進入了他的著作。」福柯面向的不是觀念中的真理而是存在於歷史事實中的真理——這對於今天的學術界和思想界來說所具有的意義非同尋常,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思考和展開爭論的重要議題。韋納同時在註釋中參照了約翰·萊赫曼(John Rajchman)對福柯的定義性表述:「福柯是我們時代偉大的懷疑者。他懷疑獨斷的統一性和哲學人類學。他是關於離散(dispersion)和獨異性(singularité)的哲學家。」(第1頁)懷疑的、離散的、獨異的,這是對「不是」之「是」的最好解讀,更好地詮釋了福柯之「是」的真實內涵。
但是,無論懷疑還是獨異,在福柯身上都是有著雙重性的。「這一位懷疑論者同時是一個雙重存在。只要思想著,他就停駐在那玻璃缸之外,以便能觀察其中遊動的魚。但若是在生活裏,他就會發現他自己也置身於玻璃缸中,自己則是眾多魚中的一條,必須面對抉擇……這位懷疑論者既是一位觀察者,置身於他對之深感憂懼的魚缸之外,同時又是那些金魚中的一條。」(導言,第3頁)「玻璃缸」和「金魚」是對思想者的精神與肉身的真實境況的隱喻,它最早來自福柯母親的回憶——福柯在高中時期的某一天曾盯著魚缸中遊弋的金魚問她:「媽媽,魚在想什麽?」(259頁)韋納的演繹和闡釋精彩地揭示了福柯作為思想者的真實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那條只能在魚缸中遊弋的、但是會思考的金魚,就像帕斯卡爾的那根會思考的蘆葦;由於思想而能置身於魚缸之外,但是又必須在魚缸之中感受魚缸的邊界、探索突破邊界和權力規範的可能。這是兼懷疑論者、觀察者和行動者於一身的多重身份,懷疑、觀察和思考的結果是拆解以及反抗來自魚缸的邊界與權力羅網的壓迫。
書中講到的一個例子很能說明福柯作為魚缸內外的思想者與反抗者的雙重形象:當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2020)在1974年當上法國總統之後,馬上邀請幾位思想家到愛麗舍宮共進午餐。福柯收到邀請後回復說可以參加,但條件是他可能會在午餐會上就所謂的「紅毛衣」案的審理向總統提問,因為在這案件裏有一人被判有罪並且可能被處以死刑。吉斯卡爾拒絕了這個要求,福柯也就沒出現在愛麗舍宮的午餐會上(251頁)。在魚缸裏不放棄言論與行動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要堅守在魚缸之外的觀察與思考,這是事關知識分子的「屁股」與「頭腦」的一種優雅而決絕的形象,是真假知識分子的試金石。我想象當時福柯在表述拒絕出席的時候,或許會模仿讓-雅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口吻在說:哦!再見吧,愛麗舍宮!
更重要的是,韋納提醒我們說「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那個魚缸」(20頁),在這裏他談的是福柯思想中的話語、真理與時代關系的論述。「我們每個人只能夠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去思考」——這是福柯的巴黎高師同學讓·瑞木松(Jean d'Ormesson)說的,但所表述的是福柯的觀點。韋納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在每個時代裏,同時代人都被封閉在話語之中,就像身處一個玻璃魚缸中一樣,他們意識不到魚缸,看不到魚缸就在那兒。錯誤的概括和‘話語’依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在每一個時期內,它們都被認作真理。真理(la vérité)因而總是被化簡為講述真理(dire vrai),簡化為時代所囿限的對真理的容忍度之內的言說——盡管這種言說總會被後來時代的人們覺得可笑。」(21-22頁)韋納力圖闡釋的是福柯式研究的原創性:只能在時間語境中探討真理,在人類歷史的巨大墳場中對「話語」進行挖掘和清理,「以澄清歷史地層之間的絕對差異,進而讓最後那一批普遍觀念走向終結」(22頁)。這當然是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的重要工作,「他的根本方法是把文本作者放置在其時代之中去做出盡可能精準的理解」(25頁),但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批判性思考:驅除和清算那種普遍的、宏大的歷史觀,揭示歷史現象的獨異性與無理據性。進而言之,只要認識到根本不存在普遍的、超歷史的真理,一旦看清楚「被那些大詞所遮蓋的思想和現實」(18頁),對歷史的批判性思考就必然引向對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金魚缸的批判性思考。
許多福柯研究者都會同意的是,在福柯的思想譜系中,關於真理、知識和權力的關系是其核心所在,正是在這裏凸顯出福柯作為權力壓迫的揭露者與批判者的思想鬥士形象。在韋納書中的「真理的社會學歷史:知識、權力、裝置」這一章因此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關於「真理」,福柯所關註的並非「什麽是真理」,而是真理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建構、被講述以及如何反過來形塑了歷史。福柯自己說過,他全部工作的目的就是來說明「整套實踐和真理統治是如何聯合起來構成了一種知識-權力機制(或裝置:dispositif)的」。韋納對此的闡釋是:「凡是被信以為真的必將獲得服從。現在就來讓我們看看這種權力:所有這一切是怎麽鑄成這一權力的呢?它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話語’給現實打上烙印,而在現實中權力無所不在,這一點我們會很快看到。凡是被斷定為真的,都要求得到服從。」(171-172頁)對於那些被建構的「真理」和被講述的同時也被人們信以為真的觀點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轉化為約束性和壓迫性的權力,凡是有觀察力和思考能力的人們應該都並不陌生。
但是按照韋納的解釋,福柯也並沒有把所有權力都看作是惡魔,下面的這兩段論述是對福柯權力觀的精準概括:「政治哲學太過經常地將權力簡化為集權政府、利維坦這個末世的巨獸。但權力並非只源自這令人厭惡的一極,‘它的傳布借助於某種毛細血管組織,這組織如此繁密,以至於我好奇是否還存在權力不起作用的地方’。……對社會起促成(或禁止)作用的,不僅有中央權力的活動,而且還有不可計數的細小權力。若無這一叢叢細弱微毫的細小權力,利維坦將寸步難行——不是因為所有權力都來自中央,也不是因為利維坦無所不在,而是因為在這利維坦下面除了抓不住的不斷流動的沙子之外再無他物。」「我們逃離不了權力關系。單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也時時處處地在改變著這些關系。權力是一種雙邊關系。它總是伴隨著我們或多或少進行抵抗但卻是自由地(是的,自由地)達成同意的服從。」(173-174頁)這是比認識到話語以「真理」之名如何轉化為權力更重要的問題——無論服從還是抵抗,都是取決於被施行權力約束的物件的同意或拒絕,在那個金魚缸裏沒有誰是真正無辜的被約束、被壓迫者。
而所謂的「裝置」,這是福柯關於權力的實作機制的形象表述,甚至可以讓人聯想到當代藝術中的裝置藝術——在不失水準的情況下它們都是某種觀念的實作機制。韋納的闡釋是:「裝置與其說是制造了我們的某種決定機制,不如說是一種藩籬,我們的思維和自由要以之為參照做出或不做出反應。……它是‘具有某種效能的’一種工具,這種‘效能在社會中引發某種後果,產生某種事情;它必定是有效果的’。它的影響不只限於知識物件;它還作用於個體與社會;當然,作用就必然引起反作用。‘話語’釋出命令、施行鎮壓、誘導勸說並進行組織。它是規則與個體之間‘聯系、摩擦,乃至可能的沖突的交匯點’。」(174頁)當人們面對作用於自己的權力約束的時候,對於何謂「具有某種效能的」工具就不難理解;另外,只要稍微關心一下最新的話語變化,也就不難發現話語與裝置的聯動關系。
在經過深入的思考之後,還是要回到作為懷疑論者和獨行俠的形象上來。韋納說「福柯既非虛無主義者亦非主體論者,既非相對主義者亦非歷史主義者。正如他所承認的那樣,他是懷疑論者」(69頁)。他想起了福柯那句確鑿無疑的原話:在他去世前二十五天,一位敏銳的訪談者問他:「如果您認為不存在普遍真理,那麽您是懷疑論者嗎?」「絕對」,福柯回答說。「就這麽一個詞。福柯質疑所有無所不包的真理,質疑我們那些偉大的、無時間的真理,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同上)福柯告訴韋納,對海德格爾來說,偉大的問題是去認識「何為真理的基礎」;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重要的是去認識當我們談論真理時我們在說什麽;「但就我的觀點而言,問題在於:真理何以如此不真?」(同上)這是從最根本問題上進行思考的懷疑論者。
關於獨行俠,是讓-克勞德·帕塞隆(Jean-Claude Passeron)建議韋納以此稱呼福柯的,韋納認為這個詞很好地勾勒了福柯的那種敏捷、優雅的形象,還有總伴隨在他身邊的笑語歡聲。同時他也指出,福柯這位獨行俠並不總是「對一切都心懷否拒」,並不是那種陰郁的悲觀主義者(77頁)。在全書最後一章「獨行俠的肖像」有不少精準、深刻而又動情的描述和分析。如果從思想光譜與行動選擇來看,韋納認為福柯「這位所謂的左翼……是一位‘非左(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的非左)非右’的尼采主義者。他從來都是不合時宜的(用尼采的話來說),從來都居於他的時代的外部。他不是一個墨守成規者,這也足以使人將他歸為左翼」。但是無論福柯是如何「非左非右」,有一點是必須提及的,那就是他只有在左翼戰士當中,只有透過【解放報】,「才能找到在他的個人戰鬥中可以依靠的同誌」(249頁)。
福柯在現實面前從不選擇忘記,「他看到,這個世界,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對他而言是沒有合法性(legitimite)可言的。他刻苦工作,並不生活在永遠義憤填膺或狂熱好鬥的狀態之中,但卻保持訊息靈通,並時常出手,打擊不可容忍的流弊」(251頁)。作為一位永遠在出擊的既非烏托邦的亦非虛無主義的、既非保守的亦非革命的改良者;他眼光敏銳,無情地洞穿迷霧而看到了種種獨異事物的任意性質(263頁)。
但是作為獨行俠的福柯並沒有隨意鼓動別人和他一起去戰鬥,他曾經在課堂上說他不會告訴諸位這是你必須加入的戰鬥,因為沒有什麽理由這麽說。在他看來選擇立場和決定是否介入完全是個人的選擇,他既不會為這些選擇做論證,也不會將它們強加於人,因為沒有任何理由證明這些選擇是正確的。「我不會將我自己展現為一個普遍的鬥士……如果說我確乎為了這樣或那樣的事業而戰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個事業對我來說,對我的真正主體性來說,是重要的」。他為了反對法國監獄的高度警戒區而采取了戰鬥行為,他認為這種制度是不可容忍的;而「當一個事情是不可容忍的時候,你就無須再忍」( 220-221頁)。更重要的是,他只是提醒別人「去認識你想要的是什麽以及你所不能容忍的是什麽」(265頁)。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這才是最根本性的問題。
由於韋納是福柯的摯友,因此他的這本書是個人性很強的思想評述。如果從福柯與歷史學研究的視角來看,還可以同時閱讀和參照福柯研究專家基利爾·奧法雷爾(CJare O'Farrell)的一篇綜述性的長文,其中有些論述可以看作是對韋納著作的補充和回應。她在論文中指出福柯著述的中心是關於真理與權力的問題:福柯審慎而又堅定地把權力和真理從先驗領域移置到歷史敘事之中,一方面關註的是哲學的而非在傳統理解上的歷史學問題,關於「真理問題」的研究不是為了尋求永恒真理的不變定義,而是為了審查在歷史中真與假之間的劃分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另一方面把權力界定為一種在其被施展時才存在著的關系,這樣做的結果是讓權力徹底成為歷史性的。因此一定程度上,每一個個體都參與了權力與反抗的關系逐步展開的歷史。(基利爾·奧法雷爾【妙思·福柯:歷史和文化的無意識】,南茜·帕端拿、莎拉·富特主編【史學理論手冊】[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2013;余偉、何立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24-225頁)這可以看作是對保羅·韋納關於「真理的社會學歷史」的一種回應。同時我想起了艾歷·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歷史哲學,他在【城邦的世界】中說,「歷史」的本質所在就是「為秩序的真理而戰!」,「人類由此而被發現是以歷史的方式向真理意義上的更高生存水平前進的」(【秩序與歷史】卷二,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70、72頁)。在真理與歷史的問題上,可以說福柯與沃格林不謀而合,也就是我曾經在一篇關於沃格林的書評中所講的:對於歷史研究本身,我們應該再次強調的是:歷史學家應以面向真理的方式向歷史探詢。
奧法雷爾關於福柯在歷史學研究中的意義與影響是這樣說的:「福柯對當代歷史編纂學的貢獻是至關重要的。他深思熟慮地著手挑戰大量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觀念,尤其是那些尋求把人類歷史某些方面予以普遍化和去歷史化的觀念。重要的是要記住他不是在孤立地進行工作。……他與激進的科學史家們和年鑒學派,有著諸多共同之處。他的工作不斷提供著豐富的工具——方法論的和經驗的工具,而歷史學家們和其他人,在範圍廣泛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職業性學科的各項科目中,可以毫不猶豫地使用這些工具。福柯的工作處於哲學研究和歷史研究的交叉點上,這也許是其具有廣泛吸重力的關鍵點之一。」(同上,245頁)應該說這是對保羅·韋納關於福柯思想與歷史研究關系的相關論述的很好補充。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在福柯的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方面,奧法雷爾與保羅·韋納的觀點是相當一致的,她指出:「福柯希望透過他的歷史實踐,能幫助人們明白他們能夠做出選擇,而非僅僅讓自己俯首帖耳地去踐履那些堅固的歷史傳統或者屈從於不變的制度性結構的重壓。……這意味著每個人,無論其處境為何,都有著某些回旋余地。……無論限制為何,處於什麽樣既定處境下,人們都有能力做出選擇。」(同上,234頁)我忘記了福柯在哪裏說過一句話:「實際上我們比自己想象中自由得多。」這也印證了韋納和奧法雷爾對福柯關於歷史實踐與現實關系的解讀是對的:從歷史實踐的視角來看,每個人實際上都有無法被徹底剝奪的自由,無論如何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選擇。
寫到這裏,在南國的寒夜中福柯的獨行俠形象似乎更像爆竹一樣綻放在夜空,猛然想起2024年即將到來。回顧過去的一年,從南國蒼翠的越秀山邊到北方的一條清澈的河流,生命的激情一直在奔湧向前。韋納說,福柯透過他的寫作建構了他的生活和他自己,但是福柯自己說:「我對我寫下的一切都不感興趣,我所關心的是我還能寫什麽,還能做什麽。」(242頁)這就是福柯作為懷疑論者、獨行俠和思想鬥士給我們帶來的最愉快的啟示與鼓舞。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