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論道德譜系】
尼采之英雄道德

對尼采而言,【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就像一部福音書,因此,在他後來的著作僅僅扮演著評論者的角色。
如果歐洲不欣賞尼采的詩歌,也許,它會理解尼采的散文。
隨著查拉圖斯特拉的歌聲遠去,先知變身為哲學家,把玩起邏輯學。
我們這位哲學家雖然懷疑邏輯,但那又有什麽關系?——如果邏輯學不能使論證牢不可破,它至少能使論證更為明白清晰。
尼采從未感到如此寂寞,連他的朋友們都覺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古怪。
曾與尼采在巴塞爾共事的奧韋爾貝克和布爾克哈特等學者對【悲劇的誕生】贊賞有加,但此時,他們不得不悲嘆,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已經沒落,而要他們為一位詩人的誕生喝彩,他們做不到。
尼采的妹妹(她差點兒就佐證了尼采的觀點:對於一位沒有妻子的哲學家來說,姐妹可以很好地扮演妻子的角色)突然離他而去,要去嫁給一位尼采極度鄙視的反猶太分子,然後,再去巴拉圭建立一塊共產主義殖民地。
考慮到兄長的健康,她懇求羸弱的尼采一同前往。
但是,比起健康的身體,尼采更珍重自己的心靈,他希望留在戰鬥打響的地方,對他來說,歐洲是一家必不可少的「文化博物館」"。
從此,尼采居無定所,不時地四處遷移,先後在瑞士、威尼斯、熱那亞、尼斯、杜林生活。
在聖馬可廣場的獅子周圍,經常有鴿子聚集,尼采就喜歡在鴿子堆裏寫作——「聖馬可廣場是我最好的工作室」。
然而,他不得不聽從哈姆雷特的建議:勿站在太陽底下,因為陽光會刺傷他患病的眼睛。
於是,尼采不得不把自己關在昏暗、骯臟、寒冷的閣樓裏。
在緊閉的窗前奮筆疾書。
由於眼疾,尼采不再著書立說,寫下的只是一些格言警句。
他將自己的部份零散感悟收集起來,整合了兩部書:【善惡的彼岸】和【論道德的譜系】。
他希望能在書中淪陷舊有道德,為超人的道德鋪平道路。
有一陣子,尼采重新做回一名語言學家,力求以那並非無可挑剔的詞源學來推廣他的新倫理。
他發現,在德語中,有兩個詞表示「不好」,一個是 schlecht,另一個是bose。
Schlecht用在上級對下級的語境中,表示「平庸的、一般的」,後來演變為「粗鄙的、沒用的、不好的」。
Bose用在下級對上級的語境中,表示「不熟悉的、不規則的、不可估量的、危險的、有害的、殘忍的」,比如說,拿破侖很bose。
許多原始的民族都害怕傑出的人,把這些人看作分裂分子,中國便有這麽一句俗語:「偉人乃公眾之不幸。」
類似的,gut也有兩種含義,分別與schlecht和bose相反:一種含義為貴族使用,表示「強大的,勇敢的、有權的、好戰的,神聖的」(gut一詞來源於Gott,神),另一種含義為平民使用,表示「熟悉的、和平的、無害的、善良的」。
在這裏,我們看到兩種相互對立的對人類行為的價值評判、兩種倫理觀念和標準,即「貴族道德」和「庶民道德」—— 一種是主人的道德,一種是奴隸的道德。
貴族道德是古典時代【大致來說,古典時代始於公元前7世紀,經歷基督教的崛起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公元5世記),直至古典文化的消解。從地理位置看,是在地中海周邊地區。】公認的道德標準,尤其對羅馬人而言。
在羅馬人(哪怕是一個普通民眾)看來,所謂的美德便是男人氣概、勇氣、冒險和膽量。
但在亞洲,尤其是在猶太人的腦海中,卻孕育了另一種道德標準:遭受政治壓迫的人們變得謙遜、無助、無私。
實際上,這是在求助。
在庶民道德的籠罩下,人們熱愛安定與和平,厭惡冒險和權力、人們不再追求力量,他們樂於狡詐,人與人之間的報復不再公開,而是變得隱秘;憐憫代替了嚴厲,模仿代替了創新,人們不再因享有殊榮而自豪,而是無情地譴責自己的良心,因為榮譽只屬於異教徒、羅馬人、封建主和貴族,良心才屬於猶太人,基督徒、資產階級和大眾。
從阿摩司到耶穌,一大批能說會道的先知將奴隸階層的思想發揚光大,使之幾乎成為普世倫理觀。
於是,「俗世」和「肉體」成為罪惡的代名詞,貧窮成了道德的象征。
而耶穌則將這種價值標準推至頂峰。
在他看來,人人都擁有平等的價值,享有平等的權利。
後來,耶穌的教義又發展出民主思想,功利主義、社會主義。
於是,人們開始根據庶民哲學、漸進的平等化和庸俗化、頹廢和墮落的生活來定義進步。
頹廢生活的最後一幕便是對憐憫慈悲、自我犧牲的贊美,對罪大惡極者不理性的安慰,以及「人類社會排泄功能的喪失」。
積極的同情是可取的,而憐憫則是一種麻痹心靈的奢侈品,對那些無可救藥、昏庸無能、窮兇極惡的廢物,那些滿是缺陷、活該害病、違法犯罪的畜生來說,憐憫則是浪費感情。
憐憫隱含著粗俗,是一種侵犯,比如,「‘探望病人’是想到鄰居無助之時,心生的一種類似性高潮的優越感」。
這一切「道德」的背後是一種隱秘的權力意誌。
愛是對占有的渴望,求愛是一場戰鬥,交媾則是戰鬥後的控制。
也難怪唐荷西要殺了卡門,那是為了防止她成為他人的所有物。
「人們以為自己在愛情中是無私的,那是因為他們想從他人身上得到好處,這些好處往往是從他自己身上無法得到的。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便會要求占有對方……【省略號之後為法國思想家邦雅曼·貢斯當的話,原文為法語。其實,尼采曾更為委婉地談論愛情,他說:「男人會在何時對女人進發激情?……最低等的激情來自純粹的色欲,但當一個男人深感脆弱、需要幫助,情緒高漲時,靈魂會像決堤的河流,啃噬他。同時,他會產生被撫摸、被侵犯的感覺。偉大愛情的源泉便在這一刻噴發。」(【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287頁。)尼采還參照諺語說:「‘真愛中,擁抱肉體的是靈魂‘,這是我聽過的最為純潔的話。」】在所有的人類情感中,愛情是最自私的,所以,受傷時,愛情最不寬容。」
即便是愛真理,也只是出於占有真理的渴望,或許,愛真理者只想開墾一片處女地,成為第一個占有真理的人。
而謙卑是權力意誌的保護色。
在權力意誌面前,理智和道德便成為絕望之物,因為它們只是被權力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武器。
「哲學體系是一座華麗的海市蜃樓」,我們看到的並非我們長久尋找的,而只是我們自身欲望的反映。
「所有的哲學家都會擺出一副姿態、好像他們的思想都是透過冷峻、純粹、神聖且不偏不倚的辯證法得來的……實際上,他們的觀點只是片面的主張,想法或‘建議’,它們基本上是被抽象、提煉出來的哲學家心中的欲望,事後,他們便會搜集種種論點來為自己辯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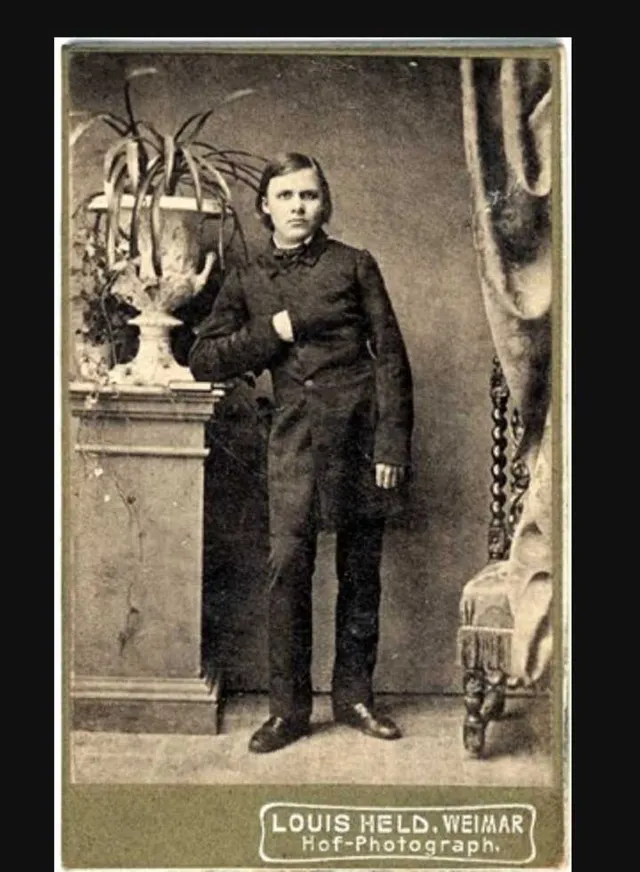
且,決定我們思想的便是這些埋藏在最底層的欲望、這些權力意誌的悸動。
"更多的時候,人類既無法意識到,也無法感受到自己的智力活動……有意識的思考………是人類最微弱的智力活動。」
本能是權力意誌最直接的動作,它不受意識的幹擾,因此,「本能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富智力的活動」。
確實,意識的作用被糊裏糊塗地高估了,「意識或許應該被放在第二位,它幾乎可以說是次要的、多余的。也許,意識註定要消失,註定要被完全的自動化取代」。
強者不會用理性的外衣來掩飾內心的欲望,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即「我要」。
對那些充滿活力、未受腐蝕、擁有主人翁精神的靈魂來說,欲望因其本身而正當地存在,而良心、憐憫或悔恨絕無立錐之地。
但如今,猶太教、基督教民主思想風行於世,使得強者們羞於承認自己擁有強大的力量和健壯的身體,他們開始為自己尋找「理由」。
貴族的美德和價值標準正在慢慢消失。
「歐洲正在受到新佛教的威脅」,連叔本華和華格納都皈依了佛教,成為可憐的佛教徒。
「歐洲整個道德體系的建立是以一種對大眾有用的價值為基礎的。」
強者不得施展強大的力量,他們必須盡可能表現得如弱者一樣,因為「勿做我們力量範圍之外的事,便是善」,康德,這位「柯尼斯堡的偉大中國佬」不也證明,人類絕不能被當作手段嗎?於是,強者的本能——打獵、戰鬥、征服和統治,由於缺乏宣泄的渠道,逐漸演變成自我傷害,並進而產生禁欲主義和「歹心」。
「一切本能,如果找不到一個排解通道,便會向內深入——這就是人類那不斷發展的‘內向化’:於是,我們便有了被稱之為靈魂的最初形式。」
墮落的原理是這樣的:領袖們受到大眾美德的影響,並被大眾美德庸俗化。
因此,「第一要務便是迫使道德體系服從等級秩序,並對各種道德假設重新進行考查,直至人們徹底認識到,說出‘適合你的也適合他’這樣的話是不道德的"。
不一樣的特點會產生不一樣的功能,所以,在社會中,強者那「罪惡」的品德與弱者那「美好」的品德都不可或缺。
苦難、暴力、危險、戰爭,與善良、和平有同等的價值。
眾所周知,偉大的人物只會在充滿危險暴力的環境中、在迫使人變得殘酷時才誕生。
對人來說,最好的東西便是強大的意誌、權力以及無限的激情。
一個沒有激情的人就像一塊豆腐,終將一事無成。
貪婪、嫉妒甚至仇恨都是鬥爭、選擇、生存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惡之於善,相當於變異之於遺傳、創新和試驗之於風俗習慣。
如果,如果永不用近乎犯罪的手段沖擊一下現有的「秩序」,哪裏有進步可言?如果惡真的不好,那它早已不復存在。
因此,我們必須警惕自己,不要過於善良,因為「人類必然變得越來越善,又越來越惡」。
發現世界上還有如此多的罪惡、如此多殘酷的事情,尼采深感欣慰。
他認為,「殘忍構成了古人極大的喜悅和快樂」,一想到這一點,尼采便感到虐待狂般的愉悅。
他相信,我們從悲劇中,或者從任何崇高的事物中獲得的快樂都是一種經過提煉的間接的殘忍。
「人類是最殘酷的動物,」查拉圖斯特拉說,「欣賞悲劇的時候、觀看鬥牛的時候、旁觀刑罰的時候,他們能夠感受到人間未曾有過的快樂。然後,人類創造了地獄……瞧,地獄就是他的人間天堂。」
如今,想想自己的壓迫者在另一個世界接受永久的懲罰,人類便能忍受一切苦難了。
終極的倫理學是生物學層面的,我們評判事物的依據應該是該事物對生命的價值,為此,我們需要從生理學的角度「重估一切價值」。
而真正能考驗一個人、一個族群、一個物種的是活力、能力和權力。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或許能夠接受十九世紀(不然,一切高尚的美德便會遭到淪陷),因為在十九世紀,肉體得到人們的重視。
靈魂是有機體的功能之一。
人類大腦中的血,多一滴或少一滴,都會給人帶來無限痛楚,這種痛楚遠遠超過被鷹啄食肝臟的普羅米修斯所忍受的痛苦。
不同的食物催生不同的思想方法,比如,米飯推動佛教的形成,而德國的形而上學則是暢飲啤酒的結果。
因此,一種哲學是真理還是謬論,完全取決於該哲學贊美的是人生的昇華還是人生的墮落。
墮落者說,「人生毫無價值」,其實,還不如讓他說「我毫無價值」。
當人生中一切崇高的價值開始腐爛,當民主--即對一切偉人的質疑——每十個年頭淪陷一個民族,人生為何還值得過活?
現今,熱愛交際的歐洲人總喜歡擺出傲人的架勢,仿佛他們才是唯一獲得認可的種族。
他們對自己的品質,比如公德心、慈善、尊重他人、勤奮、節制、謙遜、寬容、同情心等,大加贊美、並視這些品質為人類特有的美德。
在這些美德的作用下,他們在普通大眾面前彬彬有禮、隱忍不言,顯得極有用處。
但在一些情況下,當人們認為領袖或領頭羊確不可少時,他們便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召集大批聰明的善於交際的人,來代替發號施令的指揮官,各種議會機構便源於此。
然而,要是果真有一位專斷獨裁者出現,來管理這些善於社交的歐洲人、那也是上天的一種祝福,好似一塊巨大的磐石被卸去——拿破侖出現後的一系列影響便是最好的明證:一部受拿破侖影響的世界史、幾乎就是一部人類追求高尚幸福的歷史。
因為,透過一個個偉大的個人、一個個偉大的時期,這種高尚的幸福橫跨了整個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