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歲的女孩椰子沒想到,會有13萬人圍觀她在社交媒體上研究「超低精力者如何改善洗澡拖延」。
人們設想了一些逼迫自己擰開水龍頭的辦法,「偷襲,趁自己不備直接擠一坨洗發水到頭上」「一進門就脫光衣服」,但結局往往是「洗發水在頭頂幹掉」「坐在冰冷的浴缸邊玩手機一小時動彈不得」,甚至因為無力洗澡而無法上床,「已經24小時沒合眼了」。
表面來看,椰子的生活並沒有明顯的紕漏,她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學業,現在正在老家做著一份朝九晚五的普通工作。然而,維持生活正常運轉需要意誌力,因為精力太低,每一項活動的能耗對她來說都相當顯著。

因為精力太低,每一項活動的消耗都很顯著/圖源:【我們是大人】劇照
洗澡的啟動困難只是冰山一角,對學業和工作的追求早已令她疲憊不堪。「我未來該如何發展」「做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之類的問題,無時無刻不在腦海盤桓。為了給自己測試解惑,對抗失控感,她碩士畢業後又修讀了倫敦占星學院的塔羅課程。
椰子把「低精力」概括成一種面對同等的生活工作壓力,要比多數人完成任務更費力、更渴望休息的狀態。超低精力者面臨著個人福祉和潛力發展持續受損的風險,卻很難在器質層面得到診斷和幹預,大眾也普遍將能量不足或慢性疲勞歸因於個人。事實上,在超額勞動時長、過剩的資訊刺激、主流標準的驅動要求下,「低精力」不過是社會病癥反映在個體上的一種表現形式。
椰子在身心的一次次磨損中,看見並具體化自己的感受,嘗試透過反思和記錄改變系統性故障的生活。她的目標是「在最敷衍的努力下做出最多的事,或者做高能量人裏最擺爛的那一個」,以下依據她的講述整理而成。
有多少人做得到「餓了就吃」呢?
我發現了一個規律,某天上午如果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並不抵觸,但無法專註,做兩分鐘就堅持不下去,原因大概率是——我餓了,是饑餓在動搖我的神誌。
這聽起來很天方夜譚,但超低精力者常常意識不到自己餓了,我們對生活缺乏實感,時常需要透過現象邏輯反推,才能發現自己其實已經餓了、冷了、病了……
我把這種「徹悟」發到網上,新訊息提醒接連不斷地跳出來:「我很難分辨自己餓不餓,因為一直是又蔫又累的狀態,也就無法感知在這個基礎上更精細的體感變化。」「當你感覺餓的時候,還有可能是渴,喝的到嘴邊就知道了,只能喝下一口就是餓,這個時候要吃東西。」

【異國日記】劇照
某種程度上,吃飯、睡覺的日常像是西西弗斯的大型推石頭活動,低能量的人被一些難以言明的「更重要的事」召喚,似乎在期待一種奇跡發生:我可以成為超人,跳過這些無用無聊的重復,只要足夠忽略日常需求,我就沒有需求。
在嚴絲合縫的現代生活裏,最基本的動物性會被忽略,我常感到懵懵的、麻麻的,好像自己沒有形體,只是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一種難以消化的情緒,仿佛我不是一團有意識的肉,而是肉的意識本身。
這種體驗可能要回溯到學生時代,我們從小攀爬應試教育的階梯,父母在養育中更重視頭腦,我會覺得關註軀體的感受好矯情,直到成年後我才發現我對塵蟎、乳糖等很多東西過敏,還有鼻炎。不被在意的「不舒服」都在靜默地消耗體能,只要體內有炎癥反應,我一定會拖延、睡不醒。
校園的規範也是如此,我們坐在教室裏接收書本知識,進行抽象的思考,很少接觸戶外,和風雨、陽光、土壤等自然實體的連線愈發微弱,在恐懼驅動下犧牲閑暇和睡眠時間學習做題,以兌換競爭排名裏靠前的位置,能量在這個評價體系中慢慢耗散。

能量在嚴格的評價體系中也會慢慢耗散/圖源:【兔子暴力】劇照
我考上了北京一所重點高校,精英主義傾向帶來了巨大的同輩競爭壓力。大三、大四是我身體機能崩盤的分水嶺,日常的上課、進食都變得比較困難,讓我意識到我的精力水平遠低於常人。在朋友們陸續收到清北牛劍的offer,擁有目之所及高遠發展空間的時刻,我最大的煩惱卻是該怎麽勸自己把衣服送進洗衣機,然後在洗完後把它們收回來,我每天就在這樣的落差和對比中打轉。
我的大腦會自動拆分一切日常基礎行為,比如朋友問我去不去吃火鍋,這件事要分成至少四個步驟:出門,需要換衣服拿東西,好累;交通,需要掏手機查導航,好累;進店,要點菜,好累;開始吃火鍋,判斷熟沒熟、撈肉、咀嚼、跟別人說話,都好累,假如恰巧坐在菜邊,還得給大家下菜,好累!最終我得出結論:不去。
我懷疑自己生病了,於是勉力打起精神,斷斷續續地體檢和看病,有的時候掛了號但起不來床,下午才到醫院檢查,醫生告訴我抽血需要在早上,我交了費卻再也沒有力氣行動,拖了很長時間。

【生而為人】劇照
能查的我幾乎都查了一遍,包括求助傳統醫學,去中醫院治未病;去營養科查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相關指標,排除甲亢、甲減的可能;因為「腦—腸軸」的關聯近年已被證實,腸道菌群狀態與大腦認知活動相互影響,去消化科查腸道功能紊亂……情緒低落是年輕人的常態,我身邊有一些抑郁和雙相障礙的朋友,我也掛了精神科做問卷,沒有達到確診的界限。
去醫院,其實也有點想「偷懶」的心情——我吃點什麽藥,或者補充我所缺乏的某些元素,會不會就好起來了?但得到明確診療方向的願望落空了。
人是目的
我的能量最低谷出現在國外留學那年。封控導致大部份課程轉到線上,我同時還在律所實習,修改一些對外部世界沒有絲毫作用的合約,時間被全部排滿。
我總在冬令時的太陽下午三四點落下時,才能意識到我今天又錯過了最後一縷光照。我揪著自己的頭發試圖把期末論文寫完,突然全身原因不明地劇痛,35歲的不確定性瞬間變得遙遠了,能不能活到明天才是真正的問題。
弗洛姆認為,異化中的人與自身的關系是「交易傾向」。他的價值觀念取決於他的成功與否:能否把自己賣個好價錢。他的肉體、他的頭腦、他的靈魂就是他的資本,他生活的任務便是有利地投資,靠自己獲利,所以他瘋狂學習時間管理、修正自己的拖延癥、每日攝入咖啡、向精英的標準看齊。
弗洛姆認為,異化中的人與自身的關系是「交易傾向」/圖源:【橫道世之介】劇照
我自我異化最嚴重的時候對「聰明藥」十分心動,那是一類可以改善認知表現的管制藥品,能讓人短時記憶力特別好從而考前抱佛腳,或者變得非常專註以完成論文。開藥需要ADHD、發作性睡病等處方,我想透過非法渠道搞一點過來。
嘗試用藥前我查閱了大量論文,絕大部份文獻追蹤統計的學生用藥後GPA並不會提升,反倒是擅自用藥可能會導致猝死、精神障礙和心臟問題等等。
雖然我最終沒有嘗試,但回想起來十分後怕:制止我的絕對不是藥物濫用的副作用,而是我覺得這藥不夠「有效」。好像學業和工作表現成為了絕對至高無上的利益,人的身體本身卻是可以輕易被犧牲的,996的勞動節奏已經傾向於把人當作耗材了,人還要再度自我耗材化。
自我剝削會形成一種長期慣性。心理咨詢師韋亦然分析過,被困在耗竭中的人就像一台充不進電的手機,每天都低能量維生,很多人會說:「我有休息啊,為什麽還好不起來呢?」
從這種問法就能窺見潛在問題:這種「休息」是很有目的性的,我們常常覺得自己「跟不上」「做得不夠」,從而過度努力。當我們最終允許自己休息時,往往已在崩潰邊緣,不得已而為之。這時候,潛意識會捕捉那種「休息是為了趕快回到工作」的心思,因此即使在休息,我們也並不完全放松和快樂。

即使在休息,也沒辦法完全放松和快樂/圖源:【我破碎的真理子】劇照
電池進入維修狀態,休息一天可能只能回20%的電,如果看到稍微有電,就馬上重新投入工作,狠狠消耗,那麽可以預見這樣的低能量迴圈會持續很久。
精力耗竭的人就像已經被過度耕種的土地,它的問題不是運用得不合理不充分,而是已經沒有原料和營養了。此時睡眠、飲食、生理狀況都非常糟糕,再自我加壓就像在過分開墾的土地上亂刨一樣,出不了更多結果。
長期以來我都在把自己作為代價,換取足夠好的成果,從申請學校寫個人陳述,到面試自我介紹,無一不是將自己設計成一套故事和符號,來匹配外部評價體系的要求。甚至連社交也是功利的,會下意識地依據學歷、職業、文化消費品味等等,計算自己和他人在鄙視鏈裏的位置。
畢業後我回了國,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我一邊打零工,一邊寄居在不同城市朋友家的沙發。我不想再參與一線城市那種,24小時隨時隨地都可能收到一個微信語音方陣的高壓高效的生活了。人真的需要一份工作才能得到自我實作嗎?

【二十不惑】劇照
曾經我極度關註意義,看了電影、聽了音樂會進行反思,對宏大敘事、理念性的抽象問題感興趣。比如偏愛3A遊戲大作,去體驗成為一個英雄拯救世界的愛恨情仇,但這套故事也都暗含了一直以來我所順應的教育方式和評價體系,就是我要走上人生巔峰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低精力的生理現狀讓我開始消解這些敘事,甚至有了嚴重的「電子陽痿」。我轉而關註現實世界裏更有可操作性的東西,比如說我餓了嗎?我今天冷嗎?我怎樣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然後再談其他。藉由具體的細節增強可控感,現在我對玄學的熱情也大大消退了。
掙脫敘事之後
我以「低能量人走向高能量」的名義,在社交媒體重新梳理生活。比如我開始用日程表監測每一天,洞察我的精力都流向了哪裏。很多人「自律」的方式,是用無數待辦事項塞滿每一天以感到充實,然後深夜啜泣為什麽完成不了。我們低能量人不搞這些,我會記錄自己做了什麽而不是計劃要做什麽。
這樣我的「崩潰時間」就會自然而然顯現出來,低能量狀態裏看似毫無緣由的崩潰其實都事出有因,刷手機停不下來不是因為真的想玩或者攝入新知,而是因為提不起一絲精力去樓下便利店甚至外賣軟件裏挑點吃的。記錄是中性的,監測它們發生,然後回溯原因,這相當於把過去雜亂的線頭理順,使之不會跟新的線頭纏結在一起。
將不確定性盡量排除也很重要,過度思慮就像後台持續執行嗡嗡作響的程式,關閉的辦法就是寫下來,包括截止時間、生活瑣事、情緒毛邊,從而收獲一個空空如也的嶄新腦子。

冬令時日落時分,海鷗飛到窗前,也許去碼頭整點薯條才是正經事/受訪者供圖
一旦生活最低限度執行的框架立起來,就能發現框架之下存在很多空間,這個空間裏才是真正的自由。在此之前,我所謂的自由時間都在刷手機或身心不良的內耗中度過。
此後,可以抱著「叠代」的心態從最微小的行動做起,如果沒有體力出門可以選擇宅家,只是在有陽光時出門取個快遞看看天空,毆打一下路邊的小花小草。
再進一步,可以以「生命體征維持餐」的邏輯,動用最少精力最快滿足最低社交量。生理疲憊和情緒低落交織,會觸發社交回避。我知道每個需要牽動肌肉做出的笑容、撕扯喉部發出的聲響,都讓人只想找個角落的紙箱縮起來,但孤獨就像饑餓,人際互動匱乏到某個程度,社交排斥又會觸發「社交疼痛」,這在大腦中引起的反應跟身體疼痛相似。
我用次數來量化社交程度,從深到淺簡陋地分類,「靈魂共鳴」像非剛需的米其林大餐,每個人都渴望但不要企圖控制它;有一定主題的逛街、爬山等典型社交,不管事到臨頭多想放鴿子,我都會以至少一周一次的頻率強制自己完成;還有「搭子」式的非正式友誼、同事在茶水間的弱關系社交、組會和工作交接等事務性溝通,都可以視為補足的選項。

和同事的社交也能夠補足一些社交量/圖源:【重新開機人生】劇照
重建附近更是一種本真而純粹的連線,我積累了一些開啟互動的辦法,比如找社區咖啡店老板這種固定的人聊聊生意誇誇出品,或者眼神釘選掃街的攝影師、釣魚的老大爺,由他們的行為發起對話,如果實在不行,跟周圍片區的小貓、小狗混熟,效果也是一樣的。
「低能量」的話題出乎意料地被關註,我觀察了我的關註者列表,有相當一部份人的昵稱後加了括弧,標註自己是「考公版」「考研版」,還有畫師等自由職業者,以及很多留學生。
大家身上有一定的共性,一是沒有天然的外部框架規範形成相對穩定的作息規律,二是在社會網絡中還沒有一個「位置」,缺乏跟他人的互動。他們長期的生活環境通常是一個房間,鮮少去戶外活動,而且他人很大程度上也不理解你為什麽會為「低能量」的事情這麽痛苦,覺得你可能只是懶惰而已,努力、意力堅強一點就能支棱起來。
我反而認為,如果為了獲得更好的學業事業表現才去設法改善低精力,其實是陷入了一種沖突,因為造成你低能量的癥結恰恰在於外部對你的不合理期望,當你拋棄這套體系後,改善之路才會更加順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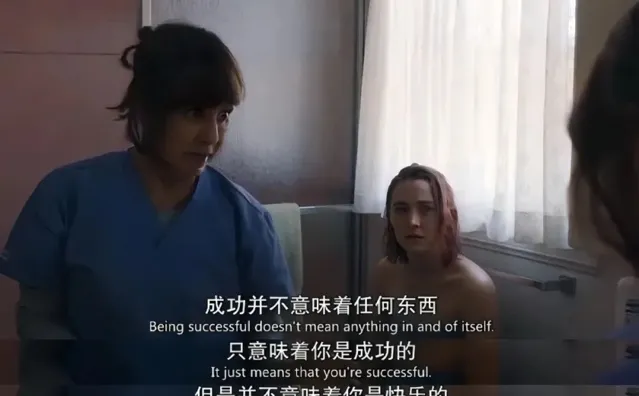
當你拋棄這套體系後,改善之路才會更加順暢/圖源:【布特小姐】截圖
我有精神狀態非常「抽象」「陰暗爬行」的時期,瓦解掉很多嚴肅事情的權威性之後,人會希望找點樂子,或者莫名其妙發生一點混亂。這也許是在發揮能動性,創造出一個項飆所說的和系統有一定距離的「橫向反思空間」,讓真實意識和現實處境有所區隔。
有段時間,我和混跡亞文化圈的朋友一起,在藝術館打麻將,因為錯過列車而鉆復雜的空子逃票登上下一趟車,還總在臨時起意嘗試用各種稀奇古怪的辦法入侵全市最高的大樓。
出於安全管理,前往頂樓需要繞過門禁、保安,我記得天台有一截鋼制的腳手架垂下來,我們要助跑一段、起跳,沿著一段方形通道爬上去,整座城市的夜景在我們腳下展開,就像電影裏一樣,那一刻仿佛完成了某種誌願。
10月份我和朋友去了貢嘎雪山轉山,4天走了近80公裏。天氣非常差,白天一直下雨,夜裏睡帳篷的時候都會擔心今晚的雪會不會把帳篷壓塌。
出發前,高寒山區高體能消耗的預期嚴重地觸發了我的焦慮,但真的去了,我發現自己比想象的還要有力。畢竟這世界上的很多事,就像轉山一樣,只要一直走,就能走完。
文中配圖部份來源於網絡,首圖插畫來源於Chessy
本文正選於【南風窗】雜誌第25期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祖曉謙
編輯 | 董可馨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