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訪談作為我們了解作家寫作意圖、解析作品的重要形式之一,其是否令參與者和讀者都有所收獲,往往取決於對談雙方的「業務水平」。它要求采訪者對作家的寫作生涯和作品內容了然於心,也需要作家對來訪者給予足夠的信任和坦誠,在對話中保持專註。而若是采訪者同樣是一名作家,對談雙方在互相引導與配合下,在話語跌宕中生成新的脈絡,那麽對談一定是精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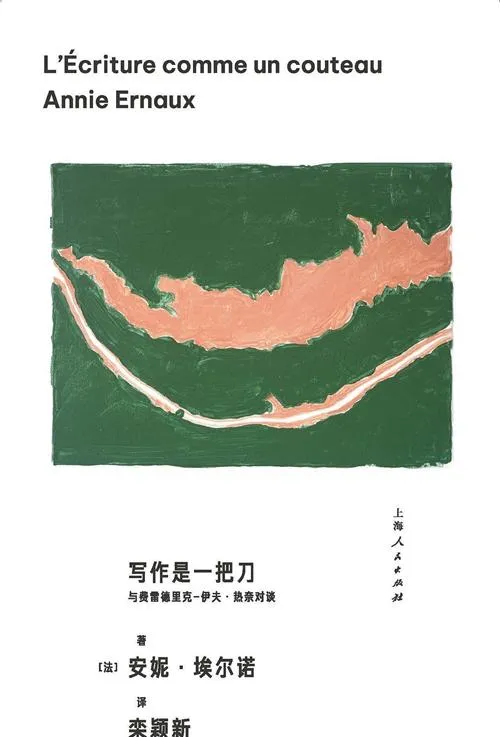
對談集【寫作是一把刀】便是由兩位作家共同完成,作為采訪者的菲德烈-伊夫·熱奈出生在法國,後來移居墨西哥,同時在墨西哥教授文學。安妮·埃爾諾無需贅述,她已憑借2022年的諾獎得主身份被全球讀者所知。
需要留意的是,兩人的對談發生在2001年到2002年之間,透過信件完成。20年前,安妮·埃爾諾並不像現在這麽知名,她是一位遊走在出版圈邊緣的作家,正嘗試著使用來自平民階層的語言,大膽披露自身經歷,以模糊虛構和真實的界限,跳脫出小說甚至文學圈所定義的作品開辟天地。可想而知,她受到了正統出版圈和許多以男性為主的評論家的詆毀。
菲德烈-伊夫·熱奈和安妮·埃爾諾的對談大多圍繞這些爭議展開,他們談到對寫作形式的看法、身為女性的創作經歷、成為作家之前的閱讀經歷,以及寫作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等等。安妮·埃爾諾對這些話題的回應都踐行了她是如何成為這樣一位獨特的創作者。她不認可人們在談論書籍時用標簽和類別進行分類,覺得它們「根本不重要」。一如她在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裏,從以自己情感生活為藍本的早期作品,到直接將父輩的生活如實還原的【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似乎沒有人可以將她的這些作品用經常熟知的「小說」「非虛構」」回憶錄」等標簽來定義。
安妮·埃爾諾
在談到女性寫作的話題時,安妮·埃爾諾的回應更加犀利,她直言自己不喜歡出現在「女性寫作」的那一欄,因為也不存在一種叫「男性寫作」的文學分野。針對一些男性評論家和讀者對自己在作品裏提到性、墮胎、出軌等情節時所表達的不適,安妮·埃爾諾指出了這種不適背後的根源,「我們都被思維定式支配,被在歷史中建構出來的文化想象支配。這種思維定式和想象給男性和女性賦予了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說話方式」。
公眾場合的色情笑話,對女性外貌近乎騷擾般的點評,一直以來,大方地談論性幾乎被預設為男性的權利,而女性對此只能保持沈默或羞恥。這種性別文化正是安妮·埃爾諾所提到的:我們被賦予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說話方式。即便在當下,女性主義之下的女性寫作正成為一種潮流,獨立自主的女性角色正受到追捧,撇開消費主義對這種現象的推動,只要在任何文本裏還能看到「女作家」「處女作」之類的字眼,安妮·埃爾諾所提到的根源就尚未被打破。
論及政治,身為左派的安妮·埃爾諾將寫作視為一種參與政治的行為,她反對那種視文學為純粹的審美意義上的活動,應該被束之高閣、與世無爭的觀點。即便這種觀點在作家和讀者身上都普遍被認可。她也確實在作品裏討論法國社會的階級問題,歷史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她不再看重寫作技巧和形式,也是對這種審美意義上的愉悅表示拒絕。
林林總總,這部對談集所呈現出來的安妮·埃爾諾有著十足的「反叛者形象」,「寫作是一把刀」極為形象地指明了她的作品和觀念是如何鋒利地劃開了正統文學的「假面」。有趣的是,在這場對談過後的二十來年,安妮·埃爾諾成為了諾獎得主。一位邊緣的、受到爭議的作家最終得到認可,她用自身的「戰鬥經驗」為「文學是什麽」這個問題給出了更多帶有啟發性的回答。
波赫士
受到爭議的作家在文學史上並不少見,擅長書寫老虎、鏡子和迷宮等文學元素的波赫士就曾因自己在政治上的言論被公眾批評。論及寫作,在拉美文學的版圖裏,波赫士也稱得上是「異類」。他不像其他拉美作家那樣,排著隊從成長的土地裏澆種一種名為「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他筆下的世界時常脫離這片土地,抵達亞洲、歐洲等異域,尤其考慮到創作盛年的他已經雙眼失明,這種寫作反而變得更加讓人驚異。
比波赫士年紀小近四十歲,在拉美文學中同樣地位頗高的馬利奧·巴爾加斯·略薩對這位前輩也產生過觀念上的轉變。收錄在【略薩談波赫士】裏的那篇【波赫士的虛構】,略薩提到求學期間自己瘋狂迷戀薩特之類的知識分子,堅信「寫作即行動」。至於波赫士,這種「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藝術家」恰恰是略薩所憎惡的。然而在讀過波赫士的作品後,略薩寫到,「我感到眼花繚亂,心中還生出了邪惡的快感,我覺得自己仿佛犯了通奸罪,背叛了導師薩特」。
作家的「真香時刻」降臨了,在【波赫士的虛構】的余下部份,略薩幾乎全方位地捍衛了波赫士的才華和地位。這本書也收錄了略薩和波赫士在不同場合下的對談。誠如略薩所說,波赫士謙虛且來者不拒,像那些來自世界各地懷揣敬仰的人一樣,略薩也造訪了波赫士的家——一個兩居室的公寓。公寓的墻上掛著陶瓷老虎,放著行軍床的臥室像一間牢房,略薩對這間公寓的描述似乎讓讀者預見了一個清教徒般的屋主。在【氣球之旅】一文中,談到波赫士的情感生活,略薩的一段描述也正好回應了這種「清教徒」的形象,「如果說愛情曾經在那裏出現過的話,那也只是文學之愛、思想之愛,而且幾乎總是無性之愛」。
一旦走進作家生活的地方,對談難免會沾染日常生活的余光。不同於【寫作是一把刀】,略薩和波赫士的對話更像是兩個熟人之間的交談,想要從其中尋找一些嚴肅的見解,或者整理出幾段可以傳頌的金句,恐怕得空手而返——
略薩:可您讀過不少長篇小說,同時還是長篇小說的優秀譯者。
波赫士:不,不。我讀的長篇小說並不多。
……
諸如此類的對話聽上去似乎沒什麽意思,但只要聯想到,它們發生的場景是布宜諾斯伊利斯市中心的一個老舊公寓,身邊有一只名叫「貝波」的公貓和一位女傭來回走動,這些又都順理成章了。想象自己是一個坐在他們身旁的熟人,或許是融入這場聊天的最佳方式。
深入作家的生活,完成一次長達二十年的對談,聽起來似乎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它發生在兩名瑞士作家勞勃·瓦爾澤和卡爾·澤利希之間。
卡爾·澤利希鏡頭下的勞勃·瓦爾澤
1936年,卡爾·澤利希拜訪了住在療養院的勞勃·瓦爾澤,後者在這裏居住多年。在卡爾·澤利希的第一印象中,這位年近六十的作家有著「一張孩子般的圓臉」,他出版過小說和散文集,但因為各種原因不受待見,卡爾·澤利希將其總結為,「對文學小圈子的疏遠導致他在經濟上嚴重受損。但到處盛行的偶像崇拜簡直讓他惡心」。
意識到「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瓦爾澤作為被世界遺忘的作家,在療養院開始了身為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而卡爾·澤利希的到訪恰恰是想要讓他重新被世人重視。從1936年初次見面,兩人一次次踏上外出散步的旅途,在用雙腳丈量土地的同時,瓦爾澤關於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關於文學和政治觀點的話語被記錄下來,組譯成這本【與瓦爾澤散步】。
在散步中對話是一種更為放松、也時刻充滿驚喜的形式,尤其對於瓦爾澤這樣一位在職業生涯中飽受挫敗,主動選擇與世隔絕,「像被砍倒的樹一直躺著」的作家來說,路途中變幻的風景是開啟他塵封已久的內心世界最合適的鑰匙。
事實上,在對每次外出散步的記錄裏,除了瓦爾澤對世界和自我接近自然主義般不變的態度——「我喜歡世界本來的樣子,喜歡它所有優點和缺點」,「我想和人們生活在一起,並消失在他們當中」,最有趣的部份恰恰是散步中被記錄下的美食。一杯酒或咖啡,一份有麵包、牛奶的早餐或一份帶菜豆和煎肉排的午餐,往往是這一天路途裏身體和精神疲憊的安撫劑,終於,在行走和對話中不斷觸及的世界可以暫時從飯桌上遠去,讓旅人和他們的觀眾都享受這份散步中的「留白」。
1956年12月25日,獨自外出散步的瓦爾澤被發現倒在雪坡上,死因是心臟病。這場持續二十年的對談結束,成為瓦爾澤生命最後的唯一實錄,為後來人重新認清這位作家的價值起到了關鍵作用。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