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论道德谱系】
尼采之英雄道德

对尼采而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像一部福音书,因此,在他后来的著作仅仅扮演着评论者的角色。
如果欧洲不欣赏尼采的诗歌,也许,它会理解尼采的散文。
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歌声远去,先知变身为哲学家,把玩起逻辑学。
我们这位哲学家虽然怀疑逻辑,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逻辑学不能使论证牢不可破,它至少能使论证更为明白清晰。
尼采从未感到如此寂寞,连他的朋友们都觉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古怪。
曾与尼采在巴塞尔共事的奥韦尔贝克和布尔克哈特等学者对【悲剧的诞生】赞赏有加,但此时,他们不得不悲叹,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已经没落,而要他们为一位诗人的诞生喝彩,他们做不到。
尼采的妹妹(她差点儿就佐证了尼采的观点:对于一位没有妻子的哲学家来说,姐妹可以很好地扮演妻子的角色)突然离他而去,要去嫁给一位尼采极度鄙视的反犹太分子,然后,再去巴拉圭建立一块共产主义殖民地。
考虑到兄长的健康,她恳求羸弱的尼采一同前往。
但是,比起健康的身体,尼采更珍重自己的心灵,他希望留在战斗打响的地方,对他来说,欧洲是一家必不可少的「文化博物馆」"。
从此,尼采居无定所,不时地四处迁移,先后在瑞士、威尼斯、热那亚、尼斯、都灵生活。
在圣马可广场的狮子周围,经常有鸽子聚集,尼采就喜欢在鸽子堆里写作——「圣马可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
然而,他不得不听从哈姆雷特的建议:勿站在太阳底下,因为阳光会刺伤他患病的眼睛。
于是,尼采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昏暗、肮脏、寒冷的阁楼里。
在紧闭的窗前奋笔疾书。
由于眼疾,尼采不再著书立说,写下的只是一些格言警句。
他将自己的部分零散感悟收集起来,集成了两部书:【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
他希望能在书中毁灭旧有道德,为超人的道德铺平道路。
有一阵子,尼采重新做回一名语言学家,力求以那并非无可挑剔的词源学来推广他的新伦理。
他发现,在德语中,有两个词表示「不好」,一个是 schlecht,另一个是bose。
Schlecht用在上级对下级的语境中,表示「平庸的、一般的」,后来演变为「粗鄙的、没用的、不好的」。
Bose用在下级对上级的语境中,表示「不熟悉的、不规则的、不可估量的、危险的、有害的、残忍的」,比如说,拿破仑很bose。
许多原始的民族都害怕杰出的人,把这些人看作分裂分子,中国便有这么一句俗语:「伟人乃公众之不幸。」
类似的,gut也有两种含义,分别与schlecht和bose相反:一种含义为贵族使用,表示「强大的,勇敢的、有权的、好战的,神圣的」(gut一词来源于Gott,神),另一种含义为平民使用,表示「熟悉的、和平的、无害的、善良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相互对立的对人类行为的价值评判、两种伦理观念和标准,即「贵族道德」和「庶民道德」—— 一种是主人的道德,一种是奴隶的道德。
贵族道德是古典时代【大致来说,古典时代始于公元前7世纪,经历基督教的崛起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5世记),直至古典文化的消解。从地理位置看,是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公认的道德标准,尤其对罗马人而言。
在罗马人(哪怕是一个普通民众)看来,所谓的美德便是男人气概、勇气、冒险和胆量。
但在亚洲,尤其是在犹太人的脑海中,却孕育了另一种道德标准:遭受政治压迫的人们变得谦逊、无助、无私。
实际上,这是在求助。
在庶民道德的笼罩下,人们热爱安定与和平,厌恶冒险和权力、人们不再追求力量,他们乐于狡诈,人与人之间的报复不再公开,而是变得隐秘;怜悯代替了严厉,模仿代替了创新,人们不再因享有殊荣而自豪,而是无情地谴责自己的良心,因为荣誉只属于异教徒、罗马人、封建主和贵族,良心才属于犹太人,基督徒、资产阶级和大众。
从阿摩司到耶稣,一大批能说会道的先知将奴隶阶层的思想发扬光大,使之几乎成为普世伦理观。
于是,「俗世」和「肉体」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贫穷成了道德的象征。
而耶稣则将这种价值标准推至顶峰。
在他看来,人人都拥有平等的价值,享有平等的权利。
后来,耶稣的教义又发展出民主思想,功利主义、社会主义。
于是,人们开始根据庶民哲学、渐进的平等化和庸俗化、颓废和堕落的生活来定义进步。
颓废生活的最后一幕便是对怜悯慈悲、自我牺牲的赞美,对罪大恶极者不理性的安慰,以及「人类社会排泄功能的丧失」。
积极的同情是可取的,而怜悯则是一种麻痹心灵的奢侈品,对那些无可救药、昏庸无能、穷凶极恶的废物,那些满是缺陷、活该害病、违法犯罪的畜生来说,怜悯则是浪费感情。
怜悯隐含着粗俗,是一种侵犯,比如,「‘探望病人’是想到邻居无助之时,心生的一种类似性高潮的优越感」。
这一切「道德」的背后是一种隐秘的权力意志。
爱是对占有的渴望,求爱是一场战斗,交媾则是战斗后的控制。
也难怪唐荷西要杀了卡门,那是为了防止她成为他人的所有物。
「人们以为自己在爱情中是无私的,那是因为他们想从他人身上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往往是从他自己身上无法得到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便会要求占有对方……【省略号之后为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的话,原文为法语。其实,尼采曾更为委婉地谈论爱情,他说:「男人会在何时对女人进发激情?……最低等的激情来自纯粹的色欲,但当一个男人深感脆弱、需要帮助,情绪高涨时,灵魂会像决堤的河流,啃噬他。同时,他会产生被抚摸、被侵犯的感觉。伟大爱情的源泉便在这一刻喷发。」(【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287页。)尼采还引用谚语说:「‘真爱中,拥抱肉体的是灵魂‘,这是我听过的最为纯洁的话。」】在所有的人类情感中,爱情是最自私的,所以,受伤时,爱情最不宽容。」
即便是爱真理,也只是出于占有真理的渴望,或许,爱真理者只想开垦一片处女地,成为第一个占有真理的人。
而谦卑是权力意志的保护色。
在权力意志面前,理智和道德便成为绝望之物,因为它们只是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武器。
「哲学体系是一座华丽的海市蜃楼」,我们看到的并非我们长久寻找的,而只是我们自身欲望的反映。
「所有的哲学家都会摆出一副姿态、好像他们的思想都是通过冷峻、纯粹、神圣且不偏不倚的辩证法得来的……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只是片面的主张,想法或‘建议’,它们基本上是被抽象、提炼出来的哲学家心中的欲望,事后,他们便会搜集种种论点来为自己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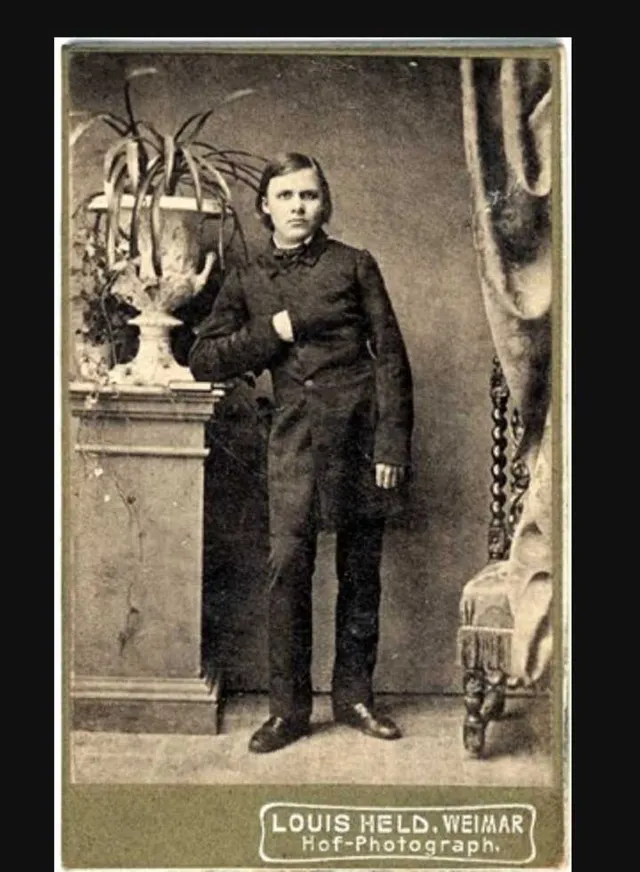
且,决定我们思想的便是这些埋藏在最底层的欲望、这些权力意志的悸动。
"更多的时候,人类既无法意识到,也无法感受到自己的智力活动……有意识的思考………是人类最微弱的智力活动。」
本能是权力意志最直接的动作,它不受意识的干扰,因此,「本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富智力的活动」。
确实,意识的作用被糊里糊涂地高估了,「意识或许应该被放在第二位,它几乎可以说是次要的、多余的。也许,意识注定要消失,注定要被完全的自动化取代」。
强者不会用理性的外衣来掩饰内心的欲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即「我要」。
对那些充满活力、未受腐蚀、拥有主人翁精神的灵魂来说,欲望因其本身而正当地存在,而良心、怜悯或悔恨绝无立锥之地。
但如今,犹太教、基督教民主思想风行于世,使得强者们羞于承认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健壮的身体,他们开始为自己寻找「理由」。
贵族的美德和价值标准正在慢慢消失。
「欧洲正在受到新佛教的威胁」,连叔本华和瓦格纳都皈依了佛教,成为可怜的佛教徒。
「欧洲整个道德体系的建立是以一种对大众有用的价值为基础的。」
强者不得施展强大的力量,他们必须尽可能表现得如弱者一样,因为「勿做我们力量范围之外的事,便是善」,康德,这位「柯尼斯堡的伟大中国佬」不也证明,人类绝不能被当作手段吗?于是,强者的本能——打猎、战斗、征服和统治,由于缺乏宣泄的渠道,逐渐演变成自我伤害,并进而产生禁欲主义和「歹心」。
「一切本能,如果找不到一个排解通道,便会向内深入——这就是人类那不断发展的‘内向化’:于是,我们便有了被称之为灵魂的最初形式。」
堕落的原理是这样的:领袖们受到大众美德的影响,并被大众美德庸俗化。
因此,「第一要务便是迫使道德体系服从等级秩序,并对各种道德假设重新进行考查,直至人们彻底认识到,说出‘适合你的也适合他’这样的话是不道德的"。
不一样的特点会产生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在社会中,强者那「罪恶」的品德与弱者那「美好」的品德都不可或缺。
苦难、暴力、危险、战争,与善良、和平有同等的价值。
众所周知,伟大的人物只会在充满危险暴力的环境中、在迫使人变得残酷时才诞生。
对人来说,最好的东西便是强大的意志、权力以及无限的激情。
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就像一块豆腐,终将一事无成。
贪婪、嫉妒甚至仇恨都是斗争、选择、生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恶之于善,相当于变异之于遗传、创新和试验之于风俗习惯。
如果,如果永不用近乎犯罪的手段冲击一下现有的「秩序」,哪里有进步可言?如果恶真的不好,那它早已不复存在。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自己,不要过于善良,因为「人类必然变得越来越善,又越来越恶」。
发现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罪恶、如此多残酷的事情,尼采深感欣慰。
他认为,「残忍构成了古人极大的喜悦和快乐」,一想到这一点,尼采便感到虐待狂般的愉悦。
他相信,我们从悲剧中,或者从任何崇高的事物中获得的快乐都是一种经过提炼的间接的残忍。
「人类是最残酷的动物,」查拉图斯特拉说,「欣赏悲剧的时候、观看斗牛的时候、旁观刑罚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人间未曾有过的快乐。然后,人类创造了地狱……瞧,地狱就是他的人间天堂。」
如今,想想自己的压迫者在另一个世界接受永久的惩罚,人类便能忍受一切苦难了。
终极的伦理学是生物学层面的,我们评判事物的依据应该是该事物对生命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从生理学的角度「重估一切价值」。
而真正能考验一个人、一个种群、一个物种的是活力、能力和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或许能够接受十九世纪(不然,一切高尚的美德便会遭到毁灭),因为在十九世纪,肉体得到人们的重视。
灵魂是有机体的功能之一。
人类大脑中的血,多一滴或少一滴,都会给人带来无限痛楚,这种痛楚远远超过被鹰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所忍受的痛苦。
不同的食物催生不同的思想方法,比如,米饭推动佛教的形成,而德国的形而上学则是畅饮啤酒的结果。
因此,一种哲学是真理还是谬论,完全取决于该哲学赞美的是人生的升华还是人生的堕落。
堕落者说,「人生毫无价值」,其实,还不如让他说「我毫无价值」。
当人生中一切崇高的价值开始腐烂,当民主--即对一切伟人的质疑——每十个年头毁灭一个民族,人生为何还值得过活?
现今,热爱交际的欧洲人总喜欢摆出傲人的架势,仿佛他们才是唯一获得认可的种族。
他们对自己的品质,比如公德心、慈善、尊重他人、勤奋、节制、谦逊、宽容、同情心等,大加赞美、并视这些品质为人类特有的美德。
在这些美德的作用下,他们在普通大众面前彬彬有礼、隐忍不言,显得极有用处。
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人们认为领袖或领头羊确不可少时,他们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召集大批聪明的善于交际的人,来代替发号施令的指挥官,各种议会机构便源于此。
然而,要是果真有一位专断独裁者出现,来管理这些善于社交的欧洲人、那也是上天的一种祝福,好似一块巨大的磐石被卸去——拿破仑出现后的一系列影响便是最好的明证:一部受拿破仑影响的世界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追求高尚幸福的历史。
因为,通过一个个伟大的个人、一个个伟大的时期,这种高尚的幸福横跨了整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