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大致是,預期一些戰鬥任務會付出空前的傷亡的情況下,究竟派哪一支部隊上陣,來承擔這樣的「炮灰」任務。這是一個好問題。我不想陷入現代軍事組織與決策的許多細節。我們來講講以前的事情。
下文中,我會先介紹一下古代世界中一種常見的情形。然後,我想來集中討論一下幾種有趣的「炮灰」選擇方法,時段都幾種在晚唐五代北宋初的一個世紀間。我們會看到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文化在這個時候已經形成了,而炮灰的選擇實際上也反映著宏闊的社會與觀念的變遷——而對此,我們目前的理解依然十分有限。
1
簡單說,在古代,不同的戰鬥單位常常由不同的社會族群構成的。一個可以確定的戰鬥單位其實就是某個地域、某個階層的人群,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作戰技能也相仿。柏拉圖覺得可以讓同性戀的人編成一隊,這樣他們彼此之間相親相愛,自然很有戰鬥力。雖然不現實,卻是西方古典時代非常典型的想法。由此,不同族群的社會身份往往已經決定了其在軍事部署中的位置。如果本身是奴隸、賤民,或者被征服的民族,自然就是用來做「炮灰」的。我們舉兩個中國的例子。睡虎地秦簡中附了一段【魏奔命律】,現在已經很有名了,我直接參照楊寬先生的解讀:
這道命令指出,所有這些身份低下的人以及「率民不作、不治室屋」的人,原來都是要殺的,因為不忍連累他們的同族兄弟沒有殺,現在派遣他們從軍,將軍不必憐惜。在烹牛賞給士兵吃的時候,只賞給他們吃三分之一鬥的飯,不要給肉吃。在攻城的時候,哪裏需要就派用他們到哪裏,將軍可以使用他們平填溝壕。說明這類身份低下的人從軍,如同罪犯一樣屬於懲罰性質,在軍隊中待遇要比一般士兵低一等,在戰鬥中要擔任攻城等艱巨的任務,在行軍或防守中要擔任平填溝壕等較苦的勞役。這是使用身份低下的人群做「炮灰」的例子。更常見的是用被征服的民族。羅馬帝國、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等莫不如此。據說,英格蘭的愛德華一世在面對蘇格蘭軍的時候有句名言,別給我射箭,箭多貴,上威爾斯人,反正他們不要錢。這個思路確實是對的,因為用威爾斯人不僅不要錢,也許還能省錢——當他們的精壯戰死以後,反叛能力也減弱了。來看個更具體的例子:
景德初,契丹大舉擾邊,經胡盧河,逾關南,十月,抵城下。晝夜鼓噪,四面夾攻。旬日,其勢益張,唯擊鼓伐木之聲相聞, 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 。這是1004年,契丹大入邊,後來就有澶淵之盟了。奚是契丹統治下的一個民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有自己的首領。在遼軍的戰鬥序列中也有相當的獨立性。在最艱巨的攻城戰中,顯然由他們承擔先發。由此,不難想象,任何主帥都不會將嫡系部隊投入無謂的消耗。有些部隊具有一些戰鬥力,而其中的人群又桀驁難治——如奚人——那顯然就是炮灰佳選了。
2
有了這樣的背景之後,我們就可以來看幾個也許會有趣的個案。【舊五代史】: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為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 梯頭 ,從簡 多 應募焉,莊宗為其勇,擢領帳前親衞兼步軍都指揮使。古代攻城,雲梯是最便捷的攻具,也最危險。其中最危險的是帶頭爬雲梯的那個人:如果雲梯中途被推下來,他摔最慘;如果僥幸爬上去了,他要獨自面對城墻上好幾個人,可能瞬間就被剁了。重賞之下才有勇夫,這要的炮灰行業當然要重金聘人才好。萇從簡這個人就經常攬這個差事,且不說每次的收入,還受到了唐莊宗的賞識,真是非常幸運了。
雖然只是在說一個人,但是對照遼軍的攻城法,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後唐的戰鬥序列中,沒有誰是活該去送死的。即使你是李存勖,你是戰鬥力最強的男人,你也沒有辦法強迫一隊人,拿著盾牌點著火去爬城墻——你還沒這樣做他們已經造反了。事實上,在那個時候,你拉這些人來築城也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情。如果他們不樂意了也造反了。總之,要想有人拼命,就得多花錢。
3
這是花錢來買炮灰的例子,但人命終究比錢復雜多了。【續資治通鑒長編】有:
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遇 以次 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這是在979年,宋太宗趙光義要攻太原了。一個城是方的,就有四個面,自然要分四隊人來進攻。最先攻進去的那一方,通常功勞最大;最後攻擊去的,多半傷亡更大。於是問題來了:不同方向的城墻,防禦水平是不一樣的。誰來攻哪一面,這相差就很大了。這可以怎麽辦呢?
至少晚唐的時候,武人們就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形成了一種心知肚明的習慣。就是說有一個預設的序列,甲乙丙丁四個主將,按照自己的官銜派個序,一二三四,分別進攻東南西北。既然是約定俗成了,大家也就沒有意見了。抽到了城防度高的那個方向,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這是一種存在在那裏的習俗。用流行的話說,叫預設值,default position。你如果遵守,大家覺得很正常;你也可以選擇不遵守,那你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我為什麽不按老規矩辦。
宋太宗部署攻城部隊的時候,可能沒太在意這種習俗。就發生了上文中的情況。曹翰這個人一看,就提出了反對意見:「我排在劉遇後面啊,他應該去打西面啊!我是去打北面的選手!」這當然是曹翰的托詞。他心裏其實要說的是,「西面城墻、防禦塔等級高啊……我不去。」但借口本身也承載著觀念——在美國可以說,我家狗病了,我不能來上課了,在中國就不行。五代宋初的武將,他們認為誰攻打哪一邊有一定的預設之規。主帥在排兵布陣的時候違反了這種預設之規,自己至少有抗議的權利。於是,宋太宗還有特地去安撫一下他,跟他說:「你多厲害啊,西面只有你能打下來。」
這件小小的事情其實告訴我們很多非常有意義的資訊。首先,沒有哪支部隊就該做炮灰的。各支部隊都是平等的。所以不可能像契丹人驅使奚人那樣。然後,如果戰前將領們總是在那裏挑肥揀瘦的,那還沒打仗自己先吵翻了;所以武人們逐漸有了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案:根據預設的序列,老天決定,童叟無欺。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軍事文化,也可以說是我們國家武人的政治智慧——這樣的智慧在文人主導的歷史書寫中是看不到的。最後,我們還可以看出宋太宗在軍中的權威還是非常有限的。他的部署下達以後,還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4
現在是最後一個例子。【涑水記聞】: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魏府,有兵十余萬。契丹將至,闔城惶遽。欽若與諸將議 探符分守諸門 ,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 請不探符 。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我們現在又回到了1004年的宋遼戰爭。
我們繼續說五代宋初的預設之規。那其實還有一種更加簡便的方法,就是抽簽——以前人稱為「探符」。這最公平了,大家沒有意見。
但對於作戰來說,這是非常不利的。比如,敵人從北面來攻城。守臣的將領抽簽決定誰的部隊來守北墻,結果最弱的那隊抽到了。最強的部隊反而在南墻。結果北墻一下被攻下了,南面的部隊順勢從南門一溜煙走了……本來可以守得住的城也就丟了。所以,這一年,孫全照站出來。他說這樣不好,「你們去選你們愛去的地方,大家都不肯去的地方,我去。」
然而,很多事情是聯系在一起的。孫全照充英雄以後,也許是可以升官發財的,但他手下的人傷亡自然就高了。那就會有一個問題:他手下人不樂意了怎麽辦?現在一個班主任,開年級部會議的時候,還要爭取一下全班先退場,少曬點太陽什麽的,家長會就可以嘚瑟了。武將是帶一隊人去送死的,正常人的做法是和上文曹翰一樣的,為自己手下爭取點好處,防禦塔多的地方咱不去。將領要反其道行之,把最艱巨的任務抗在自己肩上,平時就必須做好基層工作。獲得俸祿賞賜都和他們一起分享,大家之間稱兄道弟。那關鍵時刻,大家才會為了大哥拼一把。所以,說這句話也要有資本的。
同甘共苦,看上去是很平常的武將美德,其實背後說明的也是這樣一個社會事實:對於普通兵士來說,平白無故你沒有權利把更危險的工作交給我。
5
我們討論了三個個案,廣義上都可以說是炮灰選擇的問題,即更危險的戰鬥任務由誰來承擔。我們看到了更好的待遇,我們也看到了訴諸隨機。背後的思路都是一樣的,我們看到了來自武人、兵士層面的一種訴求:要求公平!大熱天的,人家都在乘涼,我們還在修城墻,這還是不公平;都一樣是部隊,他們拿錢多我們拿錢少,這也是不公平;或者,每次炮灰都想到我們,分戰利品都想到別人,這還是不公平……
這種對公平的訴求,在傳統中國,概括起來就是「均」,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不是要求絕對平均的意思,某種意義上在說,作為公平的正義——羅爾斯什麽的真的是太年輕的……對於唐朝人來說……
展開一些的話,我們過去對於晚唐五代兵變的研究,往往關註於事件的性質:到底是遊手好閑的武人貪得無厭要鬧事?還是窮困潦倒的無產階級走投無路訴諸暴力?這種關切固然有意義,但很多時候就是一件說不清的事情。比如甘陽被打了,這到底是飽受壓迫的青椒決絕的發泄,還是對於年邁老人的無恥踐踏。我們現在可以采訪當事人,掌握學術體制的完整的資訊,至少理論上,但要辨析清楚一件事情的性質還是很困難。在古代史中執著於這樣的追問恐怕只能是一個死胡同。這裏我想到的是兩位英國史學家。其一是 E.P. Thompson,他有一個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的概念。簡單說,關於糧價而產生的暴動英國從一種基層的政治文化來理解,就是農民覺得價格應該是這樣的,這是公平合理的,如果超出了這個公平的範圍,那麽我們就有權利拿起武器。在這個問題上做的更深入的是Steven Justice,他有一本書叫 Writing and Rebellion: England in 1381 。他主要的貢獻在於,指出了在1381年英格蘭農民大起義的過程中,農民群體對於自己的權利、國王教會的權力等問題有著非常深入、系統的理解,並且按照他們理解的公平糊正當,從新來運作文書,建立他們的組織。在這樣的視角下,戰鬥序列的編排,戰區的補給,兵變的發生,這些看似不同層面的現象其實都指向著同一個廣闊的問題:處於社會基層乃至邊緣的人群對於公平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的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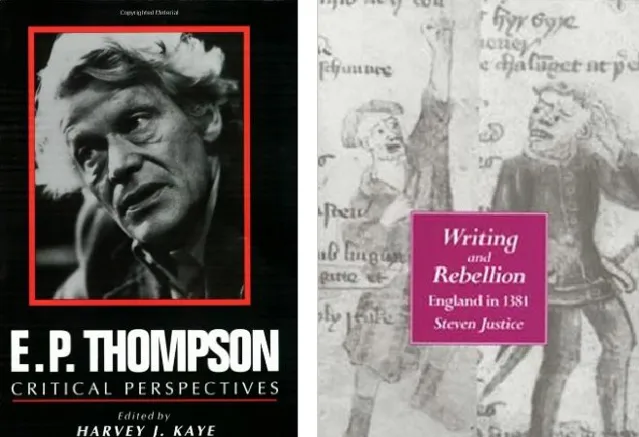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一開始的問題:誰來做炮灰?這在古代世界,相當長的時間,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部隊本身的身份內容已經決定了。只要在社會的中下層有了非常強的公平意識以後,才成為了一個問題。而在實際的戰鬥組織過程中,他們也發展出了不同的機制來實踐這種公平——設定預設值,或者抽簽,等等。有人說,十六世紀前後,英國的紳士們自發的設計了許多規則,成立了很多俱樂部或社會組織,在國家與教會之外做了很多事情,於是現代公民社會開始形成了。那麽,這些武人們自發的規則設計,又應該被放在一幅怎樣的歷史畫卷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