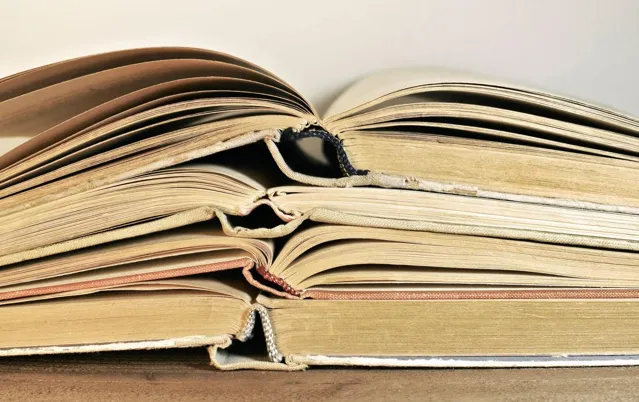
彭國翔/文
駐訪期間的人與事
2012年,在馬普所駐訪期間,除了學術性的聚會之外,大家自然少不了日常的交流。我當時租住在哥廷根東面山坡上一位老太太的房子的頂層,是一個帶陽台的套房,有自己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那個山坡離哥廷根的地標之一「俾斯麥塔」(Bismarckturm)不遠,我散步時也去過幾次,在那裏可以鳥瞰整個哥廷根這座城市。房子二樓是房東老太太自住,一樓的租客則是巫達教授。我和巫教授雖然住在同一幢房子之中,但平時幾乎不串門。見面基本上都是要麽在所裏,要麽就是一起沿著哥廷根的老城墻散步,走一圈恰好大約一小時,或者到外面的餐廳喝啤酒。好像只有一次大家晚上聚餐飲酒之後,已有醉意的巫達和另外兩位所裏的年輕人,應我之邀到我住處閑聊。巫達喜歡飲酒,記得有一次在哥廷根歌劇院旁邊的酒吧裏,他對我說:「喝啤酒要一口氣把一大口喝下去,然後打一個嗝,那才是最舒服的。」他邊說還邊示範,喜氣洋洋地喝下去然後打了一個嗝的樣子,我至今仍有印象。
巫達是大涼山出來的彜族人,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又到澳洲從事過博士後的研究,接受的是地道的人類學訓練。我從他那裏聽到不少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尤其是彜族的故事,大都是以前聞所未聞的。對於拓寬自己的見聞和了解人類學的研究物件和方法,我覺得都有很大的收獲。後來巫達從上海大學調到了中央民族大學,我則從北大調到了浙大,可以說是彼此南北易位。有一次我去北京開會,還在民族大學附近和他及他夫人見面一聚。
巫達兄大概早就知道範筆德教授喜飲酒,就從中國帶去了兩瓶五糧液。我以前並不太知道,西方學者中也不乏喜飲烈酒者,結果那次讓我長了見識。不僅範筆德教授對中國的高度白酒頗有好感,初次見面的丁荷生教授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晚上大家聚餐,那一次好像不是巫達兄帶去的五糧液,而是威士忌,當然還有啤酒。席間丁教授飲了不少,顯然是喝得有些醉意。從餐廳出來之後,他的腳步明顯有些踉蹌,卻堅持說要開車送我們回去。結果除了他的好友鄭振滿教授、巫達兄和我之外,大概還有中間短期去存取的劍橋大學的周越(AdamYuetChau),四個人坐他開的車,一路行駛。也許當時大家都有些微醺,興高采烈之余,有些忘乎所以。幸虧哥廷根不大,最終大家都各自安全回到住處。但事後想起來,難免有些擔心,所以至今記得。那之後不久,丁荷生就從麥吉爾大學轉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了。在他的任期之內,我有一次還收到他以系主任名義發來的信件,就系中某位學者升等的事宜請我幫忙審查。在他擔任系主任之前,我曾經承擔過新國大中文系另一位學者的升等審查案,了解其中的程式。但丁荷生在任的那次,恰好我正手邊有事需按時完成,無法在新國大中文系要求的時限內完成,就介紹其他的學者承擔了。這算是我們在哥廷根之後打的一次交道吧。
周越是我們已經到了哥廷根一段時間之後才去的,好像總共在那裏呆了不到一個月。他也是學宗教人類學專業出身,研究物件也屬於民間宗教的範圍。那時他剛剛得到劍橋的講師職位。但由於他是北京出生,大概十幾歲隨父母移居香港,然後再去美國取得的博士學位,所以和我及巫達談起來並無隔閡。後來我回國之後,大概2013年的下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李建欣專門去找我,邀請我擔任英文版【中國宗教研究】的編委,並請我介紹海外的相關學者,我還特意向他推薦了周越,建議他也邀請周越擔任刊物的編委。
除了和我一樣來訪的學人,我在馬普所還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學人余丹(DanSmyerYü)。他當時也是馬普所的「雇員」,但和其他年輕的研究人員不同的是,他好像還承擔所裏的一些組織、行政方面的工作,既是博士後研究員(pos-doctoralfellow),又是「工作人員」(staff)。之所以說他特殊,除了這一身份之外,還有他的經歷。在見到他本人之前,從馬普所網頁上他的照片以及他的英文名字來看,我還以為他是一位藏人。但見到本人並幾次聊天之後,我才知道他原來竟是在杭州出生長大的。雖然我那時還在北大任教,尚未調到浙大,但由於一直喜歡杭州,便對他的這一背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跟他說起,來之前看他馬普所網頁照片上的裝束,以及他英文名字中的「middlename」,以為他是藏人。結果得知,那是因為他的研究領域之一是藏傳佛教並在藏地呆過,照片只是身著藏裝而已。至於中間名,或許與他在美國留學和工作時娶了一位美國太太有關,但這一點我沒有問過他。記得有一次承他邀請,我和巫達一起去他家,才知道他對攝影和視覺藝術很有興趣,家裏有很多不同款型的照相機。他說起相機和攝影也是如數家珍。我本來以為他會在馬普所呆較長時間,不料他2013年就離開了,後來聽說回國到了雲南大學任教。
年輕的研究人員中有幾位來自中國大陸,其中有一位是新疆人,若非她自己介紹,並說得一口純正的普通話,乍見到她時,單憑相貌,我和巫達兄都以為她是外國人。還有一位來自台灣並在美國取得了社會學碩士和博士的女士黃維珊,由於母語是中文,大家交流起來也更順暢。所以,除了所裏官方的活動之外,我們這些擁有共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學人們,也私下聚過幾次。
我一個人在馬普所的時候,飯後基本上都要沿著哥廷根老城的城墻步道散步,有時候是和巫達兄一道,有時候是自己。後來家人前來,我們只要不外出旅遊也常去散步。因此,除了牧鵝少女之外,哥廷根老城的城墻步道,大概成了哥廷根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建築物了。而當我十二年後再到哥廷根大學教學時,又恢復了在那裏散步的習慣。
馬普所並不屬於哥廷根大學,但哥廷根大學畢竟是哥廷根最大的學術和教育機構。對於這種典型的大學城來說,整個城鎮可以說就是圍繞大學來運轉的。因此,馬普所自然也和哥廷根大學有著密切的學術聯系。2009年,範筆德去參加我在東亞系的講座即是一例。而我在馬普所駐訪期間,自然也和施尼德教授保持著聯系。不過,我不是那種喜歡社交、尤其是刻意經營朋友關系的人,歷來奉行「淡如水」的交友原則。既然是在馬普所駐訪,除了馬普所的活動之外,我並未參加多少哥廷根大學東亞系的活動。只記得有一次施尼德教授邀請我和當時在那裏客座的來自台灣的蔡彥仁教授去他家裏吃晚飯,這次造訪使我對他家對面的開闊麥田以及旁邊據說是靠專利吃飯的鄰居留下了深刻印象。蔡教授留學哈佛,對儒家的宗教性問題也有關註和研究,和我的研究路徑有一致之處,我之前也拜讀過他的相關論文,可惜英年早逝,令人唏噓。
2019年至2020年,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擔任研究員,期間本有順便再次存取哥廷根的打算。但由於2020年1月「新冠」已經席卷全球,幾乎所有柏林高研院的研究員都不得不提前結束了駐訪。我本擬在2020年的幾個學術活動也都隨之取消。2023年再訪哥廷根,距離2012年駐訪馬普所已有十一年了。
哥廷根大學的教學
也就是在2023年暑假我到哥廷根第二次演講的那一次,施尼德教授在和我野外散步聊天時,即向我發出了去東亞系講課的邀請。他告訴我,他們東亞系有一種密集課程,為期一個月,一般在6月至7月的中下旬。這個時間北美和東亞地區的大學基本已經放假,但德國的大學仍在學期之中,因此比較適合邀請德國之外的國際學者前來講課。夏天杭州酷熱,去德國正好可以避暑,於是我當即便答應下來。
我們在2月初便已商定了課程的具體安排,課程的名稱最後定為「HowtoBecomeaPersonofWisdomintheCosmos:AConfucianProject」。事實上,這門課本來的名稱是「EssentialsofConfucianism」,是我曾經在浙大艾寧國際校區以及北大的燕京學堂給國際學生開過的儒學通論性質的英文課。因為在哥廷根大學的課要用英文講授,所以我就把這個現成的課程派了用場。當然,在我看來,對於從整體上了解儒家傳統的要義來說,這門課基於我數十年來對於儒學根本義理的融會貫通,也的確比較合適。之所以改成「HowtoBe-comeaPersonofWisdom intheCosmos:AConfucianProject」,是和施尼德教授協商,覺得這個題目對於德國高校一般的學生來說更具有吸重力。
還沒到哥廷根之前,選課的情況我已經有所了解。去年陪同施尼德教授和我同去奎德林堡的博士生朱紫一擔任我這門課的助教,她告訴我最終有27位同學選修了這門課。以我的經驗,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對於任何高校東亞系的研究生課程來說,這個人數算是相當多了。除了德國學生之外,還有不少在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很特別的是,有一位看起來年紀很小的女生課後告訴我,她尚在讀本科,小學即隨父母移居德國。這樣的學生,德語已經接近母語,如果能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將來一定能承擔在德國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還有一位德國學生叫Philipp,對於儒學已有很好的基礎,在知識結構和儲備方面甚至已經超過不少中國的留學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課程結束時,我表示很希望他將來能成為新一代的漢學家。
還有兩位學生,這次和我在哥廷根算是難得的相遇。一位是我在浙大指導的碩士研究生蔡昊洋,我之前推薦他到波鴻魯爾大學從羅哲海(HeinerRoetz)教授遊。羅哲海教授雖已退休,但仍幫助昊洋在波鴻取得了留學生的身份。我來哥廷根授課之前,昊洋已在波鴻有近半年的時間。他知道我在哥廷根講授一門密集課程,每周二、三的下午,每次三個小時,就每周二上午從波鴻趕來,在哥廷根住兩晚,不僅全程參與了我的課程,由於「同在異鄉為異客」,還多了一些在國內反倒不易有的私下交談的機會。午飯或晚飯之外,我的城墻步道散步,昊洋也都是陪同的。如此一圈走下來,我們就有固定的一個小時左右的聊天時間。其實,除了上課之外,這種聊天的時間,對於學生從老師那裏獲得知識和啟發,是最好的機會。如果一個學生不主動經常和老師交流,又不能認真仔細地研讀老師的著作,雖然名義上也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其實是很難「出師」的。昊洋對我的治學方法和各種想法之前已經比較熟悉,本不必每周專程趕來。但他謙稱並未聽過我的英語授課,所以要來,其實是他好學與善學而已。
另一位是呂澤鋒同學,他是我2023年暑期在義大利維真古典學院(TheAcademyVivariumNovum)認識的年輕人,當時高中畢業不久,正在那裏進修拉丁文。維真學院是一所獨特的專門提供拉丁文與西方古典教育的機構,在介紹我的柏林訪學經歷時已經講過,這裏就不贅述了。澤鋒2023年從維真學院畢業,我在哥廷根授課時,他已經是圖賓根大學主修哲學的學生了。得知我在哥廷根授課,他特意從圖賓根(Tübingen)乘五個小時的火車前來聽了兩次課。雖然來去匆匆,我們能在哥廷根重逢,也是難得的緣分。像他這樣真正接受過良好的西方古典語文訓練,同時又對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自始即有濃厚的興趣者,我也盼望能夠越來越多,使中西之間真正有深度的思想交流代不乏人。
學術之路
二戰之後,隨著人才的流動與資源的再分配,世界學術的中心無疑轉到了美國。美國的高校大多能夠給博士研究生提供優厚的獎學金,於是日益吸引了世界範圍內的留學生。其中,中國留學生占據了相當的比例。相比之下,那些歐洲古老的大學,似乎失去了吸重力。不過,像哥廷根這樣的歐洲傳統大學雖然很少能夠提供優厚的獎學金,但沒有學費且生活成本並不高,卻構成了其吸引學生的優勢。這次我課上的一些中國來的學生,例如來自山東的博士生翁海峰、來自武漢的碩士生朱宇昂等,從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向我介紹了哥廷根大學招生和錄取方面的一些情況。透過和他們的閑聊,我感覺這也是一個優勢。美國的高校固然提供優厚的獎學金,但競爭激烈,不是人人都能有;即使得到,去掉不菲的學雜費,往往也所剩不多。如此一來,與在德國留學相比,僅就成本而言,其實也相去不遠。
當然,美國的高校對於研究生培養都有一套較為嚴格的程式,包括達到一定學分的修課要求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考試等,這就使研究生的資質和水準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相比之下,以哥廷根大學為例,德國的研究生沒有學分的要求,也就是說,一堂課不上,只要透過論文的口試,即可獲得博士學位。這樣的話,學生水準難免良莠不齊。也因此,如今美國畢業的博士比歐洲包括英國在內的博士在整體上更有資質,也是學界公認的。然而,美國的那套研究生培養制度,可以確保能夠獲得博士學位的基本上都是「合格產品」,卻並不能保證產出的都是一流學者。德國的那種制度雖然有可能導致「註水」,但對於真正有誌於學術研究且悟性較高的學子來說,這種不用修課,完全自由的方式,反而可以使得碩、博士研究生在求學期間擁有充分的時間去閱讀更多的學術著作。對於人文社科領域的學生來說,這顯然是最為重要的。兩者相較,其間的得失利弊似乎也未可一概而論。當然,最優秀的學生不管什麽樣的制度都會脫穎而出。
施尼德教授對他的研究生都非常好,將他們一一介紹給我。上次請我來講座時和他指導的博士生座談,請我就他們各自的選題提出建議,即是一例。這次為期一個月的授課,時間更為寬裕,不但他正在指導的學生如朱紫一、刁珊、翁海峰和我有很好的交流,已經畢業好幾年的學生彭沁沁,也兩次專門從她家所在的法蘭克福前來聽我的課,並和我與昊洋有過餐敘。上次座談時在座的Felix,在課程快結束時也從外地前來,不僅聽了我的課,還和我們一道在歌劇院旁邊的餐廳喝啤酒聊天。施尼德教授說他為人靦腆,擔心對他找工作不利。我這次和他進一步接觸,的確感受到了他的這一面。不過,我也對施尼德說,一些醉心學術的學者往往都有這一特點。他們不擅長或者不太喜歡和人打交道,至少客觀上會讓他們更專註於自己從事的工作。德國的文科博士生很難一畢業就能找到固定的工作,像漢學這樣極其小眾的專業更是如此,往往都要經過好幾個地方的博士後和合約工之後,等到某所高校空出一個位子,再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才能得到一個固定的教職。但是,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不少莘莘學子投身到包括漢學在內的人文領域之中。或許,在生計之外,這就是學術的魅力吧。
也正因此,大力建設和發展東亞系,其實可以為年輕的後輩學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我這次前來授課,距離2009年施尼德由荷蘭萊頓大學返回德國重建哥廷根大學的東亞系,恰好整整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從無到有,乃至一度將哥廷根大學的東亞系建設成為德國高校中最大的東亞系,施尼德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他告訴我,當年他的博士論文寫了800多頁,後來正式出版時只發表了其中的300多頁。我們多年前閑聊時,他也告訴我有不少研究計劃。他這些年來將大量的心力和時間投入到了東亞系的建設當中,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沒有影響。這次見面,他不止一次和我談到,希望進一步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以便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同時,他也提到,最近數年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東亞系也面臨萎縮的局面,現有的教授退休之後,校方大概不會再有所補充了。這當然是個不好的訊息。目前東亞系從事中國研究的教授,除了施尼德之外,還有夏德明(DominicSachsen-maier)和一位教中文的女士,加上2024年夏剛剛新進的一位年輕教授,一共也只有四位。雖然比大部份德國大學中東亞系的漢學教授人數仍然要多,但較之鼎盛時期的八位,已經減少了一半。
德國歷來是教授治校,教授在學校的運作過程中享有很大的權力。比如,博士生的招生基本上由教授個人決定。從學校到院系的各項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教授也有很大的權力。我記得施尼德教授曾告訴我,哥廷根大學有專門的教授委員會,只要有15位教授聯名,就可以罷免校長。當然,擁有權力的同時也意味著承擔更大的責任。所以,德國的教授在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之外,無論是否擔任明確的行政職務,大都要承擔很多行政方面的工作。如果要在這些工作之外再去跑計畫、拿課題,還有多少時間能用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就可想而知了。
如今,計畫和課題在中國已經成為高校考核的標準之一。其不合理之處,我曾有文章談及,也引發了較為廣泛的反響。與施尼德教授談起,他也對德國的計畫與課題問題有所批評。盡管德國學界的計畫和課題和中國的不可同日而語,但高校把計畫和課題作為業績之一,為了爭取到計畫和課題,學者們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對計畫和課題本身的學術價值有時反而不免有所輕忽,已成為德國學界日益凸顯的問題。對於那些只顧跑計畫、拿課題以至於不能沈潛於學術研究本身的人與事,施尼德教授不止一次向我表示了他的嗤之以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此,世界上真正以學術為誌業的人文學者,都會產生心同理同的共鳴吧。
這次哥廷根之行雖然比兩次演講呆的時間要長,比馬普所的那次駐訪要短,但因為有了教學的經驗,所以感受頗與往不同。雖然每周兩次、每次三個小時的課程不免密集,以至於一個月的時間很快過去,但畢竟不是短短的三兩天。得知我有一個月在哥廷根,羅哲海教授還與波鴻魯爾大學主持東亞研究的MarionEggert教授一道,特意湊我的時間舉辦了一次小型的工作坊,使我得便回訪波鴻,特別是重遊了闊別已久的潛園。
此外,我幾乎每晚飯後的城墻步道散步,仿佛接續了2012年夏天馬普所駐訪時期的時光,可以讓我在自由自在的漫步中,從容思考心念所及的種種問題。那些問題並不總是令人輕松愉悅,有些難免讓人心情沈重。然而,能夠自由自在地思考,讓自己的心靈世界日益向廣大精微而趨,「淵然而有定向」,不淪為自以為是其實不過是提線木偶的「dasMan」,更不「自售」而「貨於帝王家」,豈不正是學人之所求?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說得也正是這個道理。
哥廷根印象
哥廷根面積不到120平方公裏,人口不足13萬,對於前前後後呆過四個多月的我來說,似乎應該是「一覽無余」了。但是,我每次到哥廷根都有新的發現。例如,俾斯麥當年在哥廷根求學時因行為不端而被市政府「驅逐」,勒令其在城外住了約半年。而他當時所謂的「城外」居所,如今是哥廷根景點之一的「俾斯麥小屋」(Bismarckh覿uschen),其實就在城墻步道之上。只要散步環城墻一周,一定會遇到。然而,也許時間久遠,即使2012年夏在城墻步道走了不知多少圈,我的記憶中也一直並無它的位置。直到今年來授課的這次,我才發現了這所「俾斯麥小屋」。與我對於「牧鵝少女」每次來哥廷根必去欣賞拍照的經驗,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中國人比較熟悉的「朱德故居」,我2012年在馬普所駐訪那次倒是看到過。但那是因為它恰好在哥廷根劇院和馬普所之間必經的路上,舉頭便可望見,並非我尋訪而得。這次去馬普所故地重遊的路上,又看見了它。如此看來,哥廷根城市雖小,我每次來訪卻都有新發現,大概是因為我從未刻意要把哥廷根的景觀一次看盡的緣故吧。
不期而遇給人帶來的驚喜,較之按圖索驥的匆匆一瞥,或許至少可以讓人多一些欣賞的從容。對於像哥廷根這樣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大學城,或許你總能在不經意間發現歲月留下的積澱和痕跡,無論是看得見的自然或人文景觀,還是載之史冊或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口中流傳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哥廷根的吸重力之所以持久不衰,在我看來,原因之一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