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也可以做一名護工?
當我一本正經地跟做醫生的英國男友說,我想成為一名護工時,一貫支持我做任何決定的他,反應令人失望:「你再考慮考慮吧,不要憑著一時沖動就想進入醫療照護行業。」
別人越是覺得不可能的事,我越想去做。
開啟電腦,座標定位於我所在的英國中部小鎮,範圍設定為10英裏(16公裏),僅在一個網站上,我就發現了50多份招聘護工的廣告,薪酬在每小時11英鎊到14英鎊(100-128人民幣)之間,主要的工作場景是醫院、養老院、以及客戶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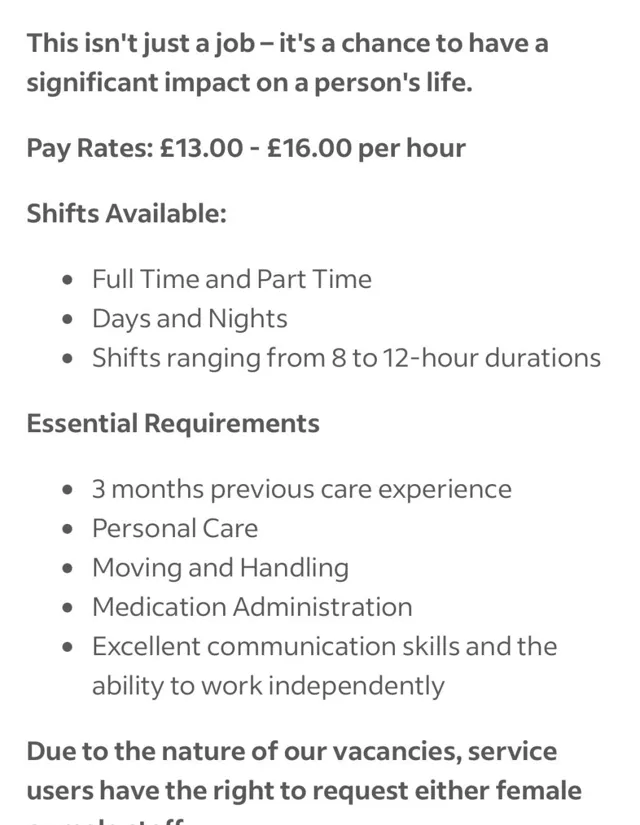
小鎮附近一家養老院的護工招聘廣告。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曾茵子 截圖/攝
「做護工可以幫助他人,有穩定的收入,不用依靠你就能拿到簽證,幾年之後還可能有培訓機會,成為護士、康復治療師助理,不是很好嗎?」我問男友。
「你之前在咖啡館打工的時候,每天回到家都要抱怨。做護工是要去給別人擦屎擦尿的,你在服務行業裏最受不了的一切,在護理工作裏只會加倍出現。」他再次給我潑來冷水。
說實話,做了幾年記者,又在倫敦讀了紀錄片研究生,考慮去做護工是出於無奈。畢業後,我曾經滿懷期望可以在英國紀錄片行業裏一展身手,誰知道摸爬滾打一年多,連相機都沒碰到——在後期公司的地下室廚房裏做咖啡,上夜班給拍攝團隊格式化儲存卡,短期合約時有時無,收據信收到手軟……面試時別人問我5年後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麽,我都不好意思說出「導演」二字。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我的學生簽證就要到期了,回國還是留英,以怎樣的方式留在這裏,我都沒有答案。
為了給失業的生活找點意義,我每周會到鎮上醫院的老年病房做誌願者。醫院位於鎮中心,屬於綜合性醫院,有急診、綜合護理和癌癥、中風等專科。總共大約790張病床,急診科24小時開放,為郡縣裏的88萬人口提供服務。
醫院官網上招募的誌願者有14個工種,除了我選擇的病房誌願者外,還可以申請去急診科陪病患和家屬聊天、開電瓶車在醫院裏運送病人、幫忙跑腿傳送醫學樣本和處方、陪伴臨終患者等。
支撐這個誌願者隊伍的是廣為人知的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根據NHS England的數據,在全英,醫療誌願者總共大約有10萬人。疫情期間,有超過40萬人參與了NHS誌願者響應者計劃,其中許多人至今仍在參與誌願服務。
同在醫院工作,男友的社交圈裏大多是醫生和護士,而誌願者工作讓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護工這個群體。有天,在和一位來自印度的護工聊天時,我提及了對簽證的焦慮。「你也可以來做護理工作呀」,他不假思索地說,好像這是個理所應當的最優解,「提供工簽,培訓期間有收入,工作也輕松——你看」,他歪頭指向他負責的病區,「他們現在都在睡覺,我就沒什麽事要做了。」
我記得那是個周末的早上,病房裏很安靜,這位護工在和我聊了會兒天後,在病區一頭的桌子前坐下,開始處理筆頭工作,時不時擡頭觀察他照護的六位病人。看著他神閑氣定的樣子,我第一次認真地思考:也許我也可以做一名護工?

我居住的小鎮。
「被需要」
誌願者的培訓在中風病房裏進行,我們要在四周掌握如何分配三餐和茶水、整理床鋪、陪病人聊天。在病房裏,我們和護工配合密切,可以幫護工「打打下手」。但誌願者主要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陪伴,而護工則負責護理的方方面面。
我陪伴的第一位病人名字叫John,他的頭發花白稀疏,臉圓圓的,身材有些肥胖。護工把我安排到他旁邊的時候,低聲提醒我:「他有點困惑。」
John坐在病床旁邊的軟椅上,面前的小桌子上沒有任何個人物件,只放著醫院統一發的水壺、杯子和紙巾。他床位上方掛著塊白板,記錄著病人的基本情況。John的白板上,蝴蝶圖案的方框裏畫著一個勾——在英國和愛爾蘭的近兩百家醫院中,患有失智癥或記憶力衰退的患者可以加入「蝴蝶計劃」,透過蝴蝶圖案標識來提醒護理人員關註患者的特殊需求。
我搬了張椅子在John對面坐下,他眼神散漫地漂浮著,始終沒有落在我身上。 我試探著自我介紹,問他:「我能在這兒陪你坐會兒嗎?如果你覺得不方便,我可以離開。」
「別離開我!」他突然轉頭看向我的方向,眼淚大顆大顆地從臉頰滑落,「別離開我……」他反復哀求道。我連忙安撫他,沒想到「離開」二字,對他來說似乎意味著拋棄。
我給他遞去一張紙巾,卻發現他的手沒有準確地找到我的位置。我把紙巾放到他手掌上。
他擦著眼淚,急促的呼吸慢慢變得平緩,「你真好」,他終於露出了一絲笑容,「謝謝你。」
「你喜歡什麽動物呢?」我試圖找個輕松的話題轉移他的註意力。
「我喜歡大熊貓。」他脫口而出。
「是嗎?為什麽喜歡大熊貓?」我笑道。
「我也不知道,它們很笨拙可愛。」John說。
「但它們每天就知道吃飯和睡覺,挺沒用的。」
「沒用……我現在不就是這樣的嗎?」他喃喃道,「其實有時候,真希望我可以快點死掉。」
我楞住了,一時無言。後悔自己剛才的玩笑話,竟如此不合時宜。一陣沈默後,我決定實話實說:「其實,能和你坐在這裏,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陪伴。你的存在,對我很重要。」
出乎意料地,John咧嘴笑了:「這麽聽起來,確實有那麽點意義。謝謝你。」
我把病床配備的行動電視機調整到他耳邊的位置,陪他一起看。他時不時扭頭望向我的方向,確認我在旁邊,又繼續安心地聽節目。過了一會兒,他突然神秘兮兮地湊近些:「你想聽個笑話嗎?」
我點頭:「當然!」
「有什麽比一個漂亮女人更好?」
「什麽?」
「兩個漂亮女人!」John被自己的話逗得放聲大笑,我忍不住搖頭,跟著笑了起來。
那天,我久違地感覺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我想,如果做護工能獲得這般成就感,我會毫不猶豫地嘗試。
病房裏的氣味與「my love」
「你能幫我拿一些尿片、擦紙、紙盆、幹凈的病服、內褲和床單過來嗎?噢,還有紅色塑膠袋!」戴紅框眼鏡的護工利落地跟我說。尿片、擦紙、紙盆、病服、內褲、床單,我反復默念這個列表,快步走向分布於病房各處的儲物間,生怕遺漏了什麽。
中風病房四周的培訓結束後,我被分配到了老年病房。這裏住著約40位老人,幾乎是中風病房人數的兩倍,許多病人患有失智癥,病房裏總有新的狀況發生,沒有一刻清閑。
就在一分鐘前,我還在聽面前這位瘦小的老奶奶念叨著她要去抓一只飛在天上的龍,突然她從床上坐起來,推開面前的小桌板要往外走。我擔心她跌倒,卻因為誌願者未經專業培訓不能攙扶病人,只能趕緊向目之所及的護工呼救。紅框眼鏡護工過來解圍,她先是用溫柔但堅定的語氣,說服老人在床邊的軟椅上坐下,然後快速地瞟了一眼床單上深褐色的銘印,給我作出指示。
幾分鐘的工夫,紅框眼鏡護工已經將床單、枕套、被單和毛毯按照汙染物和非汙染物分類,分別裝入紅色和白色塑膠袋。另一位護工加入進來,她們拉上病床四周的簾子,開始給老人進行換洗。
在醫院裏,但凡被血液或排泄物汙染過的物品,比如床單、衣物或杯子,誌願者通常是不碰的——這些都需要護工、護士等專業人員來處理。即便如此,病房裏的氣味是誰也逃不開的。剛開始做誌願者時,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覺得那股強烈的味道還殘留在鼻腔裏。在與護工們的聊天中,我發現,這也是他們普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
Bimbola個子不高,臟辮紮成馬尾束在腦後,很愛笑。她也是老年病房的一名誌願者,今年41歲,與此同時,她的正職是一名住家護理員(Live-in Carer)。
在英國做護工的工作場景主要有三種:醫院、養老院和老人家裏。三者職責類似,通常都不需要統一的職業資格註冊。相比之下,在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醫院工作,環境更規範,帶薪年假和病假、養老金計劃和職業發展機會都有保障。養老院大多為私人機構,待遇和保障因雇主不同而差異較大,但總體薪資低於NHS。住家護工一般受聘於第三方機構,除護理外,他們還要負責照顧客戶日常生活,包括做飯、清潔、帶客戶外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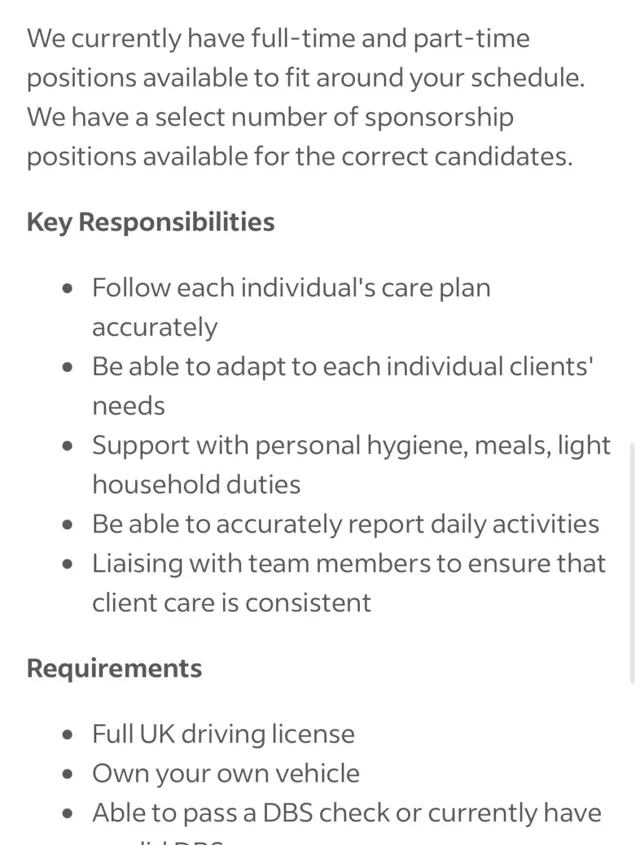
小鎮附近,招聘居家護理人員的廣告。
上崗第一天,Bimbola跟著前輩護工學習如何給客戶清洗身體時,驚訝地發現客戶竟然是一名男性。「啊!我不能看!」她驚叫著捂住眼睛。她告訴我,在她的家鄉奈及利亞,護工只照顧同性別的客戶,而這也是她必須克服的第一個障礙。
清理排泄物是第二個障礙。Bimbola坦言,剛開始她也忍不住想看向別處。「每次清理後,我甚至恨不得找個地方嘔吐。」她做出一副惡心的表情。後來,她開始用一種新的視角思考:「如果客戶是我婆婆,她會希望我在照料她時別過臉去嗎?」這樣的自問慢慢幫助她克服了心理障礙。
老年病房的簾子內,傳來熟悉的安撫聲:「親愛的,把你的臀部擡起來好嗎?我知道很不舒服,對,就這樣,你做得真棒!」
在這個醫院裏,不論醫生、護士,還是護工和服務員,都習慣稱病人為「親愛的(my love)」。剛聽到時,我覺得這種稱呼有點矯情刻意,像淘寶客服常用的「親」,但在病房的特殊語境裏,它卻奇妙地生出一種溫暖的力量,拉近了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的距離。
為保護病人私密,每次護工們在拉上簾子給病人做護理之前,都會禮貌地請誌願者離開。即使隔著簾子看不到裏面的情景,簾子外的人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氛圍。有時簾子內是護工和病人平靜地聊著家常,有時卻是病人的喊叫和咒罵。簾子開啟後,我偶爾會看到護工們臉上的疲憊,有時他們甚至忍不住對我苦笑搖頭,但他們轉頭面對剛剛朝他們發脾氣的病人時,依然溫柔地稱他們為「親愛的」。
忙、忙、忙
Michael是一位20歲的英國白人小夥,目前正在攻讀醫學院。「學醫的人通常都懷著幫助別人的理想,也許有點天真。」他帶著幾分自嘲回憶道。2023年,他利用大一暑假,在倫敦一家私人養老院做護工,既為賺取零花錢,也想積累與醫療相關的經驗。
他簽的是零小時合約(Zero-hour Contract),沒有保障最低工時、沒有病假津貼或養老金,雇主隨時根據需求給雇員派工作,雇員也有自由接受或拒絕工作。這種合約一般存在於服務行業,根據英國議會下議院圖書館的數據,目前英國大約四分之一的社會護理工作者采用零小時合約。英國2023年最低薪資線為每小時10.42英鎊,Michael的薪資是11.10英鎊每小時,僅僅略高於此。
在Michael的想象中,護理工作是為了幫助客戶更好地享受生活。然而,真正開始工作後,他才發現,護工能做到的只是維持客戶的基本生存:擦洗、換衣、餵食——他的工作重復且永無休止。「當你好不容易把每個人都洗漱好,已經到了午飯時間;等你讓每個人吃完飯,又到了換洗的時間。如果你稍微多陪一位客戶聊幾分鐘,下一位客戶可能就要在屎尿中多等幾分鐘。」
作為新手,Michael為每位客戶花的時間比熟練護工要多,他也堅持不走捷徑,確保護理品質。然而,這份認真負責反而讓同事們不願與他搭檔,因為他的工作節奏拖慢了整個團隊。
理論上,他在12小時的輪班中有半小時午飯時間和兩次短暫的休息時間(各15分鐘),但實際上,他幾乎沒有機會停下來喘口氣,午飯時間也常被壓縮。一天工作下來,Michael感覺筋疲力盡。零小時合約下,接班或休息由員工自己決定,為了多賺錢,他常常連續上四五天的長班,休息兩天後繼續。
客戶的不領情也讓他備受挫折。他理解,被陌生人擦洗不僅意味著失去私密,還可能伴隨著身體上的不適,因此不少客戶會表現出抗拒甚至憤怒。但當他的努力換來的只是客戶的咒罵時,他仍然感到難以釋懷。「其實,客戶的一句‘謝謝’就能讓整個護理過程順利許多」,Michael說。
他依然提醒自己:保持職業操守,不能因為與某些客戶關系較好,就對他們投入更多的時間或情感。
忙碌也是Bimbola的常態。做住家護理時,她一般在客戶家裏住兩周,第三周休息。她要負責照顧客戶生活的方方面面:洗漱、穿衣、買菜、做飯、拿藥,陪客戶散步、聊天。除了每天一小時的午餐,客戶睡覺的時間是她唯一的休息時間。但她也無法完全放松。有時,她要利用這段時間打掃衛生;而她終於躺下後,休息也可能隨時被打斷。
有一次,她剛入睡,就被患有失智癥的老人叫醒,對方問窗簾是不是沒拉上。Bimbola再三確認後,老人才返回自己的房間,而她卻再也難以入眠。「即使是休息的時候,如果客戶敲門,你也不可能說‘我沒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需求有多緊急。如果因為你的照顧不周導致問題發生,責任全在你。」她感嘆道。
而在老年病房,護工的時間更是捉襟見肘。他們一般是37.5小時每周工作制,每次輪班12小時,中間可能穿插一些半天班,工作日或周末輪休。在醫院,護理都由醫院聘用的護工完成,免費提供給病人。這源於NHS提供可及且平等的醫療服務的宗旨。NHS成立於1948年,主要依靠稅收作為營運資金。除了處方藥、視力測試和牙科等少數服務外,大部份治療是免費的。
對於需要24小時一對一看護的病人,醫院會額外聘請護工,一般是兼職護工,每小時薪資比全職護工高。即使一個病人有自己的住家護工,他們也不被允許帶到醫院,因為醫院要對在病房裏發生的事情負責,每個在醫院工作的人都需要經過嚴格的背景審查。NHS護工薪資每年在24000英鎊到26000英鎊之間,根據經驗不同有所差異。
然而,英國醫療照護行業的專業人員處於嚴重短缺狀態。
根據NHS England數據,截至2024年9月,NHS約有十萬七千個全職等效崗位空缺。國王基金會的調查表明,員工的流失主要由於工作壓力、薪資偏低和缺乏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人口老齡化和失智癥患者的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英國老齡協會與護理品質委員會2024年的調查顯示,英國每4名老年人中,就有1名沒能獲得所需的照護服務。
對於失智癥患者來說,失去了時間和空間的秩序感,陌生病房裏嘈雜的聲響和來往的人,都可能讓他們困惑、恐懼。大多數時間,他們只是等待——等待三餐,等待家人到來,等待換洗。
有一次,一位患有失智癥的老奶奶Rose,焦急地把我招到床前,懇請我幫她換洗。「稍等一下,我去找護工幫你好嗎?」我話音未落,Rose就一把抓住我的手,不讓我離開她視線半步。「你如果走了,就不會回來了,到時誰來幫我?」她眼裏滿是焦慮和恐懼。分身無術,我只好坐在她床前,陪她一起等待。護工、護士來來往往,我一個又一個地「逮住」他們,轉達Rose的請求。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得到的是一個接一個的「等一下」。
「看吧,沒有人會幫我,他們就讓我一身臟地躺在這裏。」Rose絕望地說。這塊骯臟的尿布好像是她此刻生活的全部,她四處張望,無論我說什麽,都無法轉移她的註意力。
二十分鐘後,終於有兩位護工有時間幫Rose進行換洗,簾子被拉上時,我也松了口氣。這樣的等待,Rose每天可能要經歷好幾次。
Rose的情況不是個例。走在病房裏,我常常被病人叫住:有的想上廁所,有的想穿上毛衣,有的想調整枕頭的高度,有的需要輔助餵食……對於患者來說,這些都是迫切的小事,很多人會跟我抱怨,為何這麽簡單的需求,卻始終沒人能第一時間幫忙解決。而事實上,每位護工通常要照顧六名病人。面對不斷湧來的請求,護工們只能不斷理清輕重緩急,優先處理那些最緊迫的狀況。
人才缺口下,缺乏吸重力的護理行業
「你要去做護工?是不是有點大材小用了?」朋友聽說我近期的職業考慮時脫口而出。
「你這話驗證了大家對護工的偏見啊!」我說,心裏卻偷偷因為朋友對我專業的肯定而歡喜。
在許多人眼裏,護工是沒有太多教育資質和職業選擇的人才會從事的工作。
在我服務的醫院2023-2024年度報告中,特別提到,他們推出了學徒計畫,希望透過給護工提供向護士助理、護士、助產士等職業發展的路徑,吸引更多人加入護理行業。這似乎意味著,護工在醫院是緊缺的,但這一職業也少有明確的職業前景。
醫院招人難,養老院也同樣缺人。Michael遞交簡歷後,僅用一周半就得到了養老院的護工工作。他記得招聘廣告上對求職者資質幾乎沒有硬性要求,只要無犯罪記錄即可。
面試過程更顯草率——經理拿著問卷逐題詢問,大部份問題涉及醫療倫理或狀況,Michael一知半解,但面試官耐心提示,甚至主動幫他總結答案填寫在答卷上。第二天,Michael被告知透過了面試。這麽輕易送上門來的工作,Michael是第一次見。
護理培訓持續四天,內容主要是急救演練和護理相關的法律、倫理知識。具體的工作內容,Michael直到第一天上崗才搞清楚。
Bimbola接受的培訓更為簡單,透過幾天線上課程,她就獲得了護薪資質,受聘於一家英國的私人護理公司後,除做住家護理(Live-in Care)外,她還做居家護理(Domiciliary Care)工作,工作方式類似於快遞員,公司派單,護理員接單上門服務。每天,她要分別去六到七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裏,幫他們做飯、擦洗、如廁。每次任務需在30分鐘到一小時內完成,然後趕往下一個家庭。公司只給每次走訪間留15分鐘交通時間,而客戶往往分布在小鎮各處。初來英國,她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車,只能搭公交車奔波,經常因遲到被護理公司的老板責怪。面對這些問題,老板只給她一個建議:「去買輛車吧。」

小鎮的道路。
Bimbola的工作日從早上7:30開始,晚上7:30結束。盡管她一天「在崗」12小時,但只有實際服務的六到七小時算工時,薪資略高於每小時11.44英鎊(約105.67人民幣)的英國2024年最低薪資水平。
她苦笑著說:「朋友叫我周末去倫敦玩,我總是回絕:‘別算上我,我沒錢。’」
隨著暑假的結束,Michael也結束了在養老院的工作。看到自己無論怎麽努力工作,都無法改善老人們的生活品質,Michael承認他有種深深的無助感。他原計劃把這份工作當作上學時的兼職,但如今他堅決表示,這輩子再也不想做護工了。
他坦言,之所以願意和家人朋友聊起自己做護工的經歷,是因為他清楚這只是份臨時的工作:「也許是因為身邊的同輩人,大多都在找需要學歷資質的工作吧。」
助人的理想還在,只是現在,他寄希望於成為醫生後可以治病救人。「不知道這種期望是不是也太天真了呢?」Michael笑道。他現在專心於學業,假期時透過給高中生做考試輔導賺零花錢。
我的心態和Michael類似。即使親眼看到護理工作的價值和重要性,社會對職業尊嚴的定義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對這份工作的考量。 看到當年一起做記者的同事們,如今有的升職成為編輯,有的轉到了更高收入的行業,和她們探討我對做護工的考慮時,我也總不由自主地把這份工作描述為一個進階到其他職業(比如康復治療師、養老行業創業)的過渡,而不是一份永久的事業。
我好奇Bimbola是如何決定長期做護工的,在奈及利亞時,她是一家室內設計公司的老板。她提到自己的表兄弟在得知她現在從事的工作後,既驚訝又直言不信她能堅持下去:「你在奈及利亞可是被大家尊稱‘夫人’的女商人啊!」
異鄉人
我所服務的老年病房裏,護工們來自世界各地:印度、羅馬尼亞、奈及利亞、義大利,有年輕人,也有中年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閑聊時,簽證和移民經歷往往是異鄉人之間迅速拉近彼此距離的話題。
有一次,我問一位來自羅馬尼亞的護工是否喜歡她的工作,她遲疑片刻,勉強笑了笑:「這工作不容易,但總比待在我的國家強。」
Michael告訴我,他所在的養老院裏,只有他一人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同事們大多依靠這份工作獲取簽證擔保。許多人在本國已是護士,但要在英國成為註冊護士,必須透過考試取得本地資質。為了在備考期間保持合法身份並有收入,不少人將護工工作視為過渡。根據慈善機構Skills for Care 2023-2024年的數據,英國護工從業者中,黑人、亞裔及其他少數族裔員工占比達40%,比英國總體人口中的多樣性比例高出23%。
一次醫院誌願者培訓活動結束後,我和Bimbola在寒風中邊走邊聊,直到走進開著暖氣的咖啡館,她才松了口氣,調侃道:「什麽時候才能適應英國這鬼天氣啊?」
Bimbola的家鄉奈及利亞那天的氣溫是32攝氏度,而此刻,她捧著一杯鋪滿鮮奶油和棉花糖的熱巧克力,跟我講述一年前她為什麽離開那個溫暖的國家。
在奈及利亞,Bimbola是室內設計公司的老板。她的父親曾在油漆廠工作,後來自己創業。Bimbola研究生讀的是教育,但畢業後被母親說服到家裏的公司工作,2007年正式接管家裏的生意。
看似安穩的生活,背後卻充滿了壓力。政府的貪腐讓她做審計工作的丈夫日益抑郁,日益飆升的物價讓他們的生活成本不斷增加。Bimbola開始思考離開的可能性。
2020年,英國推出了醫療與護理工作者簽證,並透過減免簽證費與移民醫保費、加快下簽速度等方式,吸引從業者到英國就業。只要有雇主擔保,從業者就能長期留在英國,簽證最長可達5年,比一般學生簽證長得多,而且到期後,只要還有雇主擔保就能續簽。
透過朋友,Bimbola了解到政策上的優惠。2023年10月,她如願來到英國。工作穩定下來後,Bimbola的丈夫和孩子們也都跟隨她搬到了英國。
我問她,有沒有後悔來英國?她並未直接回答,而是講起一次與客戶的對話。那位在小鎮上長大的老人向她抱怨英國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她笑著回應:「我來英國後,沒經歷過停電,連發電機的聲音都沒聽到過。晚上十點半,人們還能安心在外走動。如果在奈及利亞,天一黑你就得待在家裏,怕搶劫或偷盜。對我來說,這裏還是比我的國家好多了。」
她坦言,如果能以教師身份移民英國會更好。做老師既符合她的大學專業,又不像護工工作那樣需要耗費大量體力,但那需要透過繁瑣的資格考試。「要是走那條路,我估計還在奈及利亞呢。」
在老年病房,膚色的分野是鮮明的:醫生、護士和服務人員以少數族裔居多,病人卻以白人為主。我所在的小鎮有85%的人口是白人,而醫院是鎮上除大學校園外,文化最多元的場所。
在病房服務期間,我曾遇到過男性患者對我說,他「最喜歡和亞洲女性上床」,並暗示讓我跟他回家,充滿騷擾意味。但更多時候,歧視性表達是間接而隱晦的。有一次,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對我說:「我沒有反對移民的意思,但現在外來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占用了很多住房,導致房價上漲,本地出生的人都住不起本來應該是他們的房子。」她滿臉親切和善,似乎沒有意識到,陪她聊天的正是一位外來打工的移民,而每天為她擦洗餵飯的,也正是那些「占用」了本地住房的人。

小鎮模組屋。
寫滿問題的皮球
老年病房的活動室裏,錄音機放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情歌,窗子貼著五顏六色的花朵圖案,窗邊大桌子上整齊地擺著各種圖書,有小說、雜誌、自然讀物。角落的大書櫃裏塞滿了桌遊、填字卡、拼圖、塗色書,書櫃旁還堆著呼啦圈和彩色皮球。
活動室的門一關,既聽不到隔壁床患者忍受疼痛時的呻吟,也聞不到屎尿的氣味。盡管離老人們的病床只有幾步之遙,卻仿佛是另一個世界。
等老人們圍成一圈坐好,Maria囑咐我給大家倒上他們想要的熱飲——在醫院裏,一杯熱茶或熱巧克力,有時能帶來莫大的安慰。隨後,她會帶領大家做一些適合坐著完成的伸展運動。
活動組織者Maria是個幹練又活潑的中年女人,來自義大利,在成為活動組織人以前,也是一名資深護工。早上忙完了老人的早餐和洗漱,她便到病床前,把有精力的老人一一「拉」到活動室裏。有些老人早早就期待著活動的開始,而讓有些老人挪窩兒,則需要勸一勸。Maria一邊開著玩笑,一邊扶老人坐上輪椅,前一刻還說對遊戲沒興趣的老人,被推進活動室時,已被Maria逗得滿臉笑容。
「想象你在擦窗子,這窗子有點大,必須要伸長手臂才能擦到。」她微笑著說,雙臂緩緩張開,手掌在空中劃出一圈又一圈的弧線,仿佛真的在用抹布擦拭窗玻璃。老人們跟著她的節奏伸展著,這看似簡單的動作,對很多久坐不動的老人來說並不容易。Maria邊做示範邊環視每位老人,提醒這位如果肩膀疼就暫時別做這個練習,又俏皮地鼓勵只看不做的那位別偷懶。
接下來,Maria拿出一只寫滿問題的皮球,這是她常用的道具。
她把皮球逐一拋給老人,接住球的人需要選擇皮球上的一個問題來回答:「你最喜歡什麽食物?」「你喜歡貓還是狗?」「什麽東西會讓你微笑?」每當一位老人給出答案,常常會激起其他老人對同一個問題的熱烈討論。有一次,他們從鮭魚三明治聊到了小鎮上最好吃的飯店,回憶起小鎮多年前的繁華景象,以及他們作為孩子在二戰期間的所見所聞。在遊戲中,老人們褪去了他們作為「病人」的身份,仿佛只是在小鎮咖啡館裏碰巧遇見的鄰居,聊著家長裏短,交換人生故事。
Maria的工作職責遠不止於遊戲,她還承擔著給老人們做直接護理的任務,而在Maria的安排下,護理工作顯得治愈且充滿樂趣。
在一個難得的晴天上午,她把一位需要洗發的老人帶到活動室裏,其他老人則在一旁做填字遊戲。溫水在紙板漿做的臉盆裏冒著熱氣,陽光灑進活動室,錄音機裏播放的是經典的聖誕歌曲。所有人的目光都被Maria給老人洗發、梳發的輕柔動作吸引,以至於忘記了手裏的填字卡。老人們七嘴八舌地聊著各自年輕時的發色,親切地稱這次活動為「Maria的沙龍」。
把活動組織起來,需要很多智慧。Maria告訴我,「如果沒有和其他護士、護工協調時間,沒有他們體力上的幫助,我一個人很難把一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帶過來參加活動。」只要她值班,Maria都會嘗試給老人們安排一些有趣味的活動,但因為時刻變化的病房狀況,活動組織不起來也是常有的事。有時,活動室會被其他工作人員用作會議室而一上午大門緊閉;有時,活動室甚至被用作臨時病房。
到了冬天,流感高發,跌倒事故增多,老年群體受到的影響尤為明顯,活動室裏也臨時加床,住進了兩位病人。一個上午,Maria都在和其他護工一起忙於給患者進行換洗。即便如此,她也不忘囑咐我把沙包和皮球帶到患者床位前,在有限的空間裏做一些拋扔的簡單運動。
尾聲
「幫忙看著有滑倒風險的病人別讓他們亂走」、「去問問這位情緒激動的病人到底需要什麽」、「去幫他做杯熱茶」、「去陪她聊聊天」……穿梭在老年病房的走道裏,我一次次被護工、護士們叫住。
經過八個月的誌願者服務,我終於弄清楚了物品都擺在哪個儲物櫃,熟悉了長住患者的早餐喜好,更知道怎麽和失智癥患者互動,對病房裏的一切氣味、情景,也都習以為常了。
兩個月前,我拿到了英國的伴侶簽證,幾天後,我接到了新的工作offer。護工作為一種職業選擇的考慮被擱置到了一旁。我沒有Bimbola的勇氣,選擇這份與自己專業無關、被社會低估的職業,作為立足他鄉的方式。
如今,無論是面對異性的身體,還是客戶的排泄物,Bimbola都能做到以專業、尊重的態度處理。一年過去了,她還在做著護工的工作,並利用業余時間攻讀一門為期六個月的醫療與社會照護課程。她希望透過學習獲取更多資質,將來有機會在醫院工作,最終成為一名護士。
「我喜歡照顧別人」,Bimbola說。在奈及利亞,每周兩天,她會騙公司的人說去見客戶,然後「溜去醫院做誌願者」,她偷笑,「我在產科病房、兒童病房、老年病房都服務過。最開心的時刻,就是當有人跟我說:‘因為你,我好多了。’」有些老人甚至對她產生了深深的依賴,每天期待著她的到來,甚至連周末去教堂,都想邀請她陪同。
不過,做住家護理,意味著她在工作的日子裏無法見到家人。剛來英國時,丈夫和孩子還在奈及利亞,Bimbola會在休息時間給他們打電話。全家團聚後,短暫的分離反倒變得難以忍受。上周,有雇主問她是否願意接一個一周的住家護理工作,她的丈夫在場,明顯不願意她答應。即使她表達了想要去的意願,雇主也再沒有聯系她。「在這行,如果你一次說‘不’,別人就不會再找你了。」Bimbola無奈地說。
「要在這一行堅持下去,必須要有熱愛」,Bimbola告訴我,「在這個國家,護工還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幫忙做一件小事,客戶也會真心感謝。」
她決定把周五的時間空出來,繼續「溜」到醫院裏做誌願者。每周一天,不用忙於給老人做身體上的照護,她有充足的時間,陪他們坐著聊天、唱歌,一起大笑。「做護理工作是出於‘必須’,而做誌願者是出於‘我想做’」。
除了Bimbola,我也遇到了不少像她這樣懷著理想主義的護工:在小鎮桌球俱樂部裏,我認識了一位球友。他在五十歲以前從事廣告設計,因為對心理健康產生興趣,轉行到精神病醫院做護工,並在六十多歲的時候成為一名康復治療師。他說直到現在,他去哪都驕傲地帶著他的護工工牌,這份工作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在病房裏,我結識到一位退休警察,為下半生尋求有意義的事業而選擇加入護理行業,她說做警察和做護工都讓人看到世間百態,很少人能有殊榮這樣親近地接觸到別人的生活。
還有一位二十出頭的小鎮女生,在這裏出生長大。她談起做這份工作的初心:幾年前她的祖母病危,去世前就在這個醫院住院。當時她看到護工們對祖母的悉心照顧,便下定決心要把護理當作自己的職業理想。一邊說著,我們拿來幹凈的床單和枕套,還沒等我彎腰,她就把病床調高,提醒我這樣就不會損傷腰部。接著,她事無巨細地向我演示,如何把床鋪得平整無褶皺,以保證病人翻身後也能睡得舒適。

小鎮。
(為保護個人私密,文中護工與患者的姓名皆為化名)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曾茵子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