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大本營的拉美,其代表國家的發展一直是中國的負面參照系。然而在巴西、阿根廷之外,智利似乎是另外一個故事。
從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中後期,智利經濟從拉美地區排名墊底的差生,一躍成為諸多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均名列前茅,至遙遙領先的優等生。2012年,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智利邁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並且至今一直處於這一組別。
1955年,就在冷戰掀起了一波新高潮時,美國國務院啟動了「智利計劃」。這項計劃的經濟目標是在芝加哥大學培訓智利的經濟學家,這裏是資本主義思想的重鎮和米爾頓·弗瑞德曼的學術家園;政治目標即遏制共產主義思潮在拉美擴張。
1973年,奉行社會主義政策的阿連德總統被推翻之後,在美國支持下,皮諾切特執政,「芝加哥小子」得到了大展身手的好機會。作為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芝加哥小子」治理下的智利令人印象深刻,其主要成就包括人均GDP從1985年至2019年提高至原來的3倍。以世界銀行每人3.2美元(按2011年的國際元計算)的標準衡量,極端貧困的現象幾乎消失。而且,從1985年至2020年,預期壽命從71.7歲提高至80.2歲,差不多增加了10歲。
然而,因地鐵票價小幅上漲2019年的智利爆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社會動亂,年輕的示威者抗議精英階層和大企業貪婪成性、犯罪猖獗、學校追逐私利、養老金微薄……在此後的2021年總統大選中,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38歲的加夫列爾·博裏奇(Gabriel Boric)當選總統。
2019年的動亂令智利精英們錯愕不已:經濟各項指標都很優秀的智利,為什麽一些民眾卻不買賬?這被稱之為「智利悖論」。
出生於智利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安德森管理學院教授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作為」智利計劃「的親歷者之一,他用一本書【智利計劃——芝加哥小子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衰】回答了這個問題。觀察者網近期連線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圍繞智利新自由主義實驗的成敗,以及"智利悖論"展開交流。

【智利計劃】作者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近期與觀察者網連線觀察者網
【對話/觀察者網 高艷平 轉譯/趙丁琪】
「芝加哥小子」們否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
觀察者網:【智利計劃】這本書講述了拉美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開發中國家都關心的關鍵問題——那就是經濟增長與提升民眾福祉之間的關系。您能告訴我們是什麽促使您關註這一主題並寫下這本書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有兩件事促使我去研究這個課題,或許是三件事。
第一,智利經濟奇跡需要有人做深入研究。之前有些著作關註了智利所發生的一切,如經濟快速增長、人們擺脫了貧困等,但他們並沒有深入探討經濟發展背後的思潮,以及這是如何發生的。因此,我想試著了解智利經濟奇跡背後的原因。
1990年之後,智利結束了獨裁統治,我也想透過研究,去了解這一奇跡是否可能在民主統治下發生,因為經濟快速增長和脫貧很大部份時間是在獨裁統治下發生的。
第二,與以上兩個話題相關的是,其他新型市場經濟體可以從智利汲取哪些經驗。你們可能知道,拉丁美洲並不是一個增長非常快的地區,不像亞洲,中國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非常快。智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6%或7%的速度增長,這對拉丁美洲人來說已經非常快了。那麽,我們可以從中吸取什麽經驗呢?

【智利計劃】書中圖表截圖
第三個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我雖然住在美國,在美國生活了40年,但我出生在智利,我母親、姐姐和哥哥都還在智利。智利是一個有趣的國家,是我出生的地方,所以我很自然地被吸引去研究它。
觀察者網:我們都知道智利是新自由主義實驗的一個典型案例。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您在書中提到那些參與「智利計劃」的「芝加哥小子」否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否意味著你和那些芝加哥小子對「新自由主義」本身有不同的理解?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是的,你說得很對。新自由主義這個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它的真正含義一直在演變。
我認為,在過去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人們並不以此為榮。在西方,人們不喜歡被標上新自由主義者的標簽,因為這個詞更像是對他們的侮辱。如果你不同意某些人的觀點,你就會說他們是新自由主義者。
我查閱了科學文獻中「新自由主義」一詞的起源。
我發現,它最初是在1938年在巴黎舉行的一次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參加的會議上提出的。最初,新自由主義是為了擊敗專制主義和集體主義進行改良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它是將社會目標與市場制度予以整合的新方法,除了追逐利潤之外,還要關註社會問題。
直到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才演變成為一種更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它已與市場濫用、不良行為、壟斷、密謀勾結等聯系在一起。那我們應該使用哪種含義?
當我問所有的「芝加哥小子」:「你是新自由主義者嗎」的時候,他們都否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這裏他們意識裏的新自由主義當然是被貶義化的新自由主義。
然後我問他們,在經濟政策方面,你支持什麽主張?我記下了他們的主張,這就是這本書定義的新自由主義:即強調使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大多數社會問題並滿足社會需求,這包括提供和分配社會服務,如教育、老年人養老金、醫療、對藝術的扶持和公共交通等。
我為什麽從阿連德的支持者成為美國新自由主義實驗的中立者?
觀察者網:很有意思。當你談到1975年弗瑞德曼的智利之行及其休克療法在智利的實施時,我有一種感覺,您對此持肯定、至少是中立的態度。但你也說過,你是一個在20世紀70年代支持阿連德的智利社會主義道路的年輕人。這兩者之間有立場沖突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我的思想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阿連德於1970年11月上台,他的目標是建設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他仿效的其實是古巴。很多年輕人(包括年輕時的我)都支持他,因為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有很多不平等現象,很多暴力和壓迫。當然也因為在這裏有很多與菲德爾·卡斯楚、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有關的浪漫主義。

【智利計劃】書中截圖
我們支持智利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但是我們發現,盡管這些想法很好,在實踐中卻行不通。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人也發現了這一點,他們開始更多地轉向市場體系。我自己也參與了智利的轉型過程(作者曾任1983—1990期間任芝加哥小子學術導師艾爾·哈伯格的助理,那段時間智利的政策深受哈伯格學術理念的影響),這就是我的答案。
關於弗瑞德曼在1975年與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會面,當時他建議皮諾切特采取休克療法。我在書也描述了我不接受的部份。如你所說,我對此持中立態度,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建議幫助智利降低了高達500%的通貨膨脹率。
我們談論的不是12%或10%的通脹率,而是500%的通脹率,這對中國讀者而言可能是無法想象的。當時弗瑞德曼的休克療法讓通貨膨脹率從500%降到了20%。但代價也很高,大量的失業和貧困現象出現了。我只是描述了這些事件,並沒有深入探討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同於中國,拉美為什麽成了休克療法和新自由主義的樂土?
觀察者網:您提到弗瑞德曼在20世紀80年代存取了三次中國,弗瑞德曼本人還寫了一本【弗瑞德曼在中國】記錄了當時的情況。我們知道中國實行了漸進式改革,而不是他的休克療法,與之相比,為什麽智利成為了弗瑞德曼的「休克療法」和新自由主義的沃土?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我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在1975年3月弗瑞德曼第一次去智利之前,智利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1500%。中國在1980年代以來從未發生過1500%的通貨膨脹。我不知道在這之前是否有過,我想是沒有。
因此,智利一開始就面臨著這樣的局面:通貨膨脹率如此之高,以至於人們無法工作,因為他們所關心和擔心的就是通貨膨脹。而中國則是從一個穩定的經濟局面開始改革的,因此有機會逐步推進。
1988年,當弗瑞德曼在中國拜訪當時的領導人時,他沒有用「休克」這個詞,而是建議中國盡快放開匯率,中國沒有這樣做。現在,中國發展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我們現在可以認為,中國的做法是正確的。如果中國按照弗瑞德曼說的做了,也許不會有後來的奇跡。
觀察者網:另一個比較物件是阿根廷。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剛剛實施了「休克療法」改革,停止發行本國貨幣,經濟全面美元化,將國有資產大規模私有化、削減公共支出等。我們從一些媒體的報道和阿根廷左翼經濟學家那裏得知,米萊的改革引起了廣大民眾的不滿。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米萊似乎並沒有從自己鄰居智利那裏吸取教訓,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分兩部份回答,第一部份還是和我們之前說的有關。在2023年11月,也就是幾個月前,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在1個月內達到了25%,不是1年,而是1個月。
所以,米萊上台時的阿根廷經濟是非常糟糕的,他一開始即面臨月通貨膨脹率25%的情況,而且還在上升,這就解釋了為什麽米萊在上任後會立馬采取「休克療法」遏制通脹。
我不確定米萊是否從智利身上吸取了教訓。但是我現在很擔憂阿根廷的情況,因為阿根廷通貨膨脹率現在每月增長4%,這意味著阿根廷的年通貨膨脹率將超過50%。現在,阿根廷匯率每月浮動只有2%。因此,每月通貨膨脹率4%,意味著阿根廷的商品生產成本,每月要漲 4%。但匯率——也就是出口公司以當地貨幣獲得的收益,只上升了2%。這可能會導致危機。
這其中有很多教訓。因為智利當時就是這樣的,智利政府當時將匯率固定在某個錯誤的水平上,阿根廷可能正在重蹈覆轍。因此,阿根廷正討論的一個問題是,米萊什麽時候才能像米爾頓·弗瑞德曼在1988年為中國建議的那樣,放開匯率市場,允許讓市場來決定美元和歐元的價格。
因此,智利的案例的確有很多經驗教訓,我也希望米萊的改革能取得成功。2022年,阿根廷時隔多年再次贏得世界杯,但我們也希望阿根廷在經濟上也取得成功。
「休克療法有時候可能是需要的」
觀察者網:你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談論從1985年到2019年智利在很多方面都取得的成功:比如經濟穩步增長,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貧困率大幅下降等等,這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同樣是在「芝加哥小子」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治理之下,1985年至2019年和1973年至1983年的結果為何如此不同?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
是的,所以我認為這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智利在1973年至1983 年這一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所以不太成功,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將通貨膨脹率從1000%降到10%的代價非常高昂,而且非常困難。這意味著要付出代價。
第二個原因是,為了通脹問題的時候,智利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實施了與美元的固定匯率(280埃斯庫多兌換1美元)。在通脹飆升的情況下,這導致本幣迅速被高估,於是智利又采取小幅貶值和爬行釘住美元的政策,使得匯率能夠跟上通脹的速度。
中國一直在避免匯率被高估。因此,當中國人民幣匯率是8.27人民幣兌1美元時,美國一直在說,中國人民幣必須變成7,必須變成6。但是中國說,不行,我們是開發中國家,我們需要保持有管理的匯率才能推動出口和發展。因此,中國做了正確的選擇。

休克療法在1982年的智利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智利計劃】書中截圖
而「芝加哥小子」在智利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把匯率固定在錯誤的水平上,這在1982年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危機,讓一切都回到了原點,經濟負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一旦他們改正了錯誤,允許匯率以類似於中國的方式保持穩定,確保出口的競爭力,智利的經濟就重新開始增長。這就是智利快速增長的第二個時期。你看,這都與匯率有關。匯率在中國、智利和阿根廷都很重要。
觀察者網:所以,您認為新自由主義和休克療法在某些情況下也是積極的?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
在數學中,初始條件——也就是你從哪裏開始是重要的。當我們面對一個動態系統時,所有不同的變量都會引發變化。如果初始條件很糟糕,那麽你就必須采取特定的行動。如果初始條件沒那麽糟糕,你就可以循序漸進。因此,休克療法有時可能是必要的。
觀察者網:中國人的觀點可能和您不同,因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休克療法很糟糕,新自由主義也很有問題。但是,對於智利來說,看起來情況並非如此。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還是那句話,中國和智利面對的初始條件不同。非常不同。正如我所說,中國沒有經歷過1000%的通貨膨脹。所以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一切都會崩潰。例如,1923年德國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情況非常可怕,其後果之一就是希特勒最終奪取了政權。因為德國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0,000% ,比智利高出10倍。
因此,從哪裏開始很重要。總的來說,我同意我的中國同行們的看法,一般來說,應避免休克療法,最好是循序漸進。新自由主義是好是壞?這取決於你的理解 。我認為任何過於極端的東西都有問題。如果你只依賴市場就會有問題,但如果你完全不靠市場那問題就更嚴重了。所以新自由主義者有時過於依賴市場,對此,我們必須小心謹慎。我們必須增加更多的社會政策和社會安全體系之類的東西。
觀察者網:所以,如果我們談論教育系統或醫療保健系統,新自由主義也許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您同意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我同意你對教育問題的看法。我們需要有一個非常好的公共教育系統,在醫療系統方面,我們需要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優質的醫療資源。而如果只允許市場運作,就會造成很多資源的緊張,產生很多的不平等。使得中下層階級無法實作階級躍升。
一個社會必須給予中產階級和中下層人群提供的最重要的社會福利,包括高品質的公共教育體系,使得他們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而且不需要付錢,這是非常必要的。
智利忽視了「橫向不平等」
觀察者網:下一個問題是關於2019年智利的民眾叛亂的。您在書中提到了「智利的悖論」:也就是,為什麽拉美地區最成功、各項經濟指標都表現最好的國家,卻遭遇了一場叛亂,抗議者聲稱自己生活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中。您的研究發現了什麽?您能解釋一下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我認為,一旦人們意識到國家正在發展壯大,老百姓就會希望獲得更好的福利,更多的平等。
但是,智利在發展過程中有兩件事沒有引起當局的重視:
其一,即使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大幅減少,但不平等依然存在。智利曾經有一半的人口是窮人,而到2019年,貧困率已經下降到了6%。
這看起來非常成功。但智利社會存在很多不平等,不平等的社會導致了緊張的局勢和政治問題。這就是2019年叛亂的原因,我們稱之為叛亂。我稱之為「智利的悖論」。
其二,我認為智利存在「橫向不平等」現象,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不平等。重要的不僅僅是收入的不平等,還有社會交往、隔離政策、種族歧視以及便利設施和公共品的提供,也包括精英階層對待普通民眾的方式。在這方面,智利往往表現糟糕。那些富人和精英是勢利小人,他們看不起窮人,他們不會友好地對待窮人,比如富人和精英不邀請窮人到家裏做客,這種關系不平等會引起人們的不滿。

在動亂之後的2021年智利大選中,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加夫列爾·博裏奇當選總統
這就是為什麽智利的示威者說,我們希望得到有尊嚴地對待。「尊嚴」這個詞變得非常重要,尊嚴不僅關乎金錢,它還關系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新自由主義已經滅亡?
觀察者網:您結尾提出了一個問題「新自由主義已經滅亡?」智利2019年的抗議者也打著終結「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口號,隨後2021年智利左翼政黨勝選,同時我們看到拉美國家的粉紅浪潮風起雲湧,當然也有極右翼的上台。您怎麽看待新自由主義在智利的未來?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如果我們把新自由主義定義為過度依賴市場,那麽這種新自由主義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的政策依賴於政府的支持,依賴於更多的稅收、更多的公共支出,諸如此類。因此,我認為這是事實。
另一方面,我認為有一點變化的是,在 2019年的叛亂之後,人們認為對政府、公共部門和左翼的依賴會迅速增加。但現在情況變得更加溫和。這個過程仍在持續,不過比我想象的要緩慢一些。但我仍然認為,我們不會回到過去那種把市場作為唯一決定因素的體制。我們會比以前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
觀察者網:即便全球範圍來看,新自由主義也在不可避免走向衰退。比如看看美國和歐洲如何出台產業保護政策,與中國展開技術競爭,政府已經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您如何看待這個新趨勢?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我認為我們正朝著政府幹預越來越多的方向發展。我認為這非常重要。但同時我希望我們不要在這個方向上走得太遠,以至於走到另一個極端。
我尤其擔心保護主義。我認為,美國和歐洲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試圖限制中國電動汽車的銷售數量這樣的事情,並不是一件好事。此外,中國試圖阻止從美國或歐洲進口某些產品,同樣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需要一些政府幹預,但不要太多,市場競爭在某些情況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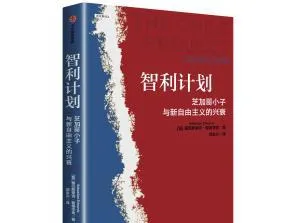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