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疫苗不得先介紹下病毒。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它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之一——人類有記載的與天花鬥爭的歷史就有三千年之久。
天花病毒曾肆虐全球:僅18世紀,歐洲死於天花的人數在 1.5億 以上。
1796年,英國鄉村赤腳大夫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的眼睛盯在了當地擠奶女工莎拉·奈爾梅斯(Sarah Nelmes)紅潤的皮膚上。
Nelmes因為經常接觸奶牛,感染一種當地人稱之為「牛痘」的疾病——雙手或者其他皮膚上出現丘疹。但除此之外,這種病並不會對人體造成多大的傷害,更重要的是,像Nelmes一樣感染「牛痘」的擠奶女工們,幾乎不會感染當時最可怕的流行病——天花。

Jenne決定從 Nelmes雙手丘疹後的疤痕膿液中提取部份樣本,並將其註射到名叫詹姆士·菲普斯(James Phipps)的小男孩手臂中。當詹納用第二根針紮Phipps的時候,他向其體內註射了大量天花病毒,但Phipps仍然保持著健康。

這個孩子獲得了對天花病毒奇跡般的免疫力。
這一革命性且極其不道德的實驗將世界推入了被稱為「疫苗」(vaccine)的時代,這個詞的詞源包含了對拉丁詞vacca的敬意——它的意思是「奶牛」。
由於Jenne的疫苗,免疫科學誕生了。

而後的180年間,億萬人透過接種「牛痘」的方式獲得了對天花病毒的免疫力,直到世衛組織宣布全世界範圍已經消滅了天花,人類終於從技術上阻斷了這種病毒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阻斷」不等於「治療」。
病毒結構非常簡單,它只帶著自己的遺傳物質(DNA或者RNA):它僅僅只提供一張圖紙,而生產則由宿主細胞的生產線來完成。在很大程度上,病毒所利用的生理途徑和宿主細胞是一樣的,所以藥物「治療」病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一旦病毒進入體內,殺死它也就是殺死自己。

不過,人類已經有一些藥物和手段能夠抑制病毒,比如因對抗愛滋病而誕生的「雞尾酒療法」——透過三種或三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來減少單一用藥產生的抗藥性,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復制,使被破壞的機體免疫功能部份甚至全部恢復,從而延緩病程進展。
除此之外, 疫苗是最有效的阻斷病毒的手段,核心思想即「防範於未然」。
Jenne的「疫苗接種」是人類偶得的技能——將病毒減毒滅活向人體植入以喚起自身免疫系統的應答,從而建立起對該病毒的免疫力。
可「疫苗」之路,艱巨且長。
人類在1981年第一次發現和報道了愛滋病,很快就在1983年分離到了愛滋病病毒。美國總統柯林頓在1997年信心十足地宣布了「愛滋病疫苗的曼哈頓工程」,其重要性可媲美於羅斯福總統在1939年宣布的「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和甘迺迪總統1961年宣布的「載人登月的曼哈頓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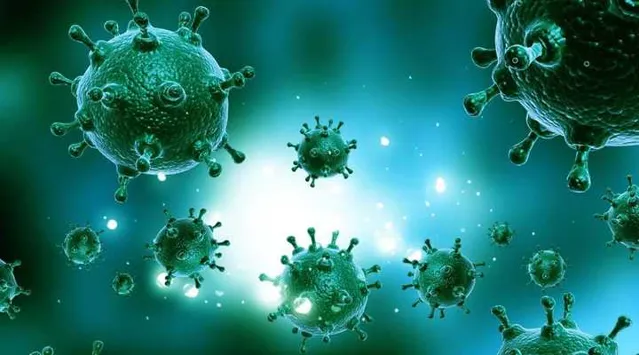
然而,當「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和「載人登月的曼哈頓工程」相繼用了6年和8年的時間順利成功後,「愛滋病疫苗的曼哈頓工程」在宣布的20多年之後,艾滋疫苗仍舊還是個夢想。
同樣的情況還有非典:2003年的非典距今已經過去了17年,直至今日,我們也無法獲得非典疫苗。

Jenne以極不道德的方式做了人體試驗,且幸運的獲得了最好結果,而從現代科研角度來看,研制疫苗都需要經過以下過程和步驟:濾出滅活的病毒,建立合格的動物模型,小量試制、中間試驗、送審和臨床研究幾個階段,全部通關才能算研制成功。
其中,「建立合格的動物模型」這一關,往往是疫苗研制的瓶頸:大部份病毒並非人畜共患,當拿某種病毒感染試驗動物時,它們不一定出現和人類一致的臨床表現,也就是說該種動物屬於不易感動物。這樣一來,透過不易感動物得到的實驗結果是不準確的。
此外,相當一部份病毒的結構與和基因片段都不穩定,總在不斷變化之中,好不容易研制出針對一種病毒的疫苗,不料想下次病毒流行時又變成另一種病毒亞種;有的病毒存在於人體內就在不停變化之中,難以穩定在一種恒定狀態。
疫苗研發之難,可見一斑。
更多精彩歡迎搜尋掃碼關註公眾號:三仟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