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位大哥的視訊後,我專門去了次紹興,和他聊了2天。
他住在紹興城郊的一處村落,被工廠和工地包圍。出租屋大約15平米,他住了16年,現在月租金300元。
他的房間很小,只有15平米,一進門,堆著滿滿的廢品,可墻壁、屋檐下掛著一幅幅色彩艷麗的油畫。他跟我說,前幾年,因為房間要堆廢品,放不下自己的畫。從2016年到2019年,整整3年,位光明燒掉了自己的每一幅畫,總數接近500張。

白天,他賣掉一斤廢紙殼,能換來1塊錢;賣一斤塑膠瓶,能換1塊2,但他卻要買上萬元的油畫顏料,用的是75元一支的英國喬琴和175元一支的林布蘭,都是進口的。
入夜,他坐在廢品堆裏,臨摹莫奈、夏爾丹、列維坦、蒙森德,最喜歡的畫家裏,有雷諾亞和郭潤文。
一開始,我和他打了個采訪電話,奇怪的是,電話裏他卻基本不提畫畫,只說之前的打工經歷。他不想渲染自己過得有多苦,而是說自己「樂觀、順其自然」。
「無所謂,為了生活,能畫什麽畫什麽,以後也不會多想。」
他甚至像絲毫不在意以後能不能畫畫那樣說。他顯然在防備著什麽。
我不知道為什麽會這樣,立馬買了去紹興的票。我想聽他說說真話。
見面那天,位光明穿了一件灰色的舊襯衣、一條布滿顏料的褲子、一雙拖鞋,在村委會門口等我。我跟著他拐過一條條巷子,來到一扇低矮的鐵門前。


當我進入這間陋室的時候,位光明顯得不好意思,「這裏太小了」。
他讓我坐下,又從櫃子裏拿出一個瓷罐,客戶送他的,說是很好的龍井茶。期間,他特意在凳子上鋪了一條毛巾,用開水燙了三次碗。

位光明不是一開始就收獲他人關註的。恰恰相反,剛開始畫油畫時,他時刻被這個世界提醒: 你是個賣廢品的,油畫不屬於你,你怎麽可能畫好畫?
這種「不屬於你」的感覺他太熟悉了。
他從小被親生父母過繼給姑父,不管是原生家庭還是後來的,哪個家庭都不屬於他,他甚至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他被當兵的姑父帶到甘肅的農墾農場,自己省生活費買了一本【紅樓夢】,被姑父當場撕毀。姑父說,這是教人談戀愛的書,他不能和當地女孩談戀愛,因為他不屬於那裏,會惹麻煩。
長大後,他想畫畫,沒有老師教,也沒有錢學,位光明只能花一百塊,收來一台廢棄的破電腦,自己修好,開始在網上搜教程。
他加了畫家群,人家釋出一張作品,他在底下請教:這個顏色怎麽調?幾句話就能說明白的事,人家模棱兩可糊弄過去,就是不願意告訴他。
他自己摸索,不收廢品的時候,就在家裏畫。沒錢買畫架,就只買畫布,自己裁成50x60厘米,粘在墻上貼的木板上,趴在墻上畫。
至今,這些墻上的木板還能看見各種顏料,和他寫下的繪畫技巧:「樹:用筆蘸深赭石;遠山:先上中黃。」

位光明知道自己畫得不好,但有些進步後,就想拍下來,發到沒有人看的微博上,肯定自己。兩年來偶爾有人點贊,他特意在評論裏回復人家:「謝謝你的點贊。」
但更多的是辛辣的嘲諷。比如,一副名為【春天的黎明】的畫,他把天色畫成了紫色,發到貼吧,就有人說:「這是秋季的暴雨,我勸你出去擡起你的腦殼兒看看天空吧。」
還有人說,「你畫畫就是在浪費顏料。」
後來他把畫和生活都分享出去,讓人看到了他的真實身份。這下別人不說他的畫了,直接改為攻擊他:「收廢品的,白天收,晚上偷。」
這句話刺痛了他。收廢品的就不能畫畫嗎?他憋著氣,在畫架上寫下三句話——
「餓死不乞討,餓死不偷盜,餓死不低頭。」

此時,這塊畫板就在我面前,可是那些畫卻沒了。500張,付諸一炬。
他不想留,「不好看的東西沒必要留」。也不想送人,「沒必要,都看不懂。」
他的屋裏充斥著太多雜物,擺成山的廢品,收來的古董投影機十幾個,但卻容不下那些不好看的畫。
位光明最初開始動筆,是畫死人的。
那時他才二十四歲,要畫畫就沒時間賺錢,他就試著用畫畫去賺錢。他買了畫板去廣州天河廣場的地下通道裏畫,把自己當街頭藝人。沒人的時候,他就畫名人像,等人圍過來問生意,就要個幾十塊。有時候一天也畫不像一副,人家就不給錢。
大多數時候,他連住旅館的錢都賺不到。
廣東有個習俗,老年人去世了,要畫遺像,很多人拿來放了十幾年的老照片讓他畫,用來當遺像。別人說,位光明畫這個晦氣,不願意接近他。位光明就不畫了,又到肇慶鼎湖、四會的一些小村莊畫牌坊,畫關公和梅蘭竹菊,寓意吉祥如意。
在村莊裏寫生,每三天就要換個地方,不然沒客戶不說,還會被本地畫家打壓。
他總是這樣,一邊跑,一邊畫。
逃也似的來到一個地方,看能不能活下去,再做想做的事。這種生活,對他來說不只是畫畫那幾年,而是小半輩子。
1972年出生,十七歲離開甘肅的農墾農場,又在高三輟學離家。原因是兩個弟弟比他早結婚,按照村裏習俗,他這個大哥要被全村人看不起。
之後,他經歷了好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在上海的碼頭挑貨,在遼寧的火車站卸煤,在廣東的工地被拖欠薪資,又被偷得一無所有。

他被頻繁地拖欠工錢,「那是90年代,工頭不給外地工發錢。反抗的人,工頭一個電話打去說沒有暫住證,就會被關進收容所。」
實在沒錢的時候,他就睡公園、睡大街,有次睡在街上,半夜被踹醒搶劫。他沒錢,腿上被人捅了一刀,縫了17針,傷痕現在還在,十厘米長。
位光明告訴我,從1991年到1997年,他在廣東幹了5、6年,連3000元都沒賺到,有一年還被騙走6000多塊。有次,錢包被人偷光,他沿著鐵路走了好幾天,靠摘農民種在路邊的胡蘿蔔、甘蔗填肚子。
「年輕的時候自以為讀了不少書,想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幾年以後才明白,自己不過就是馬路邊的一粒沙,什麽都不是,比我強的人多的是。」
電影【鐵達尼號】上映那年,位光明看到傑克給露絲畫素描,他覺得自己用點心,能畫得比他好。 看完電影後,他買來幾根一毛錢的碳筆,白天沿著107國道撿垃圾,晚上在廉價旅店練習畫畫。
2002年春節,位光明遇到了現在的妻子。他在街上畫畫,妻子一連幾天都來看他,倆人就這麽在一起了。他想到自己親生父親家和養父家都不要他,索性入贅。他有了四個兒子,都跟妻子姓。
但成家之後,他無法讓妻子跟著自己四處流浪。 如果說,傑克是愛上露絲開始作畫,那麽位光明就是愛上妻子之後,決定不畫了。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嘛」,他放棄了畫畫,一心一意要賺錢養家。
2005年,位光明離家掙錢,剛來到紹興的時候,就到了這座城市東北角的邊緣。他去石料廠打工,實在太苦,發現收廢品挺自由,就幹了這個。
他挨家挨戶去街面上收廢品,這裏是城市的邊緣,分布著各種藥廠、化纖廠、服裝廠,街上的店面卻不多,收多少廢品全看運氣。多的時候一天能收幾百塊,少的時候就幾十塊。
遇上下雨天,連出去碰運氣的機會都沒了——廢品被淋濕的話,就賣不到價錢。
轉折出現在11年後。
一個塑膠廠的老板娘聽說他會畫畫,覺得不可能,便掏出100塊錢,讓他給自己畫一幅。
位光明心裏對畫畫的熱情又被點燃。他花去200多,買了些畫布和顏料,又畫了五六遍,才勉強拿給老板娘。
拿給老板娘看的時候,他能觀察到對方「很勉強,也不喜歡,含糊著答應幾句」。但老板娘沒多說什麽,又掏了100塊,還把廠裏的廢品都包給了他。
他終於有了份還算穩定的收入,不用再跑街面。
他想,是時候重新握起畫筆了。
接近三年的時間裏,他一邊收廢品,一邊在無人知曉的時候畫油畫。他的手指粗大,布滿老繭,不靈活,看手機的時候用食指直往螢幕上戳,卻夾得穩畫筆。
在這間破舊的小屋裏,他不用再跑了。 別人眼裏的陋室,已經是他努力爭取過,一個很滿意的可以繼續夢想、穩定生活的場景了。
位光明的房子很高,靠近高速路,他曾帶著我翻高速欄桿過了一次馬路,去隔壁的村子吃一碗餛飩,兩個人花費8元,再走回來。
在巷子裏走的時候,他熟練地穿梭、拐彎,又回過頭囑咐我:「遇到頭發花白的人靠近,要躲遠一點,這裏很多人沒低保,要是被碰瓷,就是一輩子的官司。」
聊到一半,突然一群人闖進了位光明的家門。打頭的年輕人有張圓臉,穿黑色T恤,不客氣地走到最裏面,擺弄著放在床上的幾個畫架。
「光明,給我送一幅畫!」
位光明有點不知所措,正要回答的時候,另一個中年人環顧了一圈小屋,然後指著一個生銹的液化氣瓶說,「這是什麽東西,安全隱患,趕緊搬走。」
位光明解釋,這個裏頭沒有氣,都廢棄了,不會不安全。中年人聲音更大了,像是在耍威風:「那也不行!」
這時有人發現了我。位光明連忙介紹,這是從北京來采訪的。這群人立馬變得客氣,還有人掏出手機來拍。
他們出去後,位光明很快向我解釋,那個要畫的人是村主任。這裏外來人口多,要定期檢查流動人口和安全隱患。他說村主任「平時不這樣,今天是喝了酒」。
他們早就習慣了畫畫的位光明,與其看他畫什麽,更關心的是村裏來了個新面孔。

位光明開啟布滿灰塵的電腦,等待幾分鐘開機,點開電影【終結者】,和我一起看了一段,跟我說:「男主身上的金屬能像瀝青一樣流動,很神奇」。
他說,自己很愛看美國科幻片,覺得裏面的畫面很美,想象力很豐富,對畫畫有好處。
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練習畫畫的機會,哪怕是透過看電影。
畫的時間久了,位光明也心疼。顏料怎麽也是一筆支出。畫畫後,他還因為經常要動腦子而抽起了煙。有時候想不出來就急得薅頭發,自嘲自己因為畫畫「變成了清朝人」。懷疑自己的時候,他一個月只畫一兩幅。
但現在,他已經不用再偷偷摸摸燒掉自己的畫了,開始有人看了他的畫,願意掏錢買下。
有了訂單,他不僅不用燒,還可以光明正大地把畫掛在屋檐下、墻壁上。油畫不容易幹,他要晾曬半個月,等幹透了,再給客戶寄出去。

這個村裏的大爺大媽們,都習慣了「又收廢品又愛畫畫的光明」。他們看不懂畫,只會說像不像,但他們知道這東西能賺錢,就不覺得奇怪了。
連位光明的妻子也這麽覺得。現在,他的妻子在老家帶孩子,長時間相隔異地讓兩個人疏於聯系。雖然妻子和兒子,都知道他畫油畫,但沒人問過他,只知道他在外打工,靠畫畫每月能打回家7000元。
能不能賺錢,依舊是大多數人衡量一件事值不值做的唯一標準。
位光明也有自己的考量。
為了改善油畫的效果,他把原來十幾塊一支的顏料換成了進口貨。
他說,貴的顏料品質確實好,畫出來光澤感強,而且不容易幹裂,「就算裂了也是蜘蛛網似的紋路」。便宜的顏料17元一支,稍微塗厚一點,顏料就裂出縫,手一摳就往下掉。
你要問他值嗎,他就會說:「你看西方藝術家畫的油畫,顏色留存了幾百年。」
位光明總愛在夜晚降臨後開始繪畫。
那時候他收工回了家,關上房門,就不再是臟兮兮的廢品回收員了。他從一排畫框裏取出一個,放在畫架上,開始今天的作品,臨摹莫奈、夏爾丹、列維坦、蒙森德。
他真正的靈感降臨經常是在後半夜,猛地醒來,感覺心裏有什麽在噴湧,不抒發不暢快。他翻身起床,迅速拿起畫筆,擠出顏料,一直畫到早晨。
「畫畫就是一支很小的筆,不斷地點點點,一直點到手抽筋,一直點到腦子崩潰,然後狠狠地抽自己兩耳光,再看看有什麽不美的地方,繼續修補。」
但多數情況下他不這樣。他通常兩個小時就能畫好一張油畫,以應付那些沒完沒了的商業訂單。作為油畫,他的作品賣得很便宜,三五百一幅,因為在快手展示了自己,不少人找他畫,訂單都排到了三個多月之後。
第一個訂單出現在2019年8月,此前他在快手發了一些自己的畫,於是有人給他留言:你的畫賣不賣?
他試探性地加了微信,對方發來300元,他花了幾個小時畫好,拍下來發到快手,又寄了出去。
找他來畫畫的人慢慢多了,快手上越來越多人鼓勵他。有東北的客戶讓他畫雪景,他畫了木屋、炊煙和坐雪橇的人。有客戶一次性下單二三十副,他幾乎要畫半個多月。
有時候一幅畫發到網上,很多人發私信說再畫一遍,想買。 一張臨摹列維坦的藍色矢車菊,位光明畫了17遍,有點無奈。
「為了生活,我總是畫同一幅畫。」

現在,快手上的訂單讓他每個月又多了四五千的收入。這樣,一個月他能寄回家七千元。妻子沒工作,最小的兒子剛上幼稚園,老二、老三讀初中,老大剛從汽修畢業,全靠位光明維持整個家庭的生計。
他算了一筆賬:小孩還在上學,之後長大成人壓力更大,四個兒子要四套房。按鎮裏的房價來算,每套首付起碼要準備十多萬,彩禮一人也要二十萬,加起來就是一百多萬。
他不敢想,一想頭發要全掉光。 「有時候很奇怪,富裕人家的老板都是生女兒,我們這窮光蛋,又生兒子。」
為了省點生活費,他一般就吃泡面,或者速凍水餃。畫得入迷時,飯也不吃了。
提到兒子,位光明說疫情之後就沒回過家,兒子基本都不和自己說話。父親節的時候,只有上幼稚園的小兒子給他打來電話,聊了幾句。「可能兒子大了,和父母就不親了。」
我問位光明,墻壁最上面用鉛筆寫著的幾個大字「周恩銘畫畫平台」是什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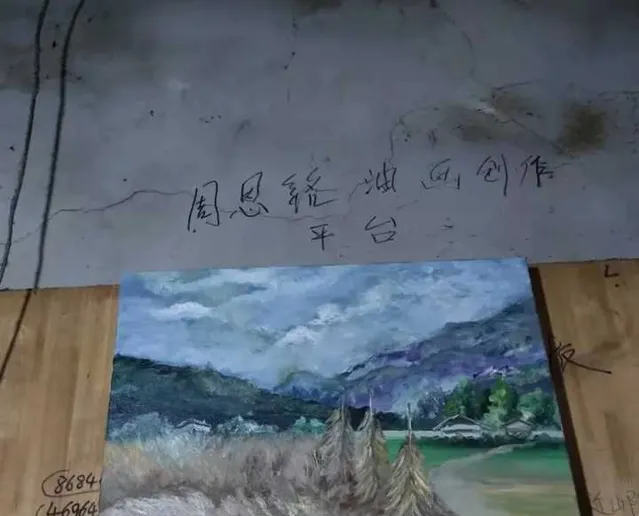
字跡下面是墻上的畫板——他原先就趴在這裏畫
他說,那是他親生父母取的原名,他一直沒有忘記,還想著以後落葉歸根。
「我理想的好日子也有,就是能睡到自然醒,衣食無憂。到那時候,我就回到妻子待的柴湖鎮,畫點自己想畫的東西。」
一個人的夢想有多大,有時窮其一生無法實作,一個人的夢想有多小,有時只是想回到自己入贅的地方。
6
回了出租屋,他剛打算畫畫,又有陌生人打來電話。他在快手的視訊上熱搜後第三天,全國各地打來了40多個電話,兩家媒體上門拍攝,從早晨8點到晚上10點半,位光明都在接受記者采訪。「同樣的話說了三遍,怪累的。」
高密度的受訪意味著他沒時間畫畫。電話裏,對方想要采訪他,他拒絕了。對方又提出能幫他聯系繪畫教授,可以去聽課,他說,「沒那個時間。一個月去幾個小時還行,其余時間要收廢品、要畫畫,賺錢。」也拒絕了。
他明白自己現在首要目的還是用繪畫維持生計,為了兒子們的房子、婚事,一遍遍地畫同一幅畫。
位光明曾經說過,他最喜歡的國內畫家是郭潤文,說他的畫很古典雅致。他有一個願望,就是能親眼看看郭潤文畫畫。
郭潤文常畫人像,但位光明卻不能。他要謀生,畫人像不掙錢,他只能畫些艷麗的風景畫,客戶喜歡、好賣。還「不能畫太寫實的,費功夫不說,畫得有一絲不像,客戶就不付錢了。」
不久前,快手幫他聯系到了郭潤文教授,說可以交流。位光明卻退縮了,覺得自己很卑微,「怎麽可能去見人家?」
後來郭潤文教授對他送上一句寄語:畫畫是快樂的。
所有的訊息回完之後,位光明開始畫一副「海浪拍打帆船」的油畫。

畫完礁石、海浪之後,快到收尾的地方了,他從堆滿廢品的櫃子旁拿出一根極細的勾線筆,蘸取白色,說要畫幾只卡玫基。這種鳥一生不斷遷徙,卻總是能快速適應環境,無論到了什麽樣的海岸,它們都能用自己的方式飛翔。
他很快速地在畫布上面勾出一只卡玫基,在海浪上優雅地飛舞。
他畫著,房間裏還有另一幅畫在等待晾幹。只是天一熱,小屋裏會飛進來蚊子,關門後又顯得悶。有蚊子飛進來,被粘在顏料上,成為一個小黑點。
他不去管,他繼續作畫。
等畫幹了,手一彈,就沒了。

看到這個問題,我想到曾經有人提醒我說,如果你沒條件去實作,就千萬不要跟別人說你有夢想,這種話他們是不會聽的。
位光明其實就是這樣,他整個追夢過程,不是打雞血,而是他現在如果只能生活,就生活,如果生活好過了,我就再精進一點。他的人生就是在畫畫這件事上,一點又一點。
這個過程裏,他沒有多過激,沒有多傳奇,也沒有超出常人的犧牲。他理性地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最後一點點做到了。聽著好像挺容易的,怎麽就那麽多人沒實作呢?
我想借著他的故事說,如果把想做的事等同於夢想的話。那麽夢想不是一件等同於錢的事,更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它應該是一個你不給自己留借口,一點點靠近的事。
這也是我的小小私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