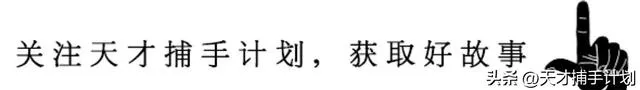
一個交往多時的人,背後也可能隱藏著多重身份。有時那真的只是私密,但有時候,背後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個女孩,在和男朋友相處時,發現對方有不同的名字。但女孩沒往心裏去,她以為這都是小事。
當這些身份被一層一層揭開的時候,女孩已經大禍臨頭了。
跨年的鐘聲如約響起,小城四下鞭炮齊鳴,震徹夜空。
一陣喧鬧過後,街道堪堪歸於平靜,離開KTV卻還未盡興的青年男女借著酒勁把街道當做舞台,不時幹嚎幾句。
一個男人跪坐在鑫蘭酒店203房間。
聲音漸近,透過窗戶,恍惚間他似乎聽到一句:「為什麽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問,我不能。」
男人心頭一顫,嘴唇蠕動,喃喃哼出下一句,「擁在懷中,直到她變冷。」
副歌傳來,撕心裂肺,已是幾十米開外。
元旦是一年伊始,代表萬物更新,但對於此刻203房裏的男人來說,卻截然相反。
懷中的女人正在慢慢變冷,他知道,自己該走了。


刑警隊到達鑫蘭酒店的時候,派出所民警正在大堂試圖和蜷縮在沙發角落的保潔大姐進行溝通——她已經嚇到幾乎失語。
旁邊坐著一對青年男女,男孩把女孩箍在懷裏,女孩背向眾人,也止不住地哭。
隊長簡單問了問現場情況。1月4日,這對年輕情侶到鑫蘭酒店前台反應自己入住的203房有異味,保潔阿姨被安排前去打掃。
203房背陰,通風有限,如果不是遇到高溫天氣,房間經常彌漫著一股難以名狀的餿味。對此,保潔阿姨習以為常。
她裏裏外外把房間打掃了一通,還不忘噴上了空氣清新劑。濃烈的化學香氣暫時掩蓋住了異味。
可晚上這對小情侶回到酒店,還是覺得房間裏氣味有點古怪,他們當時沒有理會。但到了第二天上午,氣味卻更加明顯。
小夥子覺得像是死耗子的臭味,兩人再次到前台,請他們安排人去打掃一下房間。
這一次,連保潔阿姨自己都聞到了這股「怪味」,她從衛生間一路嗅到床邊,發覺這股臭味是從床下散發出來的。
「難不成真有死耗子?」阿姨也犯了嘀咕。
床腳的縫隙太小,掃帚伸不進去,阿姨叫上電工師傅,讓他把床墊擡起來看看。
電工腰馬合一,雙手一擡,阿姨卻一聲尖叫,踉蹌地跑下樓去。
床下有人。確切地說,是一個死人。
掀開床墊,屍臭得以肆意散發,法醫胡豆被嗆得直擺手。
屍體已經腐敗,從身形能看出是一具女屍。她身體微曲,頭腳與床向一致,被好好側放在四塊床板中間,頭下甚至還枕著一件衣服。紫黑的面部早就看不清長相,一身睡衣睡褲還穿得完好。
法醫胡豆看了看屍體,只有脖子上有一道勒痕,屍表沒有其他明顯外傷,房間內也沒有打鬥痕跡。
可以肯定的是,女孩絕不是自殺,不然屍體不會自己跑去床下,應該是被勒死的。這個203房間就是案發現場。
聽了胡豆的意見,隊長稍微松了一口氣。
雖然幾天的打掃已經破壞了現場,但如果胡豆的判斷沒錯,只要能找到入住過這個房間的人,就能找到兇手。
確定了自己和屍體隔著一張席夢思床墊背對背睡了一天一夜,小情侶癱坐在地,甚至忘記了哭喊。看樣子,他們是兇手的可能性很小。
隊長一邊安排人給他們心理疏導,一邊下令封鎖現場,除了技術員留下勘察現場,所有在場人員帶回刑警隊開展詢問。
幾天之後,幾百公裏之外,一個海濱小城的出租屋裏,那個入住過203房間的男人正用手機不斷搜尋著新聞。他已經三天沒有出門了。
突然,一條貼吧訊息引起了他的註意:【痛失愛女,五旬老漢停棺酒店欲自殺】。
貼文的配圖是一群人拉著一條橫幅,上書「還我女兒!」一個老漢站在隊伍的最前面,手中握著一把砍刀,就架在自己脖子上。
老漢的對面,是蓄勢待發的特警和數以百計的圍觀群眾。
帖文說,老漢的女兒莫名其妙死在酒店客房,他帶領親戚把棺材擡到酒店門口,要向酒店討要說法,酒店老板態度強硬,擺明了與我何幹的架勢。老漢情緒失控,聲稱要當著眾人血濺當場,讓冷漠的酒店老板再背上一條人命。
貼文言不盡實,但男人知道,自己做的事終於敗露了。
那個差點成了他嶽父的人,如今成了貼文裏揮刀自殘的老漢。
但至少,有人給女人收屍了。
這一刻,他竟有些釋然。

隊長越來越覺得自己低估了這案子的難度。
從入住記錄上看,和死者安潔登記入住的這個男人叫方遠,人口系統裏的資訊顯示他來自四川。可隊長讓四川警方調來方遠的照片交給酒店服務員辨認,服務員卻非常篤定地說,照片裏的男人和當天入住的男人不是一人。
入住人和登記人不是同一個?隊長從來沒想過這樣的情況。
酒店監控畫質低劣,很難辨認來往住客的身形,只好把死者安潔的父親請來,讓他對視訊裏的男人進行辨認。
安潔的父親看了幾眼便十分肯定地說,視訊裏的男人就是安潔的前男友,叫盧澤平。
據安父反映,盧澤平是安徽蕪湖人,和安潔交往了兩年多,兩人近期鬧了點矛盾,可能是安潔想要分手,但盧澤平不同意。
雖說盧澤平在麗江有個服裝廠,算是比較富裕,可他平時脾氣暴躁,加上年紀比安潔大得多,安父也不同意兩人在一起。
根據安父的描述,專案組在人口系統裏把蕪湖地區與盧澤平同名的人找了個遍,連諧音的都沒放過,卻根本沒有「盧澤平」這麽一號人。
從方遠到盧澤平,兩個名字居然都找不到對應的人,這已經不能算巧合了。
專案組也得到了四川警方反饋的訊息,這個叫方遠的人身份證丟了有幾年了,現在人正在四川,近期沒有出過門。
也就是說,這個畫面中的男人從入住登記開始,就用了一個假身份。甚至更早先,和安潔談戀愛時就用的是假身份了。
案件開始撲朔迷離。身份資訊對不上號,只能從監控入手。
民警一路追著男人在監控裏的軌跡,發現他離開酒店後到了縣城客運站,最後一次出現在畫面裏,是購買了一張前往昆明的車票。
昆明,還有安父說的那家盧澤平開在麗江古城的服裝店——追擊的路線似乎明朗了不少。
安父的情緒越來越激動,每天都到賓館門口去鬧,隊長下了死命令。組裏人兵分兩路,一組去昆明,一組去麗江,為了防止事態擴大,一定要盡快破案。
偵查員大林和法醫胡豆一路奔波趕到麗江,來不及欣賞雪山古城,立即就開始搜尋那家名叫「靚麗百分百」的服裝店。
地圖APP上顯示,還真有這麽一家店。大林和胡豆依據地圖的指示找了過去,可從街頭走到街尾,這店憑空「消失」了。
兩人只能挨家挨戶地詢問,可問了一圈,周圍的街坊也沒說出什麽,胡豆有些煩躁,嚷嚷著走累了要休息一下。 兩人找到一家關著門的商鋪,在台階上坐下抽煙。
兩支煙燃盡,大林站起身來拍拍屁股準備走,一回頭,發現自己身後這家大門緊閉的店居然沒有招牌!

大林靈光一閃,一把拉過胡豆,「老胡,你說會不會就是這家!」
胡豆將信將疑,兩人走近一看,卷簾門上貼了一張轉讓資訊,大林趕忙撥通了上面留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旁邊裁縫店的大爺,看到兩人在商鋪門口,大爺走了過來,熱情地問他們是不是要租房。
「不是,我們想問一下這家店以前是不是賣女裝的?」胡豆遞了一支煙過去。
大爺說是,「但是前幾天老板說要轉讓,叫我幫他們處理下。」
大林和胡豆對望一眼,有戲。
大林迫不及待地問大爺,這家店的老板叫什麽名字。
「老板麽叫盧剛嘛,一般麽都是老盧老盧地喊,我麽年紀大點,叫他小盧。」
大爺的回答讓胡豆和大林有些疑惑,這盧剛又是誰?
兩人向大爺表明身份,說明來意,可大爺明顯不相信那個盧剛和警方要找的「盧澤平」有什麽關系。
「盧剛這個人可以的嘛,良心好的,他有個憨包表妹,好像叫李慧,什麽也不會幹,他說他都照顧了十多年了嘛。」大爺一臉惋惜的表情。
根據大爺的話,盧剛兩年前來到麗江,開了這家店。沒過多久,後面又來了一個叫安潔的小姑娘,恰好來自雲南金沙。盧剛跟大家介紹說安潔是他的女朋友。
看來這個盧剛就是他們要找的「盧澤平」。
又一個新身份。
大林越聽越覺得迷糊,這男人為什麽要辦這麽多假名?難道是早有預謀要殺安潔?
大林追問道,「大爺,你有沒有見過盧剛的身份證件,或者其他有什麽能證明身份的東西?」
大爺皺起了眉頭,半晌才說,自己倒真從來沒見過盧剛的證件,連營業執照上的名字寫的都是他另一個妹妹,周媛。
「哦,對了,這次轉店,就是周媛叫我幫她轉的。」大爺補充道。
大林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他想不明白,為什麽這個男人要一直隱瞞身份,太刻意了。
見沒有突破,胡豆又問了一句還有沒有其他有價值的線索。大爺倒是很配合,抓耳撓腮,仔細回憶,又說出一條重磅線索——每逢寒暑假,會有一個大學生來店裏幫忙。「我聽到過幾次他叫盧剛‘爸爸’,有人的時候,又叫他老盧。」
大林和胡豆趕緊把調查的情況反饋給隊長,比對結果顯示,周媛和那個大學生都是湖北襄樊人。
襄樊警方協助查詢了兩人的家庭成員資訊,一個名叫「周祥」的人引起了專案組的註意。
資訊顯示,周媛有個哥哥叫「周祥」,也是大學生的父親——這個男人應該就是大爺口中的盧剛,安父口中的盧澤平。
三重身份慢慢歸到了同一個人身上,專案組幾乎可以斷定,這個周祥就是殺害了安潔的兇手。
可他為什麽像能預見這場命案似的一再掩蓋身份?安潔的死,是因為戳破了他的什麽秘密嗎?

2014年,周祥第一次見到安潔的時候,是在號稱艷遇之都的麗江。那時他已經成了「盧澤平」。
靚麗百分百服裝店的招聘廣告貼出去半個月,應聘的女孩來了四五個,但周祥對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並不感冒。
老家是金沙縣的安潔對上了周祥的胃口,小姑娘性格活潑,口齒伶俐,加上也有做過銷售經驗,賣衣服很有一套。
更重要的是,安潔長得漂亮,已經中年的周祥動了心。
而出生在金沙江畔小山村的安潔也有自己的算盤。自小就向往城市生活,初中畢業就輟學外出打工。她天性愛玩,花錢大手大腳,這些年都沒攢下什麽積蓄。
去年,安潔拗不過父母,還回家結了個婚,男方在公路段工作,收入穩定但工作辛苦,掙的薪資刨去生活開支,根本不夠安潔的開銷。
沒過半年,隨著男人的工作調動,兩人和平離婚。
前些年混跡夜場,加上姿色尚可,年紀也不大,雖然離過婚,安潔身後仍然有很多追求者。用她的話說,追她的人可以從金沙江邊排到縣城。
其中除了街頭混混,也不乏一些土豪老板。但在安潔眼裏,那些不入流的小混混當玩伴還可以,讓她委身下嫁絕不可能。而去做那些老板的小三,在小縣城這個熟人社會,父母面上又不太好看。
思來想去,只有找一個外地的有錢人才能實作面子和票子的雙贏。
對比下來,老實本分的周祥成了不二人選。在安潔的心裏,周祥是完全可以駕馭的,或者說周祥的錢,是完全可以駕馭的。
安潔沒有拒絕周祥的示好,禮物照單全收,應酬一場不落,雖然這個男人足足大她14歲。三個月後,兩人便確定了關系。
周祥對安潔有求必應:衣服、包包、項鏈、手機,只要安潔開口,周祥都一一滿足。在安潔的軟磨硬泡下,周祥還盤出了他在麗江的另外兩家服裝店,專心經營靚麗百分百。這種攻勢讓安潔很受用,覺得自己一定是周祥「特殊」的那一個。
唯一疑惑的是有幾次有人叫自己老公「老周」——而自己叫他都是「老盧」。
不過安潔沒有細究過,她覺得江湖上混的,有幾個名字很正常,畢竟她也不是那麽在乎「周祥」這個人。
可這種久違的激情卻讓周祥一廂情願地以為,總有一天安潔會嫁給他。至於現在的虛榮,只是安潔年紀還小,不懂事罷了。
半年過後,安潔說自己上一段婚姻得到5萬塊錢的補償,她爸爸喜歡車,她想和周祥再借點錢,給父親買輛風光的車開開。
周祥覺得這是好事,反正也要在安潔身上花錢,還能討未來嶽父的歡心,這筆錢他願意出。於是周祥湊了12萬,辦了15萬的貸款,帶安潔到省城提了一輛奧迪Q5。
這輛Q5周祥只開過一次,就是接新車回家,把車鑰匙遞到安父手裏的這一次。
這年春節,周祥如願到了安潔的老家過了一次年,那時他覺得時機成熟,向安潔父母表達了結婚的願望。安父卻說,女兒長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決定。
安潔不置可否,說周祥還有待考驗。周祥心下了然,安潔這是還沒玩夠。
年後,周祥感到生意難做,加上每個月還上萬的車貸,自己身上壓力不小。他向安潔提出由她管理服裝店,自己去古城擺地攤。
眼看地攤生意不錯,周祥又拿出5萬塊錢,和一個老鄉合夥擺攤做起了玉石生意。周祥不能兼顧兩個攤位,便發動安潔和自己一起擺攤。
他每天賣力吆喝,安潔卻成天趴在手機上和她金沙老家的朋友聊天。玉石生意一直貼錢,周祥忍不住說了她兩句,沒想到安潔反倒質問他,為什麽他吃閑飯的妹妹不用出來擺攤?
兩人爆發了戀愛以來的第一次爭吵。安潔扇了周祥四個耳光,周祥還了一巴掌,這徹底激怒了安潔。
安潔開始收拾東西,當晚就準備搬回金沙老家,周祥苦苦哀求,沒想到安潔非常幹脆,扭頭就走。周祥再也忍不住,質問她現在生意不好,你要和我分手,以前生意好的時候怎麽不分?
「這不是生意好壞的問題,我和你在一起就是覺得累,你不知道,追我的男人在我老家有一大票。」說完,安潔瀟灑離去,留下周祥坐在台階上默然不語。
沒多久,安潔返身回來,拿走了周祥買給她的蘋果電腦,拿走了店裏2萬塊的營業款,說是這算她這段時間在服裝店上班的薪資。
周祥沒有阻止,他知道安潔正在氣頭上,自己說什麽也沒用。

安潔就這麽回了金沙老家,切斷了和周祥的一切聯系。周祥只能透過之前共同認識的一些朋友、親戚打聽安潔的近況。
時間越久,周祥發現對於安潔的思念越發不可自拔。三個月後,周祥坐上了前往金沙縣的客車。
路上他給安潔的父親打了電話,表明來意,安父很詫異:「你們不是分手了嗎,你為什麽還來找她?我現在很忙。」隨即掛斷了電話。
周祥沒有氣餒,他依然覺得自己的真誠能夠讓安潔一家回心轉意。到達縣城後他買了兩條中華和一大袋水果,打著出租直奔安潔老家。
安父獨自在家,雖說還是讓周祥進了家門,但面對周祥的追問,他對女兒安潔在哪只字不提。「安潔現在已經和縣城一個開美容店的男的在一起了,她也搬過去住了,她說你們兩個人不合適,你不要再來煩她了。」
周祥真沒想到,三個月時間沒聯系,安潔已經和別的男人在一起了。
他獨自走到金沙江邊,望著腳下滾滾而去的金沙江水,迎面是河谷幹燥的風。他想起了初識安潔時她的QQ簽名:金沙江的風沒有選擇在江上停留,而是選擇了遠走。或許這一次,他真的該離開了。
周祥回到安潔家,向安父攤牌,「讓我離開她也可以,但我有條件,買車錢我出的大頭,要麽安潔給我10萬塊錢,車我不要了,要麽把車給我,我給你們15萬。」
安父下意識地看了看停在院子裏的Q5,沒有回答。
「我沒有明確表示過車是我送你的,相關的手續和還貸款的記錄都在我手上,打官司的話是你們吃虧,你們考慮下,我在金沙待兩天等你們。」周祥決定給安家一點壓力。
第二天一早,安潔電話如期而至。
「我們沒有在一起,他離婚帶著一個孩子,我接受不了。」安潔開門見山。
周祥只是一再地說:「我忘不了你,你跟我回去,只要你跟我回去,我什麽都聽你的。」
他沒想到安潔真的答應跟他回去,但要求倆人在一起的事不能對外人說,「我爸媽不同意我們在一起。」
周祥看到希望的曙光,隔著電話點頭如搗蒜。
安潔說自己9月1號要去學車,讓周祥先回去等她。安潔還給周祥吃下了一顆定心丸,給她父母一點時間,她會讓他們重新接受周祥。
9月底,安潔履行了兩人會面的約定,兩人在賓館呆了三天,和好如初。
期間,安潔不時到麗江陪周祥。
每一次周祥都能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心更軟了。所以即使安潔每次來都要帶走店裏的營業款和學車的日常開支,周祥都欣然應允。
11月,安潔拿到駕照。周祥又一次懇求安潔回到麗江,安潔幾次都以朋友結婚、老人生病為由沒有回去,時間一直到了12月底。
年關,是金沙百姓家家戶戶殺年豬的日子。吃年豬飯是隆重的習俗,主人家會殺豬宰羊招待自家的親朋好友,且早晚都擺流水席。周祥得知安潔家馬上要殺年豬,坐不住了,他想借此機會把安潔帶回麗江。
可安潔卻很抵觸,說家裏有重要的客人,周祥去的話她爸媽會有想法。
也許是為了留下余地,安潔允許周祥在殺年豬後的第二天來,周祥只能妥協接受。
12月29號,周祥啟程前往金沙縣。這一次,安潔親自開車到車站接他,他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當晚,他們就住進了縣城鑫蘭酒店,那間203房。

周祥不知道,安潔不滿他的原因,其實和自己另外兩個女人有關。
當初安潔成功當上「靚麗百分百」的老板娘之後,才發現店裏除了她,還有兩個「不是善茬」的女人。
第一個就是周媛,她是周祥最小的妹妹,在服裝店又持有股份。安潔心裏清楚,自己老板娘的地位要穩,要看周媛的臉色。所以對於周媛,她是輕聲細語曲意逢迎。
好在周媛熱衷「國粹」,天天都有牌局,除了月底把關賬目,其他事情都不太上心。
但另一個女人,表妹李慧的存在卻讓安潔十分反感。
那個女人三十多歲的年紀,相貌平平,不怎麽說話,偶爾開腔也感覺前言不搭後語,似乎大腦不太靈。可周祥卻很反常地對她好吃好喝供著,說她年輕時受過刺激,要格外關照。
看著李慧整天在店裏發呆出神,什麽也不幹,安潔覺得周祥是花錢養了個廢人,勸周祥趁早把她辭退,讓她回家。
沒想到周祥極力維護李慧,還向安潔擺明了態度:就算李慧什麽也不幹,自己也會養她一輩子!
這讓安潔十分來氣,覺得周祥和李慧的關系絕對不止表兄妹那麽簡單。
李慧倒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仿佛周遭發生的一切都與她無關,除了和周祥偶爾說說話,安潔的出現掀不起她內心一絲波瀾。
更過分的是,周祥還有過一段婚姻,在湖北襄樊老家。他很早就被父母安排了一門親事,妻子是個地道的農村婦女。周祥一門心思闖蕩社會,並不愛她。
算上今年,他已經18年沒有回家了,但兩人沒有離婚,因為家中的老人由妻子照料,周祥每個月會定期寄生活費回去,作為和這個家唯一的聯系。
安潔沒想到,到了暑假,周祥那個18歲的兒子周天陽居然來店裏投奔他了。加上周祥打了自己一個耳光,那時候開始她便懷恨在心。
安潔本意一定要和周祥分手,可沒想到,這次他追到了金沙,還要收回給父親買的那輛車。權衡之下,安潔準備先和周祥和好。
那天,他們一起住進了鑫蘭酒店203。
晚上,安潔用被子裹著身體坐在床上玩手機,訊息提示音不斷響起,周祥擡手看看表,已經將近11點,心中莫名煩躁。
「這麽晚了,你在和誰發訊息?」周祥忍不住問道。
安潔把手機朝周祥一揚,說是她一個男性朋友,曾經和周祥說過。周祥沒有看,吐了一口煙,問了一句什麽時候回麗江。安潔把電話一扔靠在周祥胸口,撒嬌說再玩兩天,等過完年再回。
這時,安潔的電話響了,她扭頭一看,把它按成靜音,用手指在周祥胸口劃著圈。
沒過多久,嗡嗡的震動再次傳來。安潔一臉無奈,說是朋友非要約她去唱歌。安潔說自己速戰速決接一個,不然等會朋友還會打來。
聽著安潔用方言講了快5分鐘還不掛斷電話,周祥有些惱火,他一把搶過電話,沒好氣地向電話那頭宣示主權:「餵,我是安潔的老公,這麽晚了你幹嘛打電話給我老婆!」
聽筒那面沒有人說話,只有一陣嘈雜的音樂聲。周祥再次提高音量,那邊迅速掛斷了電話。
安潔奪回手機,質問說朋友和她爸在一起,只是叫她過去陪一下。
周祥沒聽安潔的狡辯,咬牙切齒甩出一句,「安潔,今天我在這裏你都這麽大膽,可想而知我不在的時候你會怎樣!」
安潔從鼻子中哼出一聲冷笑,「你沒有資格管我。」
聽到這話,周祥騰地一下坐起,可安潔頭也不擡,自顧自發著微信,回了他一句,「有人出7萬塊錢給我開一家花店,我不會跟你回去了。」
周祥再也忍不住,揪著安潔的頭發一把將她拉倒,擡手就要扇她。
安潔沒有躲避,反而將臉迎了上來,瞪著周祥一字一句地說,她原本就不打算跟他回麗江,自己已經跟別的男的好了,也同居了,「我就是嫁給叫花子,也不會再跟你在一起了。」
周祥心頭怒氣上湧,一把用手臂環箍住安潔的脖子。
「你用力,你今天掐不死我你是我兒子!」安潔滿不在乎。
往事歷歷在目,耳邊回響著安潔刺耳的話,周祥大腦一片空白。
他不敢松手,他害怕一松手自己心愛的女人就又消失不見了。這樣的怒火,讓他感覺熟悉又陌生。
距離上一次同樣的憤怒,已經過去十二年了。
此時的周祥就像中了魔怔,「你不要走!不要離開我!」他自言自語,不斷重復,全然忘卻了懷裏的安潔已經無法回答。
等周祥回過神來,發覺安潔早就臉色蒼白,四肢下垂。
「老婆!」周祥慌了起來,趕緊松手去探安潔的呼吸。
半天感覺不到呼氣,周祥嚇了個激靈。
他把頭伸到安潔胸口,聽到還有心跳,就拼了命地給安潔做心肺復蘇。
不知道按了多少下,安潔還是直勾勾地望著他。他再度把頭伸到安潔胸口——
兩聲心跳之後,什麽聲音也沒有了。
周祥崩潰了,他把安潔擁在懷裏放聲哭泣。除了自己的哭聲,房間裏再沒有其他聲響。
安潔死了,自己殺了人。
眼前的空氣突然凝固,懷中的安潔逐漸模糊。前半生所有經歷仿佛在那一刻倒灌回周祥的腦袋,他又要開始逃亡了。

周祥徹底失蹤了。
專案組這邊依靠在麗江的資訊搜人,沒想到,由於系統升級,再加上周祥很久不在居住地,他的身份在十多年前已經被登出了。
正當隊長被這些五花八門的身份弄得心煩意亂的時候,收到了一份來自湖北警方的反饋:那張酒店視訊截圖裏的男人被證實就是周祥,而且他們不是第一批來找周祥的警察了——早在十多年前,廣東那邊的警察就曾到村裏找過他。
隊長趕緊安排偵查員排查在逃人員。在海量資訊裏比對後發現,2003年在廣東,一個叫周坤的男人曾用過周祥這個名字,夥同一個叫謝艷的女子,殺害一名20多歲的年輕女性後外逃,一直沒被抓獲。
又一個新身份——從方遠到盧澤平,從盧澤平到盧剛,從盧剛到周祥,從周祥到周坤,我們這回似乎終於觸到了他的「真身」。
但又一個新的難題擺在專案組面前:當年那個和周坤一起犯案的「謝艷」,此時又在哪裏?
趕赴昆明的專案組成員經過一天一夜的篩選比對,終於在客運站發現了周坤的蹤跡,他坐上了前往廣西的客車。
隊長不敢怠慢,立即帶隊趕赴廣西。在此期間,專案組發現,周坤這次逃跑居然還帶著自己的憨包表妹李慧。這周坤打的是什麽算盤?
二人同時到達廣西之後,又輾轉去了浙江。
專案組一路追著兩人的蹤跡到了台州,隊長判斷周坤有案在身,應該不敢住賓館酒店,出租房成了大家突破的重點。
那是一座位於城郊的小樓,房東看了照片之後確認,這一男一女確實租了他的房子,可是這兩天一直都沒露面。這時已經是深夜淩晨,既不能確認房裏是否有人,又不能判斷房裏有幾個人。
隊長決定,暫緩行動,專案組輪班守在小樓的兩個樓梯口守株待兔。
初春的天氣並不友好,尤其是在深夜。專案組民警怕打草驚蛇,不敢發動車子開暖氣,大家只能裹緊身上的衣服。最難熬的還是隊長下令不許大家抽煙,幾條漢子凍得直咬牙。
第二天清晨,在車裏熬了一夜的大林正準備將胡豆叫醒換班,發現樓上下來了一個女人。
大林輕拍胡豆,示意他把李慧的照片拿出來。
「沒錯,就是她。」胡豆不敢眨眼,再三確認。
後座的隊長也被二人驚醒。
「隊長,抓不抓?」大林問道。
隊長的腦子快速地轉著,「老胡,你帶小楊過去跟住,先別急著動手,我和大林帶人上去房間看看周祥在不在,等我的命令。」
胡豆帶著小楊尾隨李慧而去,隊長則讓房東帶著自己和大林前去敲門。
「有沒有人在家?我把電表箱的鑰匙拿給你們下。」按照事先隊長教的說辭,房東一邊敲門一邊朝著門內喊道。
房間裏半天沒有聲音,房東繼續喊著,不一會兒屋裏終於有人應聲了。
屋裏一個男人喊:「哦,大姐啊,你等下,我穿件衣服。」
起先是穿拖鞋的聲音,隨後一陣腳步聲越來越近,大林握緊了手中的槍。
「咯吱」門鎖開啟,裏面的人探出頭來。看了無數次視訊監控的隊長和他一對眼,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眼看對方明顯一楞,大林立即用身體倚住門,其他兩名偵查員迅速上前控制住了周祥。
「叫什麽名字?」隊長從背後將他上了銬。
周祥沒有回答,而是反問隊長,「你們是不是金沙的警察?」
這一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就知道你們會來,我等你們好久了。」說完,周祥竟然開始大哭。
那一天,台州下起了小雨。
據說,金沙也是。

12年前,在周祥還是「周坤」的時候,曾在廣東一家制衣廠打工時認識了同鄉謝艷,雖然沒有明確地給謝艷一個名分,但兩人還是像男女朋友一樣同居了。
後來周祥認識了在會所上班的廣東女孩小倩,兩人開始交往。
交往的4個多月裏,小倩並不知道周祥已經在襄樊老家結婚生子,直到一次周祥洗澡時她幫他接了一個電話,而那個電話恰好是周祥老婆打來和他要生活費的。
小倩當即要求周祥要麽做選擇,要麽做了斷。
周祥卻舍不得老家的兒子,沒能答應小倩和家鄉的妻子離婚,小倩一怒之下回到會所做回了小姐。
一天夜裏,小倩回到出租房拿東西,發現周祥竟然和聲稱是自己表妹的謝艷睡在了一起,她瞬間明白了兩人真正的關系。
不管周祥怎麽解釋,小倩始終認定周祥背叛了感情,欺騙了自己,還放下話要到制衣廠把周祥的名聲搞臭。
兩人從爭吵到撕扯,聽著小倩一句接一句的辱罵,周祥忍無可忍,一把勒住小倩的脖子,直至她停止了呼吸,一旁的謝艷嚇得呆在當場。

自此之後,周祥就帶著謝艷,化名盧剛和李慧,踏上了逃亡之路。
12年間,他們一路由東向南,一路不斷變換身份,經歷了擺攤、倒貨、開店一系列的生活,楞是給自己打下了一份家業。
對外,他都說謝艷是自己的表妹李慧。換掉名字後,目睹他殺人經過、受了刺激的女友謝艷成了「憨包表妹」,而他搖身一變,從殺人犯變成了對自己憨包表妹不離不棄的好哥哥。
原以為這會是最好的歸宿,沒想到安潔的出現打破了周祥對未來的一切設想。
「我沒有想到,我會愛上她,更沒有想到,我會殺了她。」周祥向隊長坦白。
「這些年我每天都提心吊膽,我想你們趕快來抓我,又怕我被你們抓到,我終於安心了。」周祥在被帶回監室前,轉身向隊長說道。
周祥對殺死女友安潔的犯罪事實沒有任何隱瞞,對12年前讓自己走上漫漫逃亡路的案子也清楚地作了交待。
「我很後悔,我只想在這裏把我身上的最後一點錢花完,花完我就去自首。」周祥看著隊長,流露出一種不像殺人犯的真誠。
12年,他還是不知道該怎樣對待一份感情。在感情裏,或許他一直沒有用得上自己那份「精明」,沒有學會真正的尊重和珍惜。
後來,經過調查確定,謝艷沒有參與周祥的任何一次犯罪。雖然她人看著癡癡傻傻的,但對她進行的精神鑒定,均顯示正常。
偵查員大林不是很理解,12年,一個女人最好的年華,她竟然跟著一個殺人犯東躲西藏。
在最後一次訊問結束後,大林問她:「你知道周祥是個什麽樣的人,為什麽還要這麽一直跟著他?」
目光沒有聚焦的謝艷幾乎沒思索,脫口而出三個字——
「我願意。」

這是個少有的,我不想就案件裏的任何一個人去分析的案子。因為與其說這是個撲朔迷離的罪案,不如說是一張交織在一起的、扭曲復雜的情感關系網。
沒人可以脫離情感關系網,但當所處的關系發生扭曲,輕的時候,可能只需承擔一種道德上的譴責——拜金、出軌、第三者、難以被追責的暴力;極端的時候,它就發展成了罪,讓這張網上的每個人都無法獨善其身。
身陷其中的人沒想過,一點點火星都能讓所有人燒作一團,因為在扭曲的人性、扭曲的情感關系裏,不會出現幸存者。
(文中部份人物系化名)
編輯:大棒骨 渣渣盔
插圖:娃娃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