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 明 張 妮
編者的話:「如果我們的歷史上沒有孔子傳道,沒有屈原投江,沒有杜甫詩史,沒有曹侯紅樓,別人憑什麽要尊重你的文化?你靠什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茅盾文學獎得主李洱這一問,振聾發聵。在【環球時報】「新時代·新作品·新閱讀」系列文化沙龍上,【環球時報】記者與李洱圍繞知識分子這一話題,就中國文學的來世今生、出海之路展開討論,深入探究短視訊、人工智慧(AI)技術對文學創作和想象力的影響,進一步挖掘創意寫作對中文教育的重要意義。本次沙龍由環球時報社發起,聯合聯通愛聽、國際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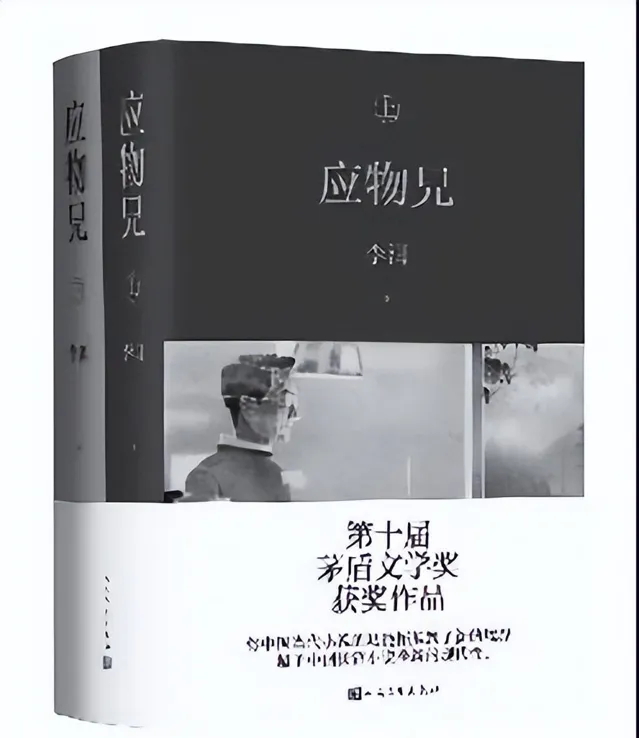
圖片說明1: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應物兄】

圖片說明2:【應物兄】作者李洱在沙龍上發言。劉明攝

圖片說明3:「新時代·新作品·新閱讀」文化沙龍現場。劉明攝
「要同時接受東西方文化的審視」
李洱,原名李榮飛,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他1966年生於河南濟源,著有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等。2019年,李洱憑借作品【應物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應物兄】中的核心人物「應物兄」本名叫「應小五」,後被初中班主任改名「應物」,又因出版社錯加了一個敬稱「兄」字,最終成為「應物兄」。小說圍繞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籌備成立和迎接儒學大師程濟世「落葉歸根」兩件事,以「應物兄」為軸心,串聯起當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生活經歷,描繪出一幅現代社會的時代畫卷。「‘應物’是中國哲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跟外界打交道時,你要能夠對這個世界應付自如,即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真正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李洱說。
有人把【應物兄】與【圍城】進行類比,認為它是「新儒林外史」。李洱對此表示:「首先,兩者成書年代不同,【圍城】的故事背景是戰爭年代,是典型的‘流浪漢小說’的寫法,敘述主線集中在幾個知識分子身上,他們跟那個年代的戰爭仿佛沒有關系,只是執著名利,耽於愛情。因此真正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知識分子有理由對【圍城】提出很大意見,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王元化先生曾經撰文痛批【圍城】,稱書裏沒有可以使人精神昇華的真正的歡樂和痛苦。我認為,對於文學史而言,【圍城】提供了經驗和教訓。」
「至於【應物兄】跟【儒林外史】的區別,後者的背景是帝國崩潰前夜,整個國家、文化、制度大廈將傾,與我們的時代截然不同。有些批評家把兩者比較,也是因為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有相似之處。【應物兄】當然也有諷刺,但更多屬於反諷,兩者有微妙的區別。」李洱表示,「在人物方面,相較而言,【應物兄】裏寫了‘有失敗感’的人,但同時也刻畫了一些有理想的知識分子。這類人在【儒林外史】和【圍城】中都很少出現。」
李洱曾形容知識分子就像蝸牛的觸角、貓的胡須一樣,是其所處時代最有力、最敏銳的群體,他們的身上凝聚了時代各種各樣的困惑和矛盾。那麽,從孔子、屈原、曹雪芹等古代知識分子,到魯迅、瞿秋白等近現代知識分子,再到當代知識分子,他們的追求、困惑、命運,有什麽相同和不同? 李洱感慨道:「如果屈原沒有投江,如果中國歷史上沒有杜甫和孔子,別人憑什麽要尊重你的文化?我們的民族憑什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衡量一個國家的文化值不值得尊重,要看其文化系統內出現過幾個重要的知識分子。這個‘看’,不僅是從自身的文化內部去看,也要站在別的文化傳統的角度去看。簡單地說,就是要同時接受東西方文化的審視。」
李洱舉例稱:「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曹雪芹還被認為是一個‘通俗作家’。胡適認為【紅樓夢】在藝術上毫無意義。1940年之後,我們才慢慢接受【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作品,直到今天將其奉為漢語小說的巔峰之作。這是因為有人借助新的批評方法,把它與【戰爭與和平】【人間喜劇】【堂吉訶德】進行比較,認為它跟它們一樣都是傑作。換言之,【紅樓夢】因為有不同時代的很多人去研究,有具備極加文化素養、同時理解東西方文化的學者去闡釋,才成為我們今天所說的【紅樓夢】,才能進入世界文學的寶庫。」
「我們的祖父輩和子孫輩實際上處於一個相同的文化語境中的‘一代人’。」李洱將梁啟超比作「某種意義上最接近孔子的人」。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一書中大膽預言未來100年的事情,從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到中華民國的成立,到世博會的舉辦,他呼籲民眾切勿沈浸在封建帝國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傷感迷離中,認為中國文化必須從頭再來!李洱說:「梁啟超在某種意義上提出了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中國文化必須在轉型當中不斷地成長。正如那些革命領袖,在絕望中激發出勇氣,驅使他們投身革命、投奔延安。」李洱認為,當代知識分子首先要勇於表達自己的真實看法。
「在多維度現實中應對挑戰」
有評論家認為,無論是【應物兄】還是【花腔】,主人公其實都是「賈寶玉」,都是在寫「寶玉」長大後要怎麽辦。李洱也曾表示,當代作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把賈寶玉放在20世紀或21世紀,續寫他的成長故事。當被問及為什麽把賈寶玉放在如此重要的文學地位去研究時,李洱表示:「很多人只看到了寶玉花花公子的一面,但讀書要看到人物與其背後文化之間的關系,既要看他在書中的身份,又要看到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糾葛。放眼整個中國的小說,作家們都是在處理同一個問題——寶玉成長的問題。寶玉成長的悲歡,某種程度上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縮影。我們面臨的問題之復雜,較孔子時期、曹雪芹時期更甚,因為當時是中國文化的內部處理問題,而我們是在東西文化碰撞、古今文明交織的多維度現實中應對挑戰。」
今年南韓作家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馬奎斯的【百年孤寂】被網飛拍成劇集,都引發廣泛討論。那麽,中國文學整體上在世界處於怎樣的位置?中國文學出海面臨哪些問題?李洱對此表示:「我們理所當然會認為,魯迅與莎士比亞應該是平起平坐的。但事實上,主要接受魯迅的國家是日本,魯迅在歐洲的傳播卻困難重重。這說明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的路上,首先遇到的是語言的障壁。拉美和歐洲大致處於同一文化系統之內,語言相似性強,轉譯相對容易。而我們處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傳統制度,使得兩者之間的理解變得艱難。」
「不少當代作家的作品,海外發行量遠超魯迅,語種遠多於曹雪芹、杜甫,但我們不能說他們比魯迅、曹雪芹還重要。中國文學作品被轉譯到國外,是否能夠引起關註討論並被外國讀者所接受,固然重要。但這不能作為評價一本書、一位作家的標準。」李洱說,「南韓和日本為什麽能在世界文學史上取得今日如此之成就,是因為它們與世界磨合的時間非常長。」李洱一直積極推動中日韓三國的文化交流,將中國文學作品推薦給日本、南韓。他說:「對於文化,我不認為應該用‘傳播’一詞,而是更註重交流對話。」
「AI永遠也寫不出這樣的句子」
除了傳統文學,網文、網劇、遊戲作為中國文化的新形式,出海勢頭正盛。美國批評家米勒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文學終結論」,認為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文學可能會終結,在新的時代當中,文學會迎來一種新的轉化或者新生。
李洱告訴記者他對此的看法:「從發展變化的角度看,科學在進步,但文學很難說是在進步。如今,我們依然向孔子學習,與蘇格拉底對話,你永遠不能說孔子過時了,蘇格拉底落伍了。文學需要不斷回到原點,所以文學是一種‘變化’,很難稱之為進步。其中技術性的部份確實在發展,但是技術一定植根於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對經典的解讀。當代作家的每一次寫作,都是在和漫長的小說史、藝術史以及文化史對話。」
當下,很多人每天沈溺於刷手機,接受的都是短視訊之類碎片化的資訊,這不免讓人擔憂:我們未來還能回歸到對深度文本的思考嗎?對此,李洱認為,白居易言「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寥寥數語就能讓人在腦海幻化出綺麗畫卷,「一條幾秒的短視訊很難產生這種效果。」他認為,短視訊輕而易舉地剝奪了人類的想象力,「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用事實講述了文學想象對人類進步的意義。人何以為人?不是靠手機裏的影像,而是靠腦海中的想象,靠故事。」
談及AI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李洱笑著說道:「AI寫不出【應物兄】,寫不出【花腔】,寫不出什麽復雜性,因為【應物兄】只能夠由人類來寫。」
【應物兄】中寫道:「他摘了一片無花果樹的葉子,把它捏了起來。他沒有去驚擾那只正在吐絲的蠶。他怕影響它作繭,影響它化蝶,影響它做夢。」「AI永遠寫不出這種句子。」李洱說,「我們要把AI利用起來,但智力、情感、想象以及人類對這個世界復雜程度的認識,只有人類自己具備,我們無法依賴人類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個東西。」
除了文學形態的發展,中國文學教育也日新月異。中文創意寫作作為新興學科,於2024年1月22日被教育部列入中國語言文學二級學科,而李洱也是中文創意寫作聯盟的發起人。他表示:「隨著教育體系日漸完善,中文教育也日趨完備。但吸收大量知識的同時,很多學生卻不會表達自己,只會說別人說過的話,不會‘說自己的話’。學生對世界的感知力越來越弱,對世界沒有自己的看法。這令我們產生了深切的憂慮,因此我們聯合中國最著名的幾所高校,共同成立了創意寫作聯盟。我們要讓學生學會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能夠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只有想的說的寫的都是真的,而且能夠真實地進行交流對話,我們才可能構建一個真實的世界,才能在世界中共同成長。這對青年學生來講意義深遠,對於文化建設而言意義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