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
因為頻繁去做義工,我接觸到了一百多位老人家,他們大部份的年紀都在70歲以上。
人到這個歲數,離別生死,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
有個老人,她寡言寡語,很少說話,因為她的直系親人在短短一年多,先先後後都沒了,先生走了,兒子女兒也走了。這種情況下,換成誰也很難接受吧。她的應對不是傾述,她把孤獨傷感都變成了閱讀,看各種各樣的的書和報紙。她的舍友唱腔很好,以前是在劇院做事的,經常給她唱唱歌解解悶。
有個93歲堅持洗冷水澡的老人家,她的腰背彎曲如弓。她不能穿很厚的衣服,不然皮膚的癢感會很強烈,撓不到,只能一天天忍著。這個婆婆的床上擺著幾個公仔,她最喜歡是那只皮卡丘,每天睡醒都要抱一下它。
剛來的時候,她的兒子隔段時間來看她。兒子有嚴重的腿病,走路走不動,幾百米多的水泥路他要走半個小時。兒子一輩子也沒成家,很難照顧她,內心壓力很大,整天愁眉苦臉的。她說,沒關系,媽都知道,哪個罵你不孝順,讓他來老人院找我。是媽自己要來老人院的,不能怪到你的頭上。
我還在老人院遇到一個起起落落的爺爺。
當年,義無反顧地放棄舒適的生活,自願從香港回來,熱情滿滿的搞建設,那時候他才十多歲。
後來當上兵了,海軍,當了五六年。期間,因為素質過硬,新兵初登場,就被委任職務。就那樣,在刺人的太陽、翻滾的海浪中,踏踏實實,幹了好幾年。明媚的前程,因為政審過不來(特殊年代的投射,他本身和出身都沒問題),在老領導的幾次惋惜勸說下,退伍了。
退伍了,沮喪了,又重新燃起鬥誌。
一路過關斬將,當上了一個重點中學的老師,之後教書育人,成家立業,在學校和當地都是有口皆碑的。
後來,十年開始了,學校裏第一個被貼大字報被打倒的就是他,一覺醒來,整個世界都變了,那些紙上寫的都是他,張牙舞爪,很熟悉,又很陌生。罪名很好笑,從香港過來的潛在特務……
沒辦法啊,認了啊,不認過不了,這是個荒唐的年代,認了也打罵,不認也打罵。最慘的,是被自己的學生打罵,那樣一副大義凜然咬牙切齒的小屁孩樣子,叫嚷著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和帽子,真讓人心寒。
一連兩個月,睡不好,吃不好,頭發大把大把的掉。
有一天,他想到了自殺。
得了,熬不住,我不活行了吧。
那些天,他的思想鬥爭劇烈,身邊的親人都覺出他有些不對勁。
有一天。
門響了。
進來了他的一個學生。
大眼瞪小眼,他感到有些苦澀的憤怒,欺負人都欺負到頭頂上了嗎,一個當學生的單槍匹馬到老師家裏搞事情?
等一等。
好像有些不對。
原來,學生是冒著大風險偷偷過來看他的。小的手緊緊握住大的手,顫聲說,老師,你要撐住啊,不要自殺。你知道嗎?不是……不是所有人都那樣看你的。
就這幾句話。
把他拉了回來。
後來也恢復了名譽和工作,一晃眼,幾十年時間都過去了。
人在老人院,心態平胡如水,對夥食對條件,沒有半點怨言。自己打趣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幹嘛要自尋煩惱呢。跟當年的好幾個學生保持了聯系,大家還會不時過來探望他,接他出去聚餐。
那天,我去探訪老人,他的桌上擺著很多的書,還散放了一些筆記本。是的,他有做自己的閱讀筆記,稱之為打發時間。老人以前是做語文老師的,但外語學得相當好,英語和日語(工作後自學的)都很紮實。
他對我說,人老了,時間就少了,我也不怕哪天就走掉。只是覺得有點遺憾。
我問他,是怎樣的遺憾呢,或者可以去試試怎樣實作。
他說,實作不了了,我身體不支持我出遠門,我前些時候轉譯了一本講日本歷史的日語書,我想去那邊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把地方和環境建設得那麽好那麽文明。
問他,怎麽想到去轉譯書呢,是想出版嗎(他的學生中有這樣的人脈)。
他說,不是,就是鍛煉一下腦筋,怕自己的思維變遲鈍了。我每天都告訴自己,要多看看書和新聞,睡覺前也想一想,今天學到了什麽,有沒有什麽還不懂的……人不會自我思考,跟死了又什麽分別呢。
是這樣的。
有的人,25歲就死了。
有的人,85歲依然青春。
(3.6補充一些)
人。
明面上是一生一世。
骨子裏是一生一死。
走向是固定了。
生之前的事,我們選擇不了。
死之後的事,我們做不了主。
兜兜轉轉一大圈,好像能做點事情做點嘗試的,就是活著這個階段了。
活著,是一個宏大的話題。
怎樣活才算活出了自己的樣子和意義,也是個見仁見智的事情。
我本人沒有宗教信仰,也沒有哲學研習,我只是千萬個路人中平平凡凡的那一類。所以我看待活著的意義,只從普通人的視角和體驗出發。
在過去的生活中,我經歷過親人朋友猝然離世的事情,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這些人中,有我的至親,有我熟悉的長輩,也有關系很普通的人,他們的離別,散布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壯年。
最初接觸到這樣的事情,我的第一反應是很疑惑,死是什麽?
跟下來,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害怕和緊張狀態。
害怕什麽?
害怕自己也會死,也會靜靜地躺在那,一動不動——這是我太婆去世給我的最大震撼,我太婆長我七十多歲,我的童年就是她、托她保管的鑰匙、滴水的瓦背和家裏的那只大黃狗。明明在她去世前幾天,我還經常見到她,並給她送去家裏熬煮的雞湯。那是一個慈祥有韌力說說笑笑的老太太,怎麽突然之間就沒了呢?
等懂事一點,這樣的離別,讓我知道了心痛的感覺,知道了個人世界崩塌碎裂的聲音。這時候就取了一種逃避的態度,反正橫豎躲不了,我就當個鴕鳥,自動遮蔽,不聽不看不哭不鬧吧——這是我爺爺去世後,我的整體應對態度。
那時,我二十出頭。我的性格和處事,受我爺爺影響很大,因為老爸老媽工作忙,我們兄妹幾個經常吃住在爺爺家,老人的脾氣又很好,處事公允,沒有長輩的架子,彼此間有非常多的互動和交集。也是因為這層緣故,老人走的時候,我特別崩潰,我跟他告過幾次別,但我沒有見到他最後一面。收到訊息時,他已經不在了。再回去,就是空空的座椅,物是人非。
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我意識到鴕鳥這種應對狀態,雖然不會給我制造新的傷害,但是它沒有帶來新的成長。同時,它並沒有真正移除掉我對人生人死人為什麽活著的顧慮,內在的傷,在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變本加厲制造更多的混亂和不安。
就這樣。
重重機緣之下,我開始去做義工。
當時就是抱著多體驗一下的想法,設想去個兩次三次,見證一下醫院、老人院的生老病死,「證明」自己不糾結於生死就可以了。
在沒有去之前,我把這些地方整個氣氛想象得很沈重。

(市橋醫院,探訪需由公益組織帶隊安排和院方溝通協商,屬於有紀律有品質的集體探訪,以免私人空降造成不必要的幹擾)
廣州這邊有三家專門的臨終關懷醫院,我有堅持去其中的兩家,一個叫市橋,一個叫江南。
相對來說,市橋比江南更特殊一些,它們的六到八樓,收治的都是一些重病和癌末的人,大部份都是臨終狀態的人。如果不是家屬(只是小部份患者有清楚的自我意識)主動提出換院出院,這邊的病人會一直在病床上待到最後一刻。
盡管是康寧科,但能知道自己確切病情的人並不多,有些病人會被家人刻意瞞著,並要求醫護人員同樣保密。類似的人有多少,沒有人統計過,之前有聽到醫院的一個主任做公益的線上講座。據他了解,在他所知道的病人中,有接近六成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實情況,有的會樂觀地以為自己還能好轉,有的則因為一天天的病癥折騰,慢慢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情況和處境,畢竟不是所有的防範和白色謊言都能起效的。
市橋這個醫院,收治的病人很雜,南北西東都有,以廣東廣州當地的普通階層老百姓為主。住進來,一個月五千左右的基礎費用,在這裏,有住了十年飽受慢性病侵蝕的人,也有當天上午才轉進來,下午就推出去的。有特別多陪伴的,家人親友們默契配合眾星捧月一樣的,也有長達好幾年,除了微信繳費從不露面的人。

我第一次去的也是市橋,這個被標註了生命最後一公裏的地方。我陪伴的第一個老人家是一個婆婆,高齡,90歲,中風,左側身體偏癱,長期臥床,牙口已掉了好些,說話詞句含糊,會有些漏風。老人吃飯的時候,喜歡吃魚,只是食堂不敢也不可能天天供應魚給老人家吃。躺在床上的時間多得可怕,等待一條魚,等待一條姍姍來遲卻又出場寥寥的魚,就是親人之外,老人的最大日常了。
就是這麽一個長期躺床的人,一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人,她的心情很平靜,她接受了自己的衰老和病痛,並不覺得害怕,也不覺得有什麽要避諱的。她只是用她的勺子(她不喜歡用筷子吃東西),等待一條魚。在7樓裏,在四十多號高矮胖瘦的病人中,她是極少數可以自主吃東西的那一部份。能自主吃飯,能不吃流食,是她在生命末期找到的一份力量。這個老人,在同一年的11月,永遠走了。再去7樓,再經過熟悉的那張床,我就見不到她了。
有位大叔,早年走南闖北,到海邊捕魚釣魚,到廣西收黑皮甘蔗,到江西趕場子找商機,辛辛苦苦了一輩子,沒見過幾個大錢。
因為房屋拆遷,獲得30多萬的補償。
這一世人,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多錢。
結果,好日子沒有享受幾天,病痛就來了,這個病痛一早就有了,但當時威脅不大,只做了簡單的手術,就那樣拖拖拉拉成了重病。
看病,吃藥,再看病,吃更多的藥。
然後確診了。
癌來了。
短短三兩個月間,真金對白銀,花掉了二十萬。自生病後,子女雖有抱怨,但妻子一直陪著大叔,把原來的工作辭了,專門租了房子在附近做短工。
我們那天陪他。
大叔對我們說,我知道的,我回不去了,我會死在這裏。
說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氣,目光灼灼的望著我,語氣十分平靜。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痛。你們不知道,那種痛痛起來有多痛……」
時間快到了。
我們要去「開會」了。
大叔也在一旁提醒,差不多了,你們該走了。
然後,他笑笑著看我又看看我的小夥伴。
「下個禮拜再來看我吧。」
大叔好像想起了一點什麽,又補充道:
「如果我還沒死的話。」
下周再去,病床空空的,大叔走了……
把目光收回老人院。
二樓那個熱愛唱歌的婆婆,每次都捧著自己的歌本,等待義工過來陪伴。她是個普通的老百姓,但她的樂感很好,還自行創造了好幾首健身歌,歌詞取材生動,朗朗上口。
她的同屋是張婆婆,常年臥床,說不了什麽話也動不了,是手手腳腳一動都不能動的那種,只有時而清醒時而模糊的神識,時重時輕的呼吸。
但很多老人羨慕她。
為什麽呢?
因為她的家人頻繁且固定來看她。
多頻繁?
這麽說吧,她有七個子女,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輪流來一個陪老人。
固定星期天來看張婆婆的是她最小的孩子,小兒子——這是一個個頭十分高大的伯伯,大概有一米八,他每次來了,絕不空手,都帶一些好吃好喝的東西給他媽媽。
不知什麽時候開始,這位伯伯留意到隔壁的一位喜歡跳舞的婆婆很少人來探訪,每次看到他來看媽媽,總是用羨慕的眼神望著,有時還要走過來,專門望一望他們。
後邊,這個伯伯每次來看張婆婆,就專門去隔壁轉一轉,陪陪跳舞婆婆。
然後他會給跳舞婆婆一只橘子。
一只很大很香的橘子。
每次都是這樣……
我見過很多說樂天知命的人,跑去臨終病房後崩潰大哭的。
有些事情,你知道和你自己去做,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碰撞。
同一個陪伴物件,同一小組的兩個義工,受限於自己的視野和內在,看到的收獲到的,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東西。同理,同一個人,受限於自己的視野和內在,在不同的時間段裏,也可能是起起伏伏相互矛盾的。
就說前面那位大叔吧,你是不是覺得他很樂觀很能接納了呢?
但在我探訪前一周,他的狀態一直在起起伏伏,說起往事,說起親友,說起患病的經過,痛哭流涕。一周前,他跟另一個義工小夥伴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故事,包括父親的酗酒,母親的去世——不同於父親,他的母親只是喜歡喝一點酒,但從不過量,七老八十後依舊保持了這個小嗜好。臨走的那天夜裏,母親還喝了點酒,她身體一向不差,沒啥大毛病,事前更沒有半點征兆,發現時人已經沒了呼吸,神態很安詳。說到母親的善終,他很感慨,也很羨慕。
大叔很明白自己的病情,心情也不是長期平靜,甚至短短一周呈現出來的狀態就完全不同,但整體上,他已經從找到自己的調節方法,他接受了自己即將離開的事實。從抗拒、否定到接受,從悲痛、後悔到平靜,這是這位大叔的磨練之道,但也有些人是反過來的。這樣的逆變,會更折騰。需要找到更多的力量。
所以你看。
人活著,確實不容易,反反復復的,起起落落的,有很多很多的功課要做。
也正是這樣。
你知道了活著活好有多不容易。
然後才會真的發自內心去珍惜,帶著自己的韌性去直面那些苦難。
這個世界。
最不缺的就是挫敗和孤獨。
但也總有一些人和事情會來溫暖我們。
傳遞一只橘子。
是我補充這份回答的意義。
看清生活的真實面目後依舊熱愛生活。
是我所看到的活著的意義。
(4.8補充)
整理了自己知道的主要涉及生死觀、告別的一部份影視劇和臨終關懷者手記、繪本。
有助於提升對死亡、告別的理解、釋懷和承載力。
【入殮師】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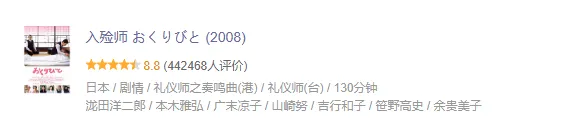
【遺願清單】(電影)

【遺願清單】(書籍)
紀慈恩就是資深的兒童福利院和臨終病房的社會工作者,體驗死亡工作坊創始人,烏托邦臨終莊園創始人,書是她本人十年2700小時臨終關懷經歷得來的觸動和成長,很值得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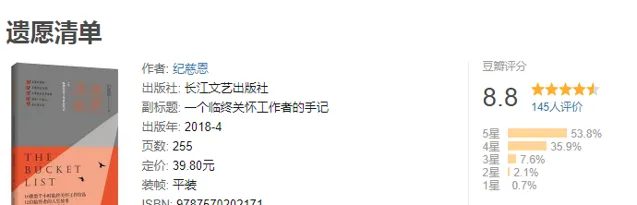
【人間世】系列紀錄片

【我死前的最後一個夏天】系列紀錄片

【死亡醫生】(電影,有故事原型,關於安樂死的爭議和嘗試)

繪本——考慮到有些人對題材表達和時間比較敏感,想了解,但又不想花太多時間,想看見,但又不想太沈重。
那麽不妨試試另一種辦法,主要透過畫面來展示的向死而生,同時這些繪本也適合跟小孩分享、講述。這也是我在另一個公益組織跟病房裏的孩子們互動的方式,講繪本故事。當然,每次內容都需要提前報備,盡量給他們帶去一些放松,生死觀內容的繪本也要擇優而從,不一定都能透過。
【有一天】
【當鴨子遇到死神】
【爺爺變成幽靈】
【一片葉子落下來】
【告別安娜】
【爺爺的墻】

在這兩篇文字裏。
關註點在於如何看待親友的老去,如何看待自己或親友的最後一程,分享了我作為旁觀者的一些心事觸動。同時,還談到我在臨終關懷醫院所看到的,一對恩愛夫妻幾十年如一日不離不棄的感人故事。
對陪伴故事和臨終關懷感興趣的小夥伴。
也可以留意我的知乎夏花專欄。
我會持續更新。
這是本文的姐妹篇。
做義工的最初考慮和動搖都在裏面。
詳細記述了早中期探訪中印象最深刻的生死故事。
(轉載請提前走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