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總是短暫的。今天是周一,上班日。
與往常一樣,你被鬧鐘叫起床,匆忙洗漱完畢下樓趕去地鐵,如果隔著一兩公裏路還得首先掃描一輛共享單車。地鐵裏人頭攢動,排著隊過安檢進站。到達車門附近,你終於在人群中擠上地鐵,因為不是始發站,此時早已沒有了座位,連站立的空間也是擁擠的。站在車廂裏,腦子裏還在不斷過近期的專案方案,愁苦之際低頭瞥見對面坐在座椅上的陌生人攤開了筆記電腦,一邊敲著字,一邊不時扶一扶螢幕謹防滑落在地。

【開往春天的地鐵】(2002)劇照。
到了辦公樓,身體蜷縮在格子間,開始這一天的工作。下班後,再重復地鐵行程,以此往返於住處和辦公室。
前不久,「京滬高鐵班味比辦公室還濃」「班味最濃的高鐵」多次登上社交媒體的熱搜。這是一種與辦公室的庸常相似卻在形式上極其奇特的「班味」(網絡流行語),它快捷、高效,它安靜、克制。京滬高鐵,中國最繁忙的高鐵,在這條高鐵線上,乘客們齊刷刷在高鐵開動後開啟電腦,有的在做標書,有的在做方案,有的戴著耳機在開電話會議。有人在苦苦加班,有人借著旅途提前完成任務,為的是到了目的地後可以躺下睡上一覺。他們講著行業術語,盯著螢幕,偶爾望向窗外。四五個小時的旅程,足夠他們開完一場會、修改一份文案。如此畫面,讓京滬高鐵被稱為是「班味超標」(網絡流行語)的地方。年輕的上班族乘客感嘆,小時候總覺得在火車飛機上用電腦打字的大人很厲害,直到自己成為打工人。上班這件事的「時間」與「空間」在這裏發生著復雜而又微妙的變化。
「班味高鐵」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但是它在最近的走紅,似乎和不少流行的「職場梗」形成了呼應,自嘲的背後,多少反映出了當下職場生態中普遍的疲態。那麽,我們能做什麽呢?
我們有一位作者,他的家鄉在京滬沿線,後在南京、上海兩地求學,畢業後在上海咨詢行業從業多年,作為「資深打工人」的他時常到北京出差。他是京滬高鐵線上的乘客。比起飛機,「我更喜歡選擇高鐵,原因之一正是它更好地提供了移動辦公的條件」。旅途是否消失,是否被工作取代(或者可以借用哈貝馬斯的「被殖民」概念),這段行程的意義是什麽?「班味高鐵」是讓工作侵入了生活,還是為我們靈活工作提供了便捷條件?其中滋味,恐怕沒有唯一的答案。且從「班味高鐵」裏蘊含的幾組關系聊起。
工作與生活:尷尬的「居間態」
「在路上」的通勤時間屬於工作還是生活?也許,它是一個尷尬的「居間態」,需要我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填充」。如果選擇步行、騎車或者駕車通勤,這段時間似乎不容選擇也無可填充,因為我們深度投入在這個位移行動的本身之中。

【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劇照。
如果選擇公共交通工具,我們的身體和註意力被「解放」出來,「居間態」的時間就成為一個需要被「處置」的物件。初入職場的時候,我傾向於用發呆、聽音樂、刷手機、閉目養神之類的方式「打發」這段時間,就像從前人所說的「消閑」。成了資深打工人以後,我好像會開始思考怎麽「利用」這段時間,比如回復一些工作時間沒來得及回復的瑣碎資訊,讀一些片段性的文獻,或者加入「知識經濟」的消費大軍,給自己充電。
某種程度上,京滬之間的差旅之路,就是放大版的通勤時間,而「班味打工人」們的普遍選擇,就是充分地「利用」它。這種對「間隙時間」最大程度的占有和利用,在全球範圍內恐怕已經流行了上百年。馬克思指出,與19世紀大規模的勞動和生產重組相伴出現的是「流通時間」和「通訊時間」的加速與控制,前者以鐵路這樣的新型交通工具為代表,後者以電報這樣的新型通訊手段為代表,兩者交織在一起,對資本主義的增長起到關鍵作用。他還說過:「重要的不僅僅是技術成就,如更快的貨運速度或即時通訊的實作;而是說,如果資本的本質過程是流通,那是因為‘這個過程永恒的持續性(constant continuity)’。」
這段話轉引自美國學者莊拿芬·克拉利的著作【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

【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美]莊拿芬·克拉利著,許多、沈河西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三輝圖書,2021年5月。
24/7體制真是當代社會一個形象且鮮明的符號。24/7的時間裏,在人們重要的行動和任務序列中,原本存在許許多多的「間隙時間」,但如今它們的處境越來越尷尬。克拉利書中還比較了福柯所謂「規訓社會」和德勒茲所謂「控制社會」的區別。如果說前者像「全景敞視監獄」一樣的權力機制還不是彌漫性的,那麽後者真正做到了「無微不至」,對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體制化控制持續不斷、沒有界限,且基本上全天候:「控制社會的特點是間隙消失了,敞開的時間和空間也消失了。命令機制和規範化的效果見縫插針,無時無刻不在發揮作用,而且以更全面更微觀的方式進入到人的內心」。這大概就是「班味高鐵」背後的職場生態吧。
你若問我作為「班味高鐵」上打工人的一員有何感受,我想說,倒也還好,因為我並不討厭自己所從事的這份工作,有時甚至有點喜歡。於是我就在想,姑且撇開工作不談,如果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廢寢忘食」「夜以繼日」,「間隙時間」同樣消失了,但恐怕就不會有「班味高鐵」這樣的酸辛苦澀。我還想到有一年去青甘大環線包車旅行,第一次用上了無人機,途中忍不住趕緊將所拍所感記錄下來,就把Surface(電腦)和迷你鍵盤放在腿上,一路顛簸,一路碼字,竟有點樂在其中的味道。

【北上廣依然相信愛情】(2016)劇照。
所以,「班味高鐵」的話題熱度,恐怕並不源於「在高鐵車廂裏工作」這個客觀事實,而是源自萬千打工人心底的感受以及背後深遠而普遍的職場生態問題。如果工作和打工人的關系成了馬克思說的「外化」甚至是「異化」,也就是工作及其成果成為「一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於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甚至「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那麽,工作對日常生活「間隙時間」的無限侵占,自然就帶上了某種悲劇意義。
但也特許以設想一下,如果是一個熱愛文字的職業作家在京滬高鐵上碼字寫作,算不算有「班味」呢?「在高鐵車廂裏辦公」本身不是工作的「異化」,但這個客觀現象所引發的廣大勞動主體的強烈反響,反映出了更深廣的職場「異化」問題。
旅途與目的地:你會不會說我酸?
「班味高鐵」涉及的另一組重要關系,是旅途與目的地,雖然這裏的「旅途」不是「旅行之途」,而是「差旅之途」。我依舊清晰地記得十幾年前大學的當代文學課上讀過的這首現代詩:
列車正經過黃河我正在廁所小便我知道這不該我應該坐在窗前或站在車門旁邊左手插腰右手作眉檐眺望像個偉人至少像個詩人想點河上的事情或歷史的陳賬那時人們都在眺望我在廁所裏時間很長現在這時間屬於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黃河已經遠去——伊沙,【車過黃河】

王福春攝影作品。圖片源自【火車上的中國人】,王福春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後浪,2017年6月。
不論詩裏蘊含著多麽深重的隱喻,末兩句已經足夠有力地描摹了搭乘高鐵的旅途狀態。曾經的天塹,迢遞的空間,一下子被速度和時間征服了。在「班味高鐵」上,可能碼下一行字的工夫,長江就已經遠去。在京滬高鐵最快班次的4小時18分裏,可以開完一場激烈拉扯的電話會,畫完幾十頁精致美觀的PPT,卻欣賞不了一眼祖國的大好河山。
德國學者沃夫岡·希弗爾布施說,鐵路一方面讓人們通達從前不易抵達的空間,另一方面卻也破壞了起點與終點之間的「旅行空間」:「這個中間物,或者說旅行空間,過去在使用低速的、勞動密集型的始生代交通技術時,是可以慢慢‘欣賞’的,在鐵路上卻消失了」,隨之消失的還有「舊式的地方認同感」(沃夫岡·希弗爾布施【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高鐵無疑讓這種「消失」更加徹底,它用一個個瞬間所跨越的歷歷晴川、沃野千裏,對於車廂裏無暇四顧的乘客來說是那麽遙遠,又那麽隔膜。

【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德]沃夫岡·希弗爾布施著,金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7月。
作為資深打工人,我曾經因工作去過很多從沒去過的城市,但如今對它們的記憶似乎大都只有某個具體的目的地——酒店或辦公樓的室內空間,而旅途——無論是從出發地到目的地還是在目的地城市之內的交透過程——好像真的被「消滅」了。我不知道是因為當時的旅途景觀都在碎片工作的「一會兒工夫」裏即時性地遠去,還是記憶選擇性地遺忘了這些在潛意識裏並不重要的「過程」。
鮑曼說:「在現代的時空之戰中,空間是戰爭笨拙遲緩、僵化被動的一方,只能進行防禦性的壕塹戰並阻礙時間的前進。時間則是戰爭積極主動、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遠具有進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領的力量。在現代時期裏,運動速度和更快的運動手段在穩步增長,掌握了最為重要的權力工具和統治工具。」(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班味高鐵」可謂這種現代「時空之戰」的典型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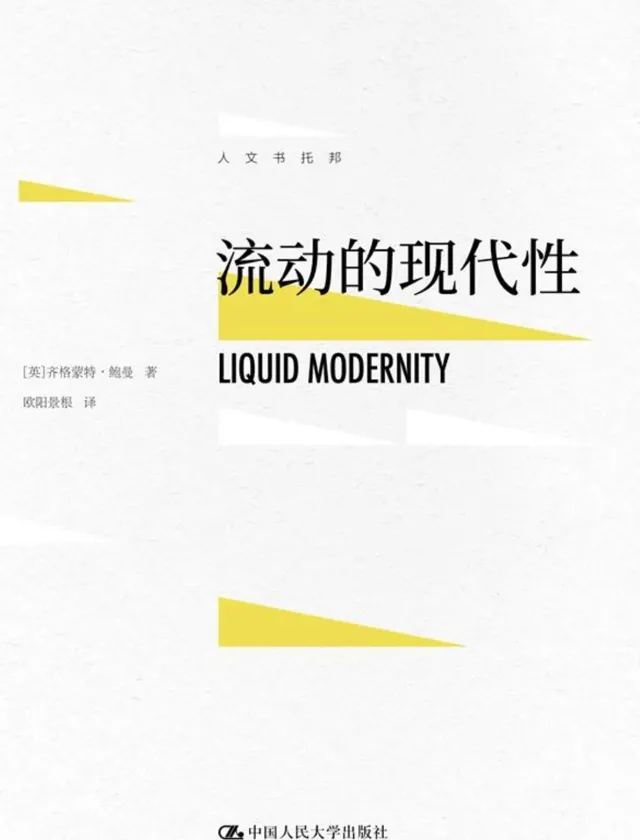
【流動的現代性】,[英]齊格蒙特·鮑曼著,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然而「旅途性」空間的「被消滅」,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因為我這個資深打工人的心底,好像一直存留著對於美好「旅程」的眷戀。我的家鄉是滬寧線上的中間城市——江蘇無錫,去南京讀本科的時候,滬寧高鐵往西北方向開,過了鎮江,漸漸能看到起伏的丘陵,穿過幾個山洞,也就到了南京;去上海讀研的時候,滬寧高鐵往東南方向開,一路平疇,過了蘇州,沿線就是陽澄湖,晴好的天氣裏能望見水光瀲灩。「包郵區」這迥異的旅途風貌至今鐫刻在我的記憶裏。
工作後有一段時間,我時常開車往返無錫和上海之間,但我不走距離更近、限速寬松的滬寧高速,而寧願繞彎走滬常高速,原因就是兩段旅途不同的體驗:開滬寧高速就像吃有「班味」的工作餐,絕對劃算和正確;而滬常高速在太湖邊劃出一道優雅的弧線,穿過名勝舊跡,途中能看到起伏的丘陵和山頂的古建,一個個高速出口還連綴起「南泉」「望亭」「東渚」「藏書」「天池山」「胥口」「木瀆」「橫涇」「光福」「香花橋」這些美麗的名字。
「旅途性」的空間絕不僅僅存在於從一城到另一城的大尺度裏,而且可以孕生在任何一種規模的「過程狀態」之中。

【大學生軼事】(1987)劇照。
在南京讀大學的時候,我在城郊的仙林大學城生活過兩年,學校又在大學城的邊緣位置,可謂「城郊之城郊」。那時我們要進城,只能坐公交,有些路線甚至還是那種十分顛簸的老式公交車。後來,當我們要搬去市中心的校區時,地鐵通了,但我和好友有時仍然會選擇坐公交。我們戲稱,和地鐵相比,那種又慢又顛的老式公交車真有幾分「蹇驢」的味道。「從前慢」的「學生郎」坐在車窗邊一路顛簸、一路發呆,讓我們聯想到「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的蘇軾,「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的陸遊,還有「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的孟浩然。
你會不會說我酸?但「酸味蹇驢」和「班味高鐵」確乎是兩種迥然有別的「過程狀態」的隱喻。
和「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的「班味高鐵」不同,「蹇驢」是慢的,散淡的,沈浸在過程之中的,它讓空間「制衡」時間,讓旅途「制衡」目的地。「郊外淩兢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內,趣入春風柳絮中」(唐彥謙【憶孟浩然】):讀到這幾句的時候,打工人們也是要心動的吧?
手段與目的,過程與結果
忍不住針對有熱度的「班味高鐵」寫點什麽,是因為這一現象讓工作與生活、旅途與目的地這兩組重要的當代關系交疊在了一起,而背後則是更為抽象的手段與目的、過程與結果之爭。
前些年人們在反思金錢的意義時,不時能聽到一句話——「錢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很多人把金錢本身當成了目的」。這個關系框架如果轉用在工作和生活之上,似乎也是適用的:工作只是手段,生活才是目的。一些人類學著作描繪了原始部落裏的勞作狀態,那大概代表了前現代社會工作的原初面貌——工作和生活、手段和目的尚沒有二分,勞作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生活。中國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計」,傳達出的也是這樣的意味。到了現代社會,工作、職業成為人們實作特定生活、人生目的的手段,二者產生了分化。而在資本主義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本性驅動下,手段和目的「異化」地纏結在一起:「營利變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手段。對於人天生的情感而言,這簡直就是我們將談到的‘自然’事態的倒錯,毫無意義,然而如今卻無條件地公然成為資本主義的指導綱領。」(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愛在黎明破曉前】(Before Sunrise,1995)劇照。
更要命的是,即使工作和賺錢不是人生的目的,越來越多的人也不知道「目的」為何物了。在「手段」(means)和「目的」(purpose)之間,可以存在無數層「目標」(objective),習慣了KPI和「結果導向」的打工人也習慣於把「目標」當作「目的」。有一句英文名言,譯成中文大意是:應該根據星辰來確定航向,而不是追隨來往船只的燈光。(Set your course by the stars,not by the lights of every passing ship.)「目的」就是那「頭頂的星空」,只要朝向「北鬥」的方向不錯,航路和旅途的曲直緩急和階段性結果,似乎就並沒有那麽重要,因為內心始終是篤定的,旅程本身就是體驗和價值所在。
換言之,如果能更好地把握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也就能更好地把握過程和結果的關系:結果固然重要,但過程也需要更松弛地「敞開」。當下職場高度膨脹的工具理性的可悲之處在於:一方面消滅目的,把手段當作目的,另一方面消滅過程,把結果奉為圭臬。消滅了「間隙時間」和「旅行空間」的「班味高鐵」,大概就是這樣一種職場生態的隱喻。
回到開頭的問題——我們能做什麽呢?作為打工人,我能想到的比較關鍵的對策,是重思和重建個體的「目的」性:在職業發展的「目的」甚至人生「目的」的全景中審視每一趟旅途,它的值與不值,它的個中況味,它的勤進或背離,它對於主體而言的意義感,都會更加清晰。

【上班一條蟲】(Office Space,1999)劇照。
重建「目的」事實上也是在工具理性膨脹的職場生態中重新呼喚價值理性,它有可能讓打工人從被動的勞動者轉變為主動的工作主體,讓「班味」變成「自驅」。而作為社會共同體的一員,我想有必要呼籲一種更加開放多元的價值取向,即當代職場、當代社會的運作並不只有「班味高鐵」這一種範式,我們可以反思它的合理性,也可以享用它的靈活便利,同時,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創新創造的可能性。
最後,如果「班味高鐵」也算是移動辦公、靈活辦公的一種最新形式的話,我想用尼基爾·薩瓦爾在【隔間:辦公室前進演化史】中寫下的一段話來作結:
「靈活性,就像科技一樣,是一種工具,一個機會:它就在那裏等待著,等待著人們去拿起來享用。……最後,就看辦公者是否能賦予這份自由真正的意義:看看他們是否能把勞工合約打磨成切實有效的合約,看看他們是否能將這份‘自主權’行使得真實可靠,看看他們是否能讓辦公空間真正屬於他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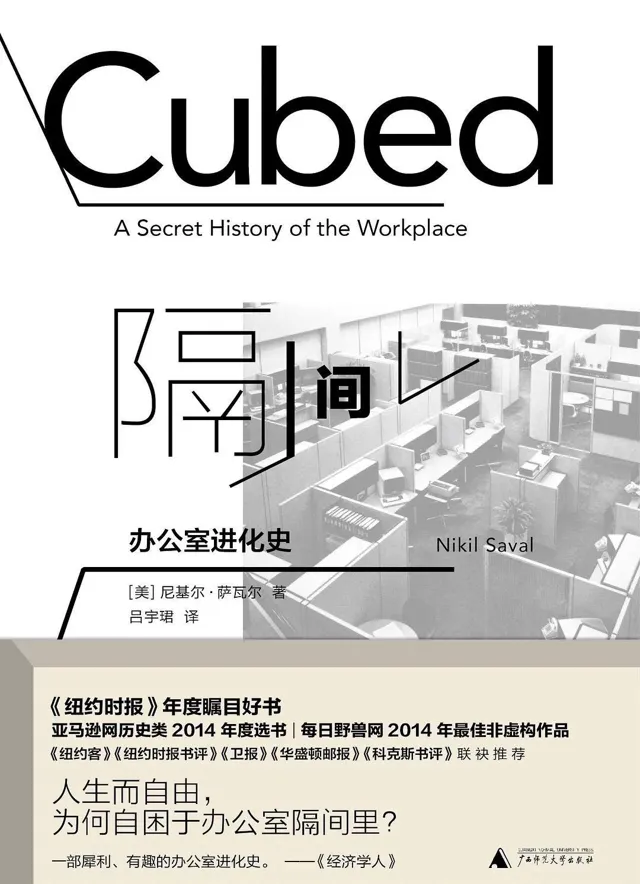
【隔間:辦公室前進演化史】,[美] 尼基爾‧薩瓦爾著,呂宇珺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18年5月。
「班不班味」,你可以選擇。
作者/徐一超
編輯/西西
校對/賈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