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問題,不禁翻出了幾年前的日記,好幾年過去了還是不忍回看。
PS:文中的「大黑嘴」就是我家貓的名字。
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 小雨
今天我家「大黑嘴」不見了。
昨天它一天沒動彈,整日不進食,把它最愛吃的香腸遞到嘴邊,也不予理睬,只是靜靜地縮作一團,半瞑著雙眼,還嘔吐了幾次,昨晚出門,至今未歸。
希望別是誤食了什麽有毒的食物,離家自生自滅了。
我心裏一天都不是滋味,快回家吧,家裏買了魚。
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 晴
今日「大黑嘴」回家了。
渾身臟兮兮的,失去了以往的神氣,形容枯槁,面色憔悴,步履遲緩。
依舊是不進食,多次嘗試去喝水,但每次都下不去口。
我估計它是在外面誤食毒物了,都說貓有九條命,你一定要熬過去。
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陰
「大黑嘴」還是沒能熬過去。
早晨迷糊中聽到它的死訊,我以為是在做夢,還想著如果它今日還不進食,就用註射器往它嘴裏灌牛奶。豈料,昨夜它鉆進了一個櫥洞,在一個舊書包裏,咽下最後一口氣。
午飯後,心神不寧,我沒法不想這件事。便玩了會小遊戲轉移下註意力,還買了點裝備,玩著玩著,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好一陣子。
「大黑嘴」也算幸運,畢竟它死去,還有人類為它傷心流淚。較之它的許多同類,也不枉費短暫的貓生。它才半歲,還未成年,竟不幸夭折。
貓應該是誤食有毒食物而死。
人或是其他動物中毒後可能很快就死了,記得小時候家裏有條小狗,誤食了鼠藥,很快就口吐白沫死掉了。都說貓有九條命,好多年前我家曾有只貓,被捕鼠夾夾斷了脊椎,下半身完全癱瘓,這種情況下,它用前肢拖著下半身,匍匐著活了下來,最終痊愈。
「大黑嘴」用三天時間耗完了九條命,若真是如此,我真希望它就只有一條命,便不用熬這麽漫長的三天。薛定諤肯定沒有痛失過愛貓,不然它肯定不會假設貓來做思想實驗,貓的生命力頑強,它會比別的生物遭受更長時間的痛苦。
這三天它吃不下飯,喝不下水,嘴角總是掛著粘液,微露著粉紅的舌尖,腹中早已吐的什麽都不剩了,昨晚我抱它進窩裏,它吐了些白沫,味道極為刺鼻,我相信那是化學制品產生的刺鼻味道,而非生物自身產生的氣味。每吐幾次還會伴著一聲尖而長、淒慘的叫聲,比踩到它尾巴的叫聲還尖促,使我坐臥不安。
我真的以為它能好起來,因為昨天它還能順著竹梯爬到房頂,雖然動作比平時遲緩百倍,它以前是身手最敏捷的一個。這幾天還以此種方式出去過幾次,回來時還緩慢晃動著尾稍,我相信它能撐下去。可能因為難受,無論在哪兒待一會都要挪挪地方。有時我見它蹲在冰冷的地上,便給它抱到太陽下柔軟的棉絮上,它蜷在那不動,過段時間再看時,它常出現在有水的地方。
它應該是想去喝水,除了趴著不動,便總是會挪步到自己的水碗,衛生間的水盆,水桶,院子裏的小水窪處,它想喝水,但是喝不下。我也試著讓它喝,純凈的水,流動的水,溫水,在碗裏,在盆裏,在桶裏,在地上,都不行。我為什麽就沒早點想到用註射器往它嘴裏灌呢,如果這樣讓它喝些水,說不定能稀釋毒素。但這些都已經晚了,它最後一面見的應該是我,夜裏我起床尋它不見,以為它又出門了。半夜裏我還聽見過它嘔吐的聲音和一聲慘叫。
我媽說,今早晨在櫥洞裏發現它時,體溫還未散盡。舊書包裏還有少許糞便,「大黑嘴」生前是那麽的愛幹凈啊。據說動物死前,會排凈身體,它什麽都排凈了,就是沒能排凈毒素。
從小到大,我家養過好多只貓。這是第二只早夭的,上一只還是十九年前,一個寒冷的冬夜,一只一歲多的貍花貓枕著紙盒死去。
「大黑嘴」是我家第一只長毛貓,毛色黑白。它毛發很長,不易打理,每次舔舐時,都只得把頭揚地高高的,顯得有些笨拙和吃力,始終保持幹凈、順暢、蓬松。有時出去打野歸來,弄得滿身浮土,沾滿了草籽、枯葉,你想伸手替他清理,剛一接觸,它便一頭栽倒在地,歪著腦袋在地上打起滾來,還架起前肢想與你比劃幾下,你只得作罷。可是幾個小時後你又不經意地看起時,它依舊是黑的發亮,又潔白似雪。背部的黑毛自然中分,腹部的白毛落向下垂,每次收起四肢趴著的時候,總能把爪子蓋住,遠看像水墨色的麥垛。兩條後腿一黑一白,每次慵懶地邁開貓步,我們就愛從後面看它兩腿一擠一擠地前後交替著,像活動的太極兩儀圖。我愛把手伸到它腹部取暖,那裏像布滿了卷曲的羊毛,溫暖又柔軟,它通常是不反對突然塞進的這只涼手,除非是興起時,又少不了一場「大戰」。由於長毛蓬松,它的尾巴顯得特別寬大,總使我想起雪豹,平時它總愛漫無目的地搖晃著它,或是高高翹起,掠過我家桌子,板凳和我們的腿。它的面部整體是黑色的,腮部垂著長鬢,使面部呈現出紡錘狀。白鼻梁,嘴角至兩頰有兩塊不對稱的黑色,好似銜蟬,因而得名「大黑嘴」。據說蘇東坡晚年有只名喚「烏嘴」的大狗為伴,從海南回家時,還帶著它一同渡海。我爸給貓起名,竟無意間與古人暗合。父親最喜歡它的眼睛,與其他幾只貓不同,略深的琥珀色,像巴洛克風格家具的顏色。一般的貓慵懶時總愛皺起眉頭,半瞇著眼睛,「大黑嘴」很少如此,總是把眼睜得圓圓地出神地盯著你看,憨頭憨腦地最招人喜愛。它總愛順著竹梯爬到房頂享受午後冬日的暖陽,舒展開身子,探出腦袋,睜圓了眼睛向下望著你,身下是家,眼前是你,背後是湛藍的天空。

在外面玩耍結束,它每次回家的路線是固定的,而且總會踩響房頂一塊活動的瓦片,我們坐在屋裏看著電視,也能知道它回家了。順著竹梯往下下時,竹梯會稍微發出吱呀的聲響,它在落地前會習慣性地「嗚」一聲,並且聲音會隨著落地時身體的震顫而被加重和拖長。於是,它斂去下房時的敏捷,翹起雞毛撣子般的尾巴,邁著貓步,慢慢悠悠地向屋裏晃去,蹭蹭我們的腿。巡視一圈家裏熟悉的一切,等你一起身,它便躍上還熱乎著的板凳,梳洗一番毛發後,逐漸蜷縮起身子,打起了盹。
前幾天下大雪,站在貓的視角,雪片應當很大。這是「大黑嘴」第一次見雪。起初,它躲在屋裏出神地張望著。潔白的爪子向外探了探後,便義無反顧地融進了雪裏。一步一個深坑,它也開始也是一步一頓,後來逐漸放肆起來,我猜這時它可能覺得這是我們玩的什麽把戲。它決定上房看看,竹梯上落了厚厚的雪,積雪向上聚攏好似朝天的斧刃。「大黑嘴」跳上一級後,猶豫片刻,謹慎地蹬梯上房,除了滑一點,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上房轉了幾圈,望向四野,但見密匝紛飛,天地一白,心裏覺得肯定不是主人在作祟,睜圓杏眼向下看了看,便躍下房頂,踏著碎瓊亂玉溜回房中,黑貓變作白貓,這只「白頭翁」抖了抖身子,殘存的雪花和水滴在燈下閃爍著。思忖片刻感覺意猶未盡,便轉身又紮進了這個新奇的世界。
我家還有幾只貓,「小黑」是「大黑嘴」的母親,體態苗條,毛色貍花兼乳白。幾只幼崽哺育完成後,它就離窩了,應該是天性使然,是時候讓小貓獨自闖蕩了。其實也並未離家很遠,我們每次晚飯後散步,都能在同一個地方遇見它。喚它一聲,她便「喵嗚~」叫兩聲,跑過來打起了滾。你若伸手去抱它,通常也不反抗,只是距家近時,它便掙脫你的懷抱,消失在了灌木叢裏。你往家走幾步回身望去,說不定能在草叢裏看到一個熟悉的腦袋正望向你。

「小黃」和「小黑」是一奶同胞,也是只母貓,已經度過三個春節了。其毛色兼黃、白和貍花三種,較之「小黑」就體態肥碩些。現在肚子很大,向身體兩側凸起,應該是懷上了第三窩小貓了。「小黑」產崽時,它離家了一段時間,偶爾會回家探看,回家嘛,自然是大搖大擺地,奈何小貓們不認識它們的姨娘,紛紛拱起脊背,炸開毛,一齊向這個侵犯領地的陌生人示威。「小黃」也是哭笑不得,又懶得和這些小崽子們理論,只好沒趣地走開。幸好前段時間,它們的關系得以緩和,可能是小貓們看到「小黃」對它們毫無敵意,在主人的眼裏也不像「外人」那般對待。外來的貓一般剛在屋檐探出頭,就被竹竿趕跑了。漸漸地它們四個像一家人一樣生活在了一起,小黃對它們也是呵護備至,視若己出。原本小黃搶奪食物最為兇悍,如今在小貓面前完全換了個樣子,眼睜睜看著小貓們把它嘴裏的食物奪走,它也只是舔舔嘴巴,悻悻地蹲在一旁,等到它們滿足地洗起臉來,再探過去拾些殘羹冷炙。

和「大黑嘴」一窩出生的還有兩只,「小黑嘴」和「小雪」。「小黑嘴」又叫「二黑嘴」,模樣和「大黑嘴」很像,都是長毛,就是白毛多了些,黑毛裏夾著更多貍花色,額頭以下基本是雪白的,是個俊朗的白面郎君,最重要的是嘴角僅有花生仁大小的黑點,因此喚作「小黑嘴」。有趣的是它黑色的尾巴稍上有一撮豌豆大小的白毛,與「大黑嘴」下巴處的黑點遙相呼應。「小黑嘴」活潑好動,每當我房門閃出一點空隙,眼前一道黑影閃過,它早已出現在我的書桌上,鍵盤上。此時我如果正伏案讀書碼字,它必在桌上趾高氣昂地踱來踱去,在書上、白紙上、鍵盤上留下一串串「梅花」標識,再將腦袋伸進你手掌,蹭來蹭去。趕是趕不走的,你只得起身離去,它便立馬隨你出屋,然後你一個箭步殺回書房,緊閉房門。這也並非萬事大吉,它在門口扣門不成後,便會跳上窗台,隔著玻璃和你對視,時不時地叫喚幾聲。尤其在晚上,我房裏台燈亮著,幾聲敲擊玻璃的聲響後,掀開窗簾,總能看見窗外有張白凈俊朗的貓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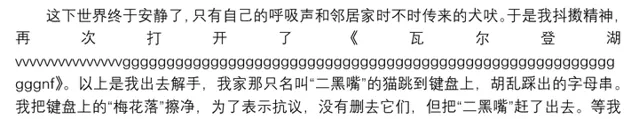
「小黑嘴」不像另外幾只那樣挑食,它常常清理其他貓飯後的殘渣。有一次,它在我爸眼皮底下跳上桌子,正在享用還未下鍋的韭菜餡素餃子,我百思不解,後來扔了塊生面團,它湊上前來,大口啖之,竟然有滋有味。
「小雪」是小三只中唯一的母貓,毛較短,體型也最小。母親告訴我它本是三只裏最重的,只是患了場病後,落下了類似哮喘的病根,便瘦了下來。它通體雪白,僅在額頭上點綴著些許黃色,重要的是整個尾巴是黃色的,古稱「雪裏拖槍」,可能就是這樣。落下哮喘的病根後,它的呼吸似乎有些困難,胸腔呼吸起伏振幅很大,光盯著它的鼻子,就能看出他在喘氣。尤其是睡覺的時候,它總需要枕在其它貓的身上睡覺,「大黑嘴」和「小黑嘴」總是被「欺壓」的物件,現在「小黃」也不能幸免,好在大家都不在乎這些,任由「小雪」時不時地將腳踩在它們臉上睡覺。對於這種「蹬鼻子上臉」的行為,它們皆回之以鼾聲。
幾只貓通常都團在一起睡覺,尤其是我家客廳有張桌子下帶了一個小小的桌洞,離沙發近,在這裏它們能清晰地聽到我們談話,從而安心入睡。由於空間狹小,三只貓總是摞起來睡,將裏面塞得滿滿的。無論「大黑嘴」和「小黑嘴」誰來墊底,「小雪」一定在最頂上。總之,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其它貓在,「小雪」都要跑過去枕在它門身上睡覺,它們也習以為常了。有時我們也不能幸免,如果此時你正坐在沙發上,四下無其它貓,「小雪」便湊了過來,後腿踩在沙發上,前爪放在你的腿上,頭枕前肢睡了起來。我家茶幾一角,二層有一塊很窄的平台,冬天陽光正好照在上面。所有的貓都愛爭奪這塊寶地,大黃身材較大,能填滿整塊領地。「小雪」經常後腿站在地上,雙爪搭在小黃身上,頭枕兩爪,直直地站著睡,這種奇異的睡姿總能引起家裏人的圍觀。既沒有貓也沒有人時,它常趴在椅子上,從脊梁向頭部逐漸降低,爪子貼在椅子邊緣,腦袋懸空朝下,這是它最常見的睡姿,這姿勢讓人心生憐意,可能這樣它能呼吸舒暢一些,我們還有其它貓們瞧它身子有恙,平時對它也稍微寬大些。可是即便如此,它吃起飯來可謂六親不認,常常叼起一塊就跑。它對吃飯這是也最為靈性,每當廚房都切菜聲,它便總會出現在你腳下,嚶嚶賺得你憐憫,常常能得到一個蝦頭或是魚尾,有時也鎩羽而歸。「小黃」也常常陪「小雪」在廚房等候,至於另外兩只,早已打作一團,滿屋裏四竄追逐了起來。只有廚房傳來魚腥味的時候,它們倆兄弟才會溜達過來,望廚房門口一坐,你們看著辦吧,反正我就這麽可愛無邪地盯著你,我們只得交魚投降。同樣的招數也適用於我們吃飯的時候,它們早就在你之前出現在桌子下方,盯著你叫了起來,「小黃」通常不叫,它覺得作為它們的長輩,這樣會有失身份。但是它那雙水汪汪的大眼一直盯著你,恐怕鐵石心腸的人也會情願自己少吃幾口。這幾天家裏都有魚吃,它們也滋潤不少,除了可憐的「大黑嘴」吃不下。
「大黑嘴」身形矯健,出手敏捷,平時也最有神氣,我家人在它身上投入的感情也最多。前幾天它不知從哪裏偷了一條魚,足有兩斤多重。叼起著沈甸甸的大魚大搖大擺地走下竹梯,在院子裏和夥伴們大快朵頤起來,至今屋檐的一角還有幾片刮下來的魚鱗。但這次「大黑嘴」沒有上次走運,他不知道吃了什麽東西,卻成了最後的晚餐。它們幾小只從出生就在一起,吃在一塊,睡在一塊,每個清晨,等我父親起床時,它們也紛紛伸著懶腰,打著哈欠走出來,活動幾下便撕作一團,打鬧累了又抱在一起互相梳理毛發。
這幾天突然就變得不同了。起初「大黑嘴」難受地尖叫時,「小黑嘴」還會趕緊湊上前去,替它梳理記下毛發。可是「大黑嘴」通常遠遠地縮在一隅,後來它們也不敢近前了,似乎在恐懼什麽。和往常不同,「大黑嘴」獨自在櫃子睡去,這次它沒有等來黎明,這櫃子曾是它第一眼看世界的地方。
今日,春寒料峭,此時窗外的雨漸漸大了起來。「小黑嘴」這幾日躁動異常,又在門口扒門了,我準備去放它進來。相信,今後我每想起我家「大黑嘴」,就一定會想起冬日的暖陽,它行走在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