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聯系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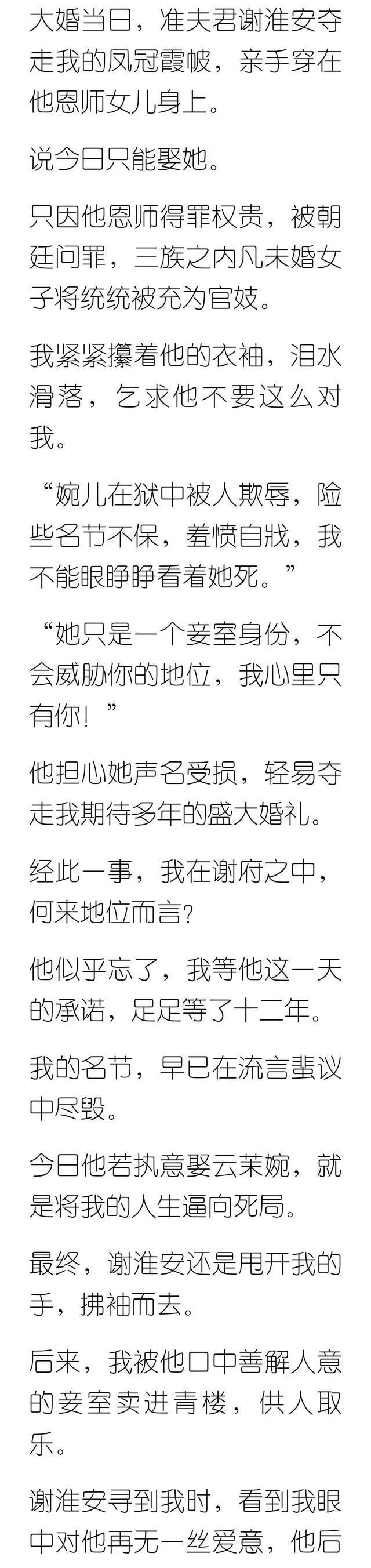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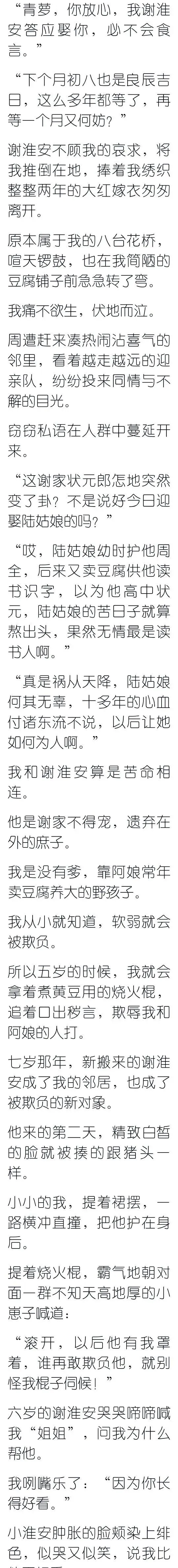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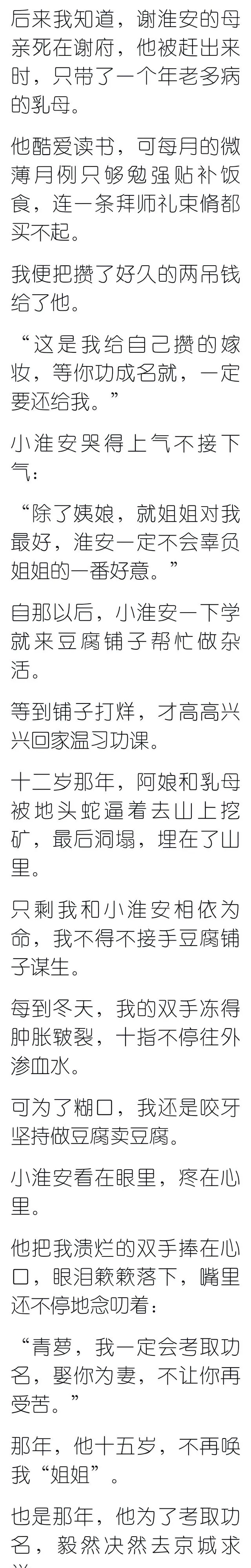
也是那年,他為了考取功名,毅然決然去京城求學。
得了他的承諾,我對自己更加苛刻。
一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將賣豆腐攢下的銀錢全部交給他。
一邊撒潑耍橫應對地痞流氓的騷擾和調戲。
苦等四年後,得知他如願考取狀元那一刻,淚水如決堤的洪水,流盡了多年的心酸和苦楚。
可我歡歡喜喜等來大婚這天,謝淮安卻奪走我的嫁衣,轉身迎娶他的恩師之女。
此時,一陣輕浮猥瑣笑聲在一片唏噓聲中格外刺耳。
「陸小娘子長得這般俊俏,謝狀元不懂憐香惜玉,我們哥幾個可願為代勞,就不知陸小娘子願不願意……哈哈哈。」
耳邊充斥著這些汙言穢語,每一句都像鋒利的刀,切割著我支離破碎的心。
淚水模糊了視線,浸濕了身下的泥土。
我羞憤難當,拼勁力氣爬起來,關上大門,掛上門栓。
又用一根粗大的柱子死死抵住。
夜晚,一只只被束縛雙腳的公雞被扔進院來。
只因本地有不成文的規定,夜裏往孤孀院裏扔公雞,若沒遭退回,便是應允該男子進屋。
我抓起公雞,一只只剪斷翅膀,扔出院子。
大門被拍的「哐哐」亂響,院外是男人們調戲的淫詞浪語。
我不敢進屋,抱著燒火棍蜷縮在墻腳,死死盯著門口,瑟瑟發抖。
默默承受著此刻的羞辱和絕望,任由淚水肆意流淌。
那個曾經給我無限承諾和期許的謝淮安,親手將我推進了無盡的深淵。
好不容易挨到天明,我緩緩站起身,雙腿因長時間的蜷縮微微顫抖。
望著那扇被拍得搖搖欲墜的大門,我心裏明白,這地方,已經容不下我了。
我等不到一個月後謝淮安娶我,也不打算再等他。
我渾渾噩噩跑進房裏收拾東西,如今這個家,我最割舍不下的便是那兩只養了四年的小白兔。
它們是謝淮安上京求學後,唯一與我消遣逗樂的夥伴。
我準備給隔壁王奶奶一些銀錢,讓她幫我照料著。
剛出門,竟迎面撞上一臉喜色的謝淮安和雲茉婉。
謝淮安牽著她的手,眼中的深情濃得要溢位眸子,笑容如三月春風般和煦,仿佛手上牽著的,是他此生至寶。
而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的眼。
當雲茉婉看清我的樣子時,臉上莫名閃過一絲妒意。
謝淮安看我背著包袱,笑容僵在臉上:
「一大早不開鋪做生意,背著包袱幹什麽?」
不等我開口,他似想起什麽,臉色瞬間沈了下來:
「青蘿,就為了昨日之事,你要走?」
「你一向懂事,就不能體諒我這一回?」
「恩師教導之恩我無以為報,只能助婉兒脫離困境,方能心安少許。」
「你若因這般芝麻綠豆小事記恨婉兒,離我而去,日後誰還敢娶你為妻?」
原來在謝淮安眼裏,與我成親,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躲在謝淮安身側的雲茉婉半掩朱顏,小聲抽噎:
「青蘿姐姐,都是婉兒不好,耽誤了你與淮安哥哥的良辰吉時,可我,我……」
雲茉婉泣不成聲,淚水漣漣,很快沾濕巾帕。
惹得謝淮安心疼不已。
他輕撫雲茉婉的後背,將她攬入懷中,她才得以說出剩下的話:
「淮安哥哥為了救我才委屈了姐姐,日後,我定會克制自己對淮安哥哥的愛慕之心,不去打擾你們。」
「只要能看著淮安哥哥過得恣意快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今日我央求淮安哥哥過來,就是為了接姐姐你回謝府的,妹妹必定好生侍奉姐姐,還請姐姐千萬莫要推辭。」
我混跡市井多年,早已學會察言觀色。
她眼底一閃而過的得意和算計,到底是沒能逃過我的眼。
接我回謝府是假,羞辱我,向我示威才是她此行的真正目的。
謝淮安作為謝家子孫,只因庶出從小就被趕出謝府。
我一個大婚當天被遺棄的女子,真回到謝府,會有人把我當人看嗎?
謝淮安如此聰慧之人,豈會不懂這個道理?
他怕是得了心愛之人,歡喜的得不願多在我身上費神。
我突然覺得可笑,也懶得與他們多費口舌。
越過依偎在一起的二人,就往外走。
雲茉婉忽然拉住我的衣袖,哭得梨花帶雨。
「姐姐執意要離開,就是不肯原諒妹妹,我心中有愧,還不如就此死了……」
她說著就要往那殘破不堪的門柱上撞。
謝淮安慌忙伸手,一把拽回雲茉婉,冷冷看向我:
「陸青蘿!婉兒大病未愈,生怕你思慮過甚傷身,拖著病體來看望你,請你回府。」
「她為你考慮周全,你為何不能大度些,圓了她的念想!」
謝淮安語氣難言不耐,他認定是我不識好歹。
我氣得渾身發抖,耳畔嗡鳴作響,死死揪住衣角才勉強逼自己站直身子。
「謝淮安,從昨日你棄我而去,你我就再無瓜葛,我是去是留,你們憑什麽替我做主?」
「就憑婉兒待你一片赤誠之心,就憑我是你的夫婿!」
指甲深深嵌進皮肉,半晌,我才從滅頂的窒息感中掙脫。
從懷中掏出謝淮安從小佩戴,被他當做定情信物送給我的玉佩,狠狠砸在他身上。
被我小心呵護多年的玉佩落在地上,應聲而碎。
一如我和謝淮安這些年的情誼。
淚水忍不住滑落,我抹幹眼淚,不容置疑道:
「謝淮安,我不嫁你了!」
余光中,倒在謝淮安懷裏的雲茉婉微微勾起唇角。
謝淮安眉心微蹙,聲音帶著怒氣:
「青蘿你休要胡言,你不嫁我還能嫁誰?」
「你我情深意厚,方圓十裏皆知,誰又敢明媒正娶把你娶回家?」
我倔強地仰起頭:
「不勞狀元郎費心,讓開!」
謝淮安臉色愈發陰沈:
「青蘿,你非走不可嗎?」
我堅定地往外走,沒有理會。
「青蘿,留下你,是婉兒的心結,恩師之禍我無力回天,但我不願她為其他瑣事再傷心。」
「來人!」
隨著謝淮安一聲大喝,兩個黑壯家丁沖到眼前。
「打暈了,抗走!」
我被隨意扔進馬車,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我恍惚聽到謝淮安輕聲安慰雲茉婉。
「婉兒,若是我早些知曉你心意就好了,我斷然不會與青蘿定下婚約……」
我不明白,他們已終成眷屬,為何還不放過我?
等我醒來,已是翌日午時。
燥熱的陽光穿透窗台,和著屋內一股陳就發黴的氣息,帶來一絲不暢的悶意。
我緩緩坐起身,只覺脖頸酸痛,頭腦昏沈的厲害。
腹中饑餓,嗓子也幹澀地發不出聲響,只想尋一口水喝。
這時,房間門被從外開啟,帶起一層厚厚的灰塵。
雲茉婉掩住口鼻,帶著丫鬟,端著一壺茶水和食盒,眉眼帶笑的走進屋來。
「姐姐可真嗜睡,你若再不醒來,淮安哥哥都要為你請郎中來了。」
我無視她的虛情假意,向她身後看去。
雲茉婉淺淺一笑:
「別看了,淮安哥哥高中狀元又剛剛大婚,前來祝賀的達官貴人都要把門檻踩碎,哪有時間來看望姐姐。」
雲茉婉今日高傲自滿,意氣風發的模樣與昨日楚楚可憐,情真意切判若兩人。
我一個眼神也沒給她,扭頭看向窗外。
不愛了,她就休想用謝淮安傷我辱我。
雲茉婉被我這份從容淡定刺紅了雙眼,臉上恨意漸濃。
她捏著我的下巴,面容扭曲,逼我與她對視。
「你一個賣豆腐營生的下賤女,憑什麽不正眼看我?!」
「即便我家族沒落,也比你這個下賤胚高貴千倍萬倍!」
「縱使淮安哥哥對你那般情深義重,我還不是一點點占據了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手指緊緊攥緊,手心傳來尖銳的疼痛。
她看著我的臉,忽然冷笑松手,輕撫我臉上紅痕。
「我答應淮安哥哥會好生侍奉姐姐,就一定不會讓他再在你身上費心。」
「姐姐昨日滴水未進,應該又渴又餓吧,妹妹早已準備好茶水飯食……」
她一邊說一邊從丫鬟手裏接過茶水,倒出一杯,笑盈盈端到我面前。
我舔了舔嘴唇,眼睛直直盯著茶碗。
下一秒,她卻猛地一揮手,茶碗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摔碎在地,熱茶四濺,噴濺在我單薄的鞋襪上。
滾燙茶水沾上肌膚,我痛得急忙縮回腿腳。
雲茉婉急忙捂嘴作愧疚狀:
「哎呀,真是抱歉,妹妹在獄中受過傷,手無縛雞之力,沒傷到姐姐吧?」
她眼中閃過一絲狡黠,隨即又換上了滿臉的關切與歉意。
身後的小丫鬟低頭嗤笑。
「妹妹待會兒再給姐姐打一壺涼茶,來,看看妹妹給姐姐帶了什麽吃食,姐姐肯定喜歡。」
小丫鬟揭開食盒,一股肉香飄散出來,引得腹中更是饑餓。
雲茉婉把一盤金黃酥脆的烤肉端到我面前。
我猛地睜大眼睛,眼前竟是一只完整的烤兔肉,一股不詳的預感湧上心頭。
「姐姐不僅將淮安哥哥養護照顧的很好,就連這兔子,都比東市上買來的肥美。」
「另一只,妹妹已經幫姐姐嘗過了,外酥裏嫩,十分美味。」
她搶走謝淮安,如今連唯一屬於我的兔子都不放過。
所有的痛苦和憤怒交織在心頭,我像是快要溺亡的人,死死拽著衣角。
「為什麽?為什麽要這麽對我?!」
雲茉婉勾起嘴角,笑得冷冰冰:
「為什麽?」
「姐姐既然決定離開淮安哥哥,為什麽還要占著陛下給他的賞賜?」
「本以為謝府也算富庶人家,沒想到光贖我就用盡了家產,我阿爹阿娘還在獄中受苦,沒有打點,他們怕是連這個冬天都熬不過!」
「你識趣就趁早交出來,我可以大發慈悲,讓你離開的體面點。」
「你若不交出來,就休怪我不客氣!」
原來她千方百計把我留在謝府,就是為了那些賞賜。
早在謝淮安與我訂親時,就將那些金銀珠寶贈予我。
既是訂親的彩禮,也是回饋我這麽多年的照料之恩。
而我將其兌換成了銀票,全部存在錢莊。
她若不提及,我差點忘了還有這份意外之財。
我看著她,眼中只剩苦笑。
我並不貪戀謝淮安的財物,若她好生相求,我自會相還。
「雲茉婉,你的淮安哥哥清楚你的如意算盤嗎?」
正在此時,門外傳來謝淮安熟悉的腳步聲。
雲茉婉輕哼一聲,擡手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白皙的臉頰瞬間紅腫。
她抓起那只烤兔肉,猛咬幾口,最後將整只兔子塞進我手裏。
在謝淮安進門時,他看到景象是我正用力推開她。
雲茉婉柔弱無骨地摔向地面,謝淮安一個箭步飛沖進門,堪堪將人接進懷中。
她嚇得花容失色,伏在謝淮安懷中,一邊幹嘔一邊哭泣:
「淮安哥哥,我只是好心烤了兔肉給姐姐補身子,姐姐不但不領情,還,還如此對我……」
謝淮安捧著她被蹭花妝容的蒼白臉頰,心疼壞了。
再看向我時,轉臉陰郁,毫不猶豫揚起手,給了我一巴掌。
「陸青蘿!沒想到你竟如此劣性難琢,心胸狹隘之人!」
「枉費我曾將你當作此生伴侶,你簡直讓人,失望至極!」
「從今日起,你哪裏也不許去,就在這別院,好好反省!」
不等我辯駁,他已俯身抱起雲茉婉匆匆離開。
我緩緩松開緊握的手指,掌心有濕熱的血液淌下。
我們的情誼,最終是化作了秋風中的落葉,飄零四散,再無歸期。
也從那日起,謝淮安再也沒踏進別院一步。
沒人給我送水送飯,在這一方別院,我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
又渴又餓只能刨出院子裏的野草根充饑。
不到七日,院中再無可食之物。
如果就這樣死在這裏,我死不瞑目!
當我無力倒在院中,以為真的會餓死時,雲茉婉來了。
我心甘情願說出錢莊銀票存根的存放處,只為她手裏那半個饅頭。
為了茍活,我低聲下氣求她施舍的模樣大大取悅了她。
「你不是清高,自認為有一身傲骨嗎?還不是為了一口吃食,匍匐在我腳下。」
「自甘墮落的東西!」
她用力踢踹我的身子,模樣又兇又狠,仿佛透過我,看向曾經落魄的自己。
等她發泄完,我才虛弱開口:
「可以,放我出去了嗎?」
雲茉婉像是聽到什麽笑話,笑得身子發顫:
「這麽想出去啊?好啊,那我就成全你。」
「來人!」
幾個婆子從門外蜂擁而入。
雲茉婉用腳尖挑起我的臉,冷笑一聲:
「大婚那日她百般阻撓,要不是淮安哥哥堅持娶我為妾,我現在已充為官妓。」
「把她賣進怡春樓,這份恩寵就賞給她了!」
我惶恐地睜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話。
拼命掙紮身子起來,卻被她一腳踹回地上。
雲茉婉為了挖苦我,不問自答:
「姐姐莫不是還指著淮安哥哥來救你?他這些日子一直忙著幫我阿爹周旋,可是絲毫沒想起姐姐呢。」
直到被兩個婆子拖進怡春樓,我才知道雲茉婉並不是開玩笑。
老鴇子給我灌了一碗糖水,喜得眉開眼笑:
「長得可真水靈,就是瘦了些,皮糙了些,好在年二十了,還能賣個好價兒。」
「嘖嘖,看那不服氣的眼神兒,是個潑辣脾氣。」
「吊著這口氣兒,正好趁今夜斷了你紅塵念頭,以後老老實實在這給秦媽媽掙銀子,包你天天吃香喝辣,穿金戴銀,啥也不想了。」
我絕望地看著她們作踐戲弄,給我梳洗,撲上香粉,扔在一間上房的大床上,卻沒有一絲力氣反抗。
不到一盞茶的時間,房門被推開,伴隨著一道震耳欲聾的笑聲,仿佛連空氣都在隨之顫抖。
那人臉上滿是油膩笑容,眼中閃爍著淫邪之色。
「秦媽媽,這便是你說的?果真是個尤物,沒枉費我花重金相邀。」
秦媽媽一臉媚笑,湊近那人耳邊低語了幾句。
那人聽後,笑聲更加放肆,那雙細小的眼裏滿是赤裸裸的占有欲和即將得逞的瘋狂。
「好,今晚就讓我來看看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說著,他一步步逼近大床。
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上,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絕望,身體止不住地顫抖。
他停下腳步,油膩的手指挑起我的下巴:
「小美人兒,別怕,只要你乖乖聽話,爺會讓你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快活。」
我試圖掙脫他的束縛,可力氣在他那粗壯的手臂面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只能無助地掙紮著,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眼見他肥碩的臉頰湊過來,我死死閉上眼睛,牙齒扣緊舌根,認命般準備結束我悲苦不甘的一生。
可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身後大門「咣當」一聲巨響,被大力踹開。
門板撞到墻又快速彈回,被一只腳抵住,踢開。
「敢碰她,你找死!」
一道低沈有力的聲音喝道,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
肥胖嫖客的動作猛地一頓,臉上閃過一絲惱羞成怒與不甘,轉頭望向聲音的來處。
只見一位身著勁裝英姿颯爽的男子疾步騰空提膝,眼神銳利如鷹,裹著一身戾氣。
不等嫖客發狠,已經被砸的口鼻噴血,仰面倒地。
我重重舒出一口氣,松開牙關,眼淚滑過眼角,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激與希望。
來人解開身上的披風將我從頭包裹住,打橫抱進懷裏。
聲音溫柔如三月春風:
「陸姑娘受驚了,我這就帶你走!」
我將頭緊緊埋在他肩頭,泣不成聲:
「多謝黃大哥相救。」
老鴇子哭喊著上來要攔,被黃大哥一腳踢得滾下樓。
他一手抱著我,一手掏出一錠金子扔地上,冷冷看著她。
「日後再敢打陸姑娘主意,黃某必定端了你這怡春樓!」
老鴇子捂著頭破血流的臉皮,撿起金子張嘴猛地一咬,大喜過望,連連點頭。
而此時,謝淮安帶著一眾家丁拿著棍棒趕來。
他擡手狠狠扇了老鴇子一巴掌:
「大膽刁民,竟敢讓我妻子以色侍人,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老鴇子被一再出現的變故激得惱怒不堪,又見謝淮安一副書生打扮。
叉起腰來:
「你又是哪個旮瘩冒出來的雜碎,竟然敢打我?」
謝淮安急忙後退兩步與她保持距離,氣得臉頰通紅:
「混賬!大膽!」
「我乃當今新科狀元謝淮安,你這婦人逼良為娼,別說打你,今日就是拆了你的怡春樓也是你咎由自取!」
老鴇子一聽頓時坐地上捶胸頓足,嚎嚎大哭:
「你們官家是天,勢大,盡管著我們老百姓欺負,一個兩個都要來拆我的樓。」
「你們讓我這的姑娘們以後怎麽活?」
「我們雖是下九流行當,也是你情我願,有賣身契佐證,官家信口雌黃,你倒說說,我哪裏逼良為娼,你妻子又是哪位姑娘?」
謝淮安也不想多跟她纏結,直接報了我的名諱。
「就是今日被你們強搶進樓的陸青蘿!」
老鴇子立馬息了聲,指著黃大哥懷裏的我:
「陸姑娘是你妻子?那這位英雄又是……」
謝淮安一把扯下我頭頂的披風,在我即將露出臉時,又被黃大哥一把奪過,重新蓋在我身上。
只是方才匆匆一瞥,謝淮安也確認了黃大哥懷中的就是我。
他臉上余怒未消,咬牙切齒:
「陸青蘿,你好不羞恥,竟跟其他男人摟摟抱抱!」
「你立即同我回府,焚香沐浴凈身,我就當今日之事不曾發生,依然會娶你為妻。
「只是不再有八擡大轎,高頭大馬迎親,更不會宴請賓客!」
他慷概激昂,自以為這是對我天大的恩賜。
見我不回應,他又試圖掀開披風,被黃大哥錯身躲開。
在這裏露臉,即使清白之身,也會被人詬病。
黃大哥都知道維護一個女子的名節,可口口聲聲說要娶我為妻的謝淮安,卻要將我公之於眾,受眾人輕薄羞辱。
可名節與我而言,早就不復存在。
我拍拍黃大哥的肩,小聲道:
「黃大哥,放我下來吧。」
黃大哥以為我會順從謝淮安同他回謝府,手上的力道不僅沒松,反而將我往懷裏抱的更緊。
我的臉頰蹭到他裸露在外的肌膚,滾燙的,心跳猛然加快。
頭頂濃重的呼吸聲拂過耳畔時,帶著令人心猿意馬的微癢。
謝淮安的怒喝讓我理智回籠。
「黃大哥,有些事,我必須跟他做個了斷。」
黃大哥這才輕輕將我放下。
我裹著披風,只露出一雙眼,腿腳發軟,緩緩走向前來圍觀的人群中央。
謝淮安以為他的話震懾到我,臉上露出一絲笑意。
我在離他三步之遙的距離停下,認真地看著謝淮安。
堅定不移地說出同樣的話:
「謝淮安,我再說最後一遍,我陸青蘿,不嫁你這忘恩負義之徒!」
「你說什麽?」
我一把扯下披風,斬釘截鐵再次開口:
「我,不嫁你!死都不嫁!」
這時不知誰喊了一聲:
「喲,這不是豆腐西施嗎?我說這狀元郎看著這麽眼熟呢,這是人豆腐西施一塊塊豆腐供養出來的狀元啊。」
「你這麽一說,我倒是想起來了,聽說這狀元郎大婚當天,拋棄豆腐西施,迎娶他恩師之女,真是夠絕情的。」
「讀那麽多禮儀之書,竟做出這等忘恩負義之事,書都讀到狗肚子裏了唉。」
人群中的議論聲如潮水般湧來,帶著諷刺與謾罵,交織成一張無形的網,將謝淮安束縛其中。
以前,有人欺辱他,都是我沖在他前面,為他擋下那些惡毒的話語和粗暴的舉動。
可如今,我只是冷冷看著他,無動於衷。
謝淮安環顧四周議論紛紛的人群,申請慌亂,臉色難堪。
「住嘴,一群蛇鼠蟻輩,你們又懂什麽?!」
最終,他還是將矛頭指向了我。
「陸青蘿,你真是泯頑不靈,事到如今還分不清孰輕孰重!」
「除了我,還有誰願意要你,你真準備在這青樓讓人輕薄一生嗎?」
謝淮安是知道怎麽往我身上捅刀的。
可此時,我心中卻沒有一絲難過。
「這一生,非要嫁人嗎?」
「我願意!」
兩道聲音同時響起,我驚詫地身子一震。
一定是我餓出毛病,聽岔了。
可下一秒,那道熟悉的聲音在身後響起,越來越近。
「陸姑娘不嫁你,是因為你不配,而不是她不夠好。」
「狀元郎又在清高什麽?」
謝淮安氣得臉色鐵青。
「我還未質問你是何粗鄙野人,不知廉恥,不懂男女授受不親嗎?」
「青蘿是我的妻,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黃大哥漫不經心地勾起一抹笑:
「要說這不知廉恥,狀元郎比在下當然更甚一籌,陸姑娘清清白白一個人,怎麽就成了你的妻?」
「婚假六禮,狀元郎做了哪一條?」
「哦,對了,在下聽說你將陛下賞賜均贈與陸姑娘,算是做了六禮其一,可在下又聽說,你那明媒正娶的妾室,早已將賞賜追回,狀元郎,不會還不知道吧?」
謝淮安眉頭緊緊皺著,嘴角抽搐,顯然對黃大哥所言並不知情。
可黃大哥對這些事,為何如此清楚?
黃大哥倏然從懷裏掏出兩根沈甸甸的金條,塞進我手中:
「陸姑娘,我知道此事有些唐突,但在下已經等不及了,你即已拒絕狀元郎,這次,能不能接納我了?」
他說完,默默伸出手掌,等我回應。
黃大哥長得極好,有文人的睿智,也有武將的風姿。
視線落在他俊朗赤誠的臉上,竟有些移不開眼。
我猜黃大哥是為了幫我脫困,擺脫謝淮安才會說這些話。
可如此輕易接受他的好意,豈不是又讓他聲名受損?
我猶豫不決間,謝淮安焦急喝道:
「青蘿,人生大事,不可兒戲!」
「你如何認識此人,我為何不知?他人品心性如何,你又了解多少?」
「所嫁非良人,你將會抱憾終生,青蘿,你為我付出良多,我知你懂你,日後定會好好報答你,我才是你的良配啊。」
他臉上的憤怒之色消散,竟如從前那般溫柔看向我,緩緩向我伸出手。
可我絕不會再選擇他。
為了盡快了解這段孽緣,我擡手搭在了黃大哥手上。
黃大哥緊緊握住我的手,喜笑顏開:
「陸姑娘答應在下,可就不能反悔了!」
「離開那個負心漢,你的福氣在後頭。」
他眼中的光亮的嚇人。
我瑟縮地想抽回手。
他卻一把將我擁進懷中:
「說好了,不準反悔,我們明日便大婚!」
「荒謬!你可知籌備婚禮需要多少時日?」
「狀元郎又怎知,婚禮是我臨時起意?」
謝淮安氣得甩袖,直接掠過他看向我:
「青蘿,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離開他,跟我走。」
這次我沒有猶豫,直接牽上黃大哥的手,走到謝淮安面前。
「黃大哥,可否借你一樣東西,我實在沒力氣了。」
「青蘿就是要天邊明月,為夫也定想辦法給你摘下來!」
我虛弱地笑了笑:
「用不著那麽麻煩,借你的手,扇他一巴掌,黃大哥敢不敢?」
黃大哥猛然低頭,皺眉看著我:
「他打你了?」
我盯著謝淮安,沈默地點點頭。
謝淮安嘴唇動了動,剛要開口,就被黃大哥一巴掌打偏過臉。
謝淮安胸口劇烈起伏,他齜牙抹了一把唇角,手掌沾滿了血。
「粗鄙……」
「小人」二字還未喊出,黃大哥又甩他一巴掌。
這一巴掌直接把謝淮安扇趴在地上。
黃大哥活動手腕,輕蔑冷笑:
「抱歉,我這粗鄙小人就喜歡用拳頭解決問題,立竿見影。」
「這第二巴掌,是教你長長記性,日後再讓我瞧見你對她有半分不敬,可就不是這麽簡單了事。」
看到謝淮安趴在地上爬不起來,我忍不住「噗嗤」笑出聲。
「黃大哥才不是粗鄙小人,黃大哥能文能武,是青蘿的大英雄。」
黃大哥當著謝淮安的面再次將我輕松抱起:
「走,大英雄帶青蘿歸家咯。」
謝淮安何曾受過這般羞辱,直氣得猛捶地面,嘶聲低吼。
我們走出大門口時,雲茉婉正提著裙擺,從門柱沖過來。
當她看到我們時,不知為什麽,忽的止住腳步,臉上俱是驚恐之色。
我恨她恨得要命,可此時已是身心俱疲,隨時都要暈過去。
黃大哥溫熱的手緊了緊,輕聲道:
「有夫君在,什麽都不用擔心,好好睡一覺,明日才有力氣拜堂成親。」
我淺淺笑了笑,直覺脖頸被人用力按了一瞬,意識越來越沈。
腦海中忽然湧入與黃大哥初見的場景。
那是半年前,我為了省下幾文錢推著板車去鄉裏購買黃豆。
卻在半路遇到重傷倒地,奄奄一息的黃大哥。
我又急又怕,不敢碰他,他卻勾起一抹笑,調笑道:
「我大抵是要死了,要不然怎麽看到了下凡的小仙女。」
「初來貴寶地,就被山中野獸襲擊,實在是……」
他話沒說完就暈了過去。
我看他衣著華貴,不像落魄之人。
荒郊野外沒有人可以求救,放任他不管,怕是真要被野獸拖進山裏吃掉。
我又拖又拽,用了全部力氣才把他拖上板車,拉回去。
用他身上的銀錢幫他租了客棧,請來大夫。
大夫看在金元寶的份上,寸步不離的守了他三天。
這才給他續上命。
不過大夫說,他身上的傷,並不是野獸所為,是刀劍所傷。
或許是哪家富貴公子闖蕩江湖遇到了山匪。
我救了他的命,他醒來卻潑皮耍賴,說我輕薄了他,讓我對他負責,照顧他傷勢痊愈。
我甚是無語,我要磨豆腐賣豆腐攢銀子給謝淮安讀書趕考,哪有時間在他身上浪費。
沒有搭理他,交代店小二按時給他送飯送水請大夫復診後,我就偷偷溜走。
沒想到他竟然拖著病體找到了我的豆腐鋪。
我妥協放棄,為了不讓別人說閑話,他給我當起小工,只能幫我收錢算賬。
而我對他的了解,也只限於他姓「黃「
我還為此給京城讀書的謝淮安寫通道明此事。
他說他不知黃大哥這人,大概是沒仔細看我的信吧。
後來,他扔給我一錠金子,要買下我的豆腐鋪。
還揚言要娶我為妻。
讓我用燒火棍暴揍一頓。
等他傷好痊愈,竟然將我的手藝偷偷全部學走。
一個人包攬了全部的活,我完全插不上手。
可能是玩膩了,忽然有一天,他不辭而別。
沒想到,他竟然在我抱著必死的決心之時,從天而降,救我一命。
意識越來越沈,身子如此困倦虛弱,明日如何大婚?
我好像做了很久很久的夢,夢到顛沛流離,刀光劍雨,廝殺聲震天。
時而有甘汁蜜露滑過口舌。
等我再次醒來,入目的竟是華麗無比的床帳帷幔。
視線向下,一個打扮精致的稚嫩臉龐赫然出現。
與我對視時,她水靈圓潤的眼睛猛然睜大,難掩喜悅。
慌忙放下手中白玉碗,提著裙擺往外跑。
邊跑邊喊:
「太子妃醒了,快,通知太子,太子妃醒了!」
「太,太子妃?」
我緩緩坐起,揉揉腦袋,我這是睡了多久,能做出這般離譜的夢來。
可下一刻,一身華服的黃大哥撩起衣擺,大跨步走了進來。
屋內的美人們紛紛跪下,喚他「太子」。
他只擡手匆匆揮退眾人,急匆匆跑到床前,緊緊握住我的手。
眼中滿是關切與激動:
「青蘿,你終於醒了!這幾日可擔心死我了。」
我驚愕地望著眼前的黃大哥:
「我睡了幾日?」
「三日有余。」
竟這麽多日,那……
我心頭滑過一瞬失落。
「黃大哥,她們,喚你‘太子’?」
黃大哥深邃淩厲的雙眼閃過一絲心虛,撇撇嘴,單膝跪在我面前,討饒道:
「青蘿,孤知你心性,若孤一早告知你真實身份,你斷然不會同意與孤成親。」
我並沒有責怪他的一絲,被他這一舉動嚇了一跳,急忙伸手去扶。
結果牽動全身,眼前一黑,一陣天旋地轉,直直往前倒去。
黃大哥急忙伸手將我攬進懷中,調笑道:
「青蘿這般迫不及待投懷送抱,就是原諒為夫了,對不對?」
這人嚴肅起來能一腳踢死人,可耍起賴來,任誰也拿他沒辦法。
我本就知曉他身份貴重,卻不曾想會貴重如此。
短暫震驚後,我也恢復了理智,推開他,抽回手。
「黃大哥貴為太子,豈是我們平民百姓可攀附的,以後還請太子殿下慎言慎行,別再與民女纏結不清。」
當朝皇家姓「李」,此「黃」實為「皇」。
當朝太子李禹。
太子殿下眉心微蹙,表情有一瞬受傷。
他不顧我的反對,復又牽住我的手,委屈巴巴道:
「三日前的婚禮被賊人破壞,本太子險些喪了命,你這般拒絕,還不如我死在賊人手裏。」
我急忙捂住他的嘴,急得口無遮攔:
「再胡說,打爛你的嘴!」
嚇得屋內婢女「噗通」跪了一地。
我急忙又捂住自己的嘴,小聲問:
「到底怎麽回事?」
原來那天太子確實舉辦了大婚,只是他不想我太累,點了我的穴道,一直處於休眠狀態。
途中,最初刺殺太子的那波狂徒再次對他出手。
而這次,太子是有備而來,擡花轎的,敲鑼打鼓吹喇叭的都是武藝高強的侍衛裝扮。
很快就將那夥賊人絞殺。
最後留了一個活口,逼問出了幕後主使二皇子。
而二皇子最信任的幕僚則是謝淮安的恩師,雲茉婉的親生父親:雲青楓。
年初太子遭刺殺,就懷疑是雲青楓所為。
可苦於沒有證據,只查到他貪受賄賂之罪,下了大獄。
沒想到謝淮安這個楞頭青贖出了雲茉婉。
得知謝淮安與我訂親,太子本已經放棄,備好大禮,準備大婚之日送到謝府。
誰知當日成親的竟是雲茉婉。
侍衛回宮回稟太子後,他心情復雜,深知謝淮安此行對我的傷害非同小可。
可他那幾日被陛下要求在身邊侍奉,抽不開身。
等他千裏迢迢趕到我家,已經物是人非。
最後在他的逼問下,謝家婆子才告訴他我已經被賣去青樓。
而雲茉婉也在那晚認出來太子殿下。
才繼承她爹的使命,在第二日發起刺殺行動。
這次人贓並獲,證據確鑿。
省上大怒,二皇子被軟禁,雲家被誅九族,秋後問斬。
很不幸,謝淮安上趕著給恩師當乘龍快婿,也在九族之列。
「我自己的命都無所謂,我就怕去晚了,你就……」
說著說著,他的聲音竟染上哭腔:
「如今本太子昭告天下迎娶青蘿為太子妃,你若不要我,就是讓孤被天下人恥笑!」
「你就這麽狠心,看著我被他們笑話嗎?」
「我,我……」
我被他噎的,竟一時失了語。
太子猛地站起,笑意盎然,大聲道:
「你不反駁,就是答應孤了,快,大婚在即,為太子妃更衣!」
一群小婢女手持托盤,有序從門外進入。
將耀眼奪目的鳳冠霞帔擺在我眼前,齊聲道:
「請太子妃,更嫁衣……」
那日,我莫名其妙成了太子妃,承受了此生最重的發冠。
婚後,太子怕我寂寞,在東宮辟了一方土地,為我建了一間豆腐鋪。
我時常親手磨出鮮嫩可口的豆腐,或做成糕點,給宮中各位娘娘送去品嘗。
後來,謝淮安請求我去獄中相見。
我沒去,他無非是想讓我替他求情,繞他一命罷了。
既然當初做了選擇,就該承擔選擇的後果。
我怎會為了一個忘恩負義之徒,傷了太子夫君的心。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