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侵即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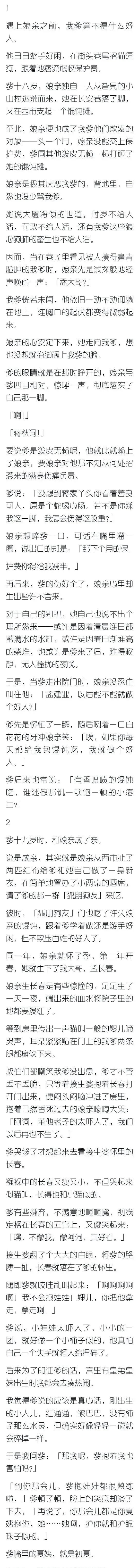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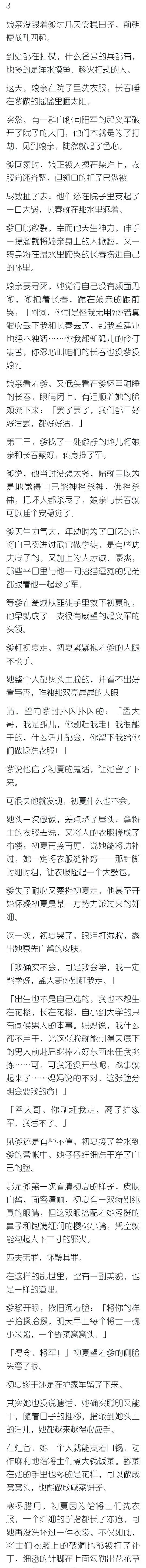
4
護家軍的人都喜歡極了初夏。
曾經和爹一起問小攤販收保護費的那些叔伯雖然從爹那裏知道了初夏的底細,也並沒有瞧初夏不起。
恰恰相反,他們都憐惜初夏。
有一天,有個叔伯忸怩著向初夏開了口:「初夏妹子,我,我中意你。」
不等初夏說什麽,那個叔伯又搶白道:「初夏妹子,你,我,你不用急著回答我,也不用有負擔,你,你等我跟著孟大哥建功立業了再……」
叔伯的臉一直紅到脖子根,在初夏的註視下,他的聲音也越來越小。
可是初夏說:「張強大哥,對不起,我不喜歡你,我有喜歡的人了。」
是了,初夏已經有了喜歡的人,明眼人都知道——初夏喜歡我爹。
張強不解:「可孟大哥已經娶了媳婦了。」
一向好脾氣的初夏卻突然發了狠:「娶媳婦又如何?就算給孟大哥做妾我也喜歡,我絞了頭發做姑子去也不喜歡你。」
實則初夏那會兒是不信,盡管一直有傳言爹已有妻兒,抓了爹的妻兒就是捏住了護家軍的命脈;盡管爹隔幾個月總有一段時日不在軍中,軍裏的叔伯都說爹是回鄉看望妻兒去了。
可也有人說爹是孤身一人,畢竟重金懸賞多年,也沒人見過爹的妻兒。
初夏只以為叔伯們說的話,是經了爹的授意,好叫她知難而退,不要再纏結他。
現下張強再次提起,初夏便也氣狠了,口無遮攔起來。
很多年以後,初夏將我摟在懷裏說她這輩子誰都對得起,唯一對不起的,大抵就是我張強叔。
又過了一年有余,戰事吃緊,局勢也到了最緊要的關頭。
爹同初夏說,他打算帶她回家。
初夏不知想到了什麽,漂亮的眼睛璀璨而明亮。
她在眾目睽睽之下,撇了鍋鏟,飛身到爹的面前:「孟大哥,你是要帶我回你的家嗎?你現在也覺得我很能幹吧,你放心我一定把我們的家打理得僅僅有條!」
少女清脆的聲音藏不住溢位來的歡喜,爹卻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有過心動嗎?
爹從來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
他們長途跋涉,在一座山又一座山的後頭,找到那個僻靜的小院,隔著院墻男童與娘親的歡聲笑語跑了出來。
然後爹推開門,與院裏奔跑著的男童撞了個滿懷:「爹?」
男童復又使勁揉了揉眼睛,分外驚喜地對身後喊道:「娘,真是我爹!我爹回來了!」
初夏臉上的血色在頃刻間褪盡,她不禁小聲囁嚅:「孟大哥……你原來真的已有妻室啊。」
可當娘親看過來時,她的視線落在娘親滾圓的肚子上,默不作聲拉開了與爹的距離。
初夏笑著沖娘親揮手:「嫂子,我叫孟初夏,你以後叫我初夏就行。」
初夏是那樣對娘親說的,她原先是沒有名字的,花樓裏的姑娘們要麽叫她「餵」,要麽喊她「小不點」。
長到八歲時,她的模樣逐漸清麗起來,彼時正值初夏,花樓的媽媽在蟬鳴聲中欣喜於她的變化,給她起了「初夏」這個名字。
「後來,我被孟大哥救了,我想我無親無故,就給孟大哥當個妹子吧,就給自己取了和孟大哥一樣的姓。從今以後,孟大哥就是我親大哥,嫂子你就是我親嫂子。」
娘親欲言又止,心頭微微松快了一些,又對眼前模樣周正的小姑娘生出幾分憐惜,她將初夏的手攏在自己的手心,眼淚漣漣:「唉,以後咱們就是一家人。」
5
有初夏在身邊,娘親的孕期也沒那麽辛苦了。
初夏很貼心,有活兒總會搶著幹,她也有才情,能夠在土地上拿木棍比劃著教長春認字學詩。
娘親半夜腿抽筋,初夏睡得再迷糊,都會起來給娘親揉腿;娘親做了噩夢驚醒,也是初夏一下又一下拍著娘親的背柔聲安撫:「嫂子,你是沒見過孟大哥打仗,厲害著呢,他不會有事的。」
有時候,哄著娘親時,初夏迷迷瞪瞪的卻兀自笑起來,她問娘親:「嫂子,你說我這樣盡心盡力地照顧你和長春,萬一,萬一孟大哥真能坐上那個位子……他是不是得封我一個公主當當?」
娘親也睡迷糊了,張嘴就來:「你怎麽這麽不貪心,我們初夏這麽好,封十個公主當都當得。」
長春鉆到娘親和初夏的中間,表情懵懂卻積極:「那長春呢,娘親,長春能當幾個公主?」
避世的山坳是爹精心為娘親和長春尋找的桃花源,因而不管山外的戰爭打得有多焦灼,娘親三人的生活一直都很安靜祥和。
有時候娘親也會同初夏說,她想爹了。
娘親的眼睛紅紅的,初夏的眼睛也變得紅紅的,她說,她也有點想孟大哥了。
捱到這年冬天,娘親終於生下我,生我時,爹都不知道。
娘親生我時也不順利,而初夏才年過十六,哪裏懂接生的事情?
她手忙腳亂地一個勁擦著娘親身下淌出的鮮血,見娘親的面色逐漸灰敗下來,就說些渾話來故意氣她:「蔣秋詞,你知曉我喜歡孟大哥吧?你若是,若是就這樣走了,我不但要爬孟大哥的床,還要虐待你的長春,我,我不給他新衣服穿!」
十六歲的孟初夏能想出的最惡毒的折磨娘親孩子的法子就是不給他新衣服穿。
可娘親確是聽了初夏的話,來了力氣,將我生了下來。
娘親看著初夏通紅的眼睛,眼淚從她的眼角滑落,她說:「初夏,你是個好孩子……兩個孩子以後就麻煩你照顧了。」
初夏想拒絕,她想告訴娘親沒有人能比親娘更愛自己的孩子,就連她那做妓女的老子娘當初拼死生下她時都想為她尋個好出路。
可惜她的娘死得早,所以她成了花樓裏的一棵賤草,原先長大了還要女承母業,也做個賣肉的。
要是娘親去了,那我和長春也要變成草。
可看著娘親逐漸失焦的眼睛,初夏的眼淚成串成串地掉,她說:「行,我疼他們就像疼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可是嫂子,你能不能,能不能再撐一撐?」
娘親卻嘴角微彎,生命最後,她說她好像看見了我爹。
小院裏沒了娘親,院外的竹林裏卻多出一個墳包。
五歲的長春還不太能夠理解一個人死了意味著什麽,他只記得初夏將睡著的娘親埋進了那個土坑裏,於是每天都問:「夏姨,娘親是在地底睡覺嗎?」
「是因為長春不乖,所以娘親才要躲去地底睡嗎?」
「夏姨,娘親什麽時候才願意從地底出來,長春想娘親了。」
每到這時候,初夏就會掉眼淚,她騙長春說:「你娘親這一年太辛苦了,所以要在地底下休息很久很久才行,興許要等到長春長大呢。」
久而久之,長春就不問了,他不想每天都讓初夏難過。
6
我長到一歲半時,爹打進京城做了皇帝。
他帶領著許多許多人翻山越嶺來到小院時,終於知曉娘親沒了。
爹追封娘親為皇後,又下了兩份詔書,一份封初夏為護國長公主,一份封長春為太子。
至於我,他看也不看,甚至連個乳名都吝嗇賞賜給我。
我們都跟著爹回了京城,爹挑了最大最華麗的宮殿給初夏做寢宮,殿名就叫歸夏宮。
他說他這輩子註定要辜負兩個人,一個是我娘親,另一個就是初夏。
他與初夏相識於微末,曾與兄妹相稱,他知初夏想要什麽,可物是人非,終究給不了初夏想要的,只好從其他地方補償她。
初夏卻甩了爹一巴掌,她說,她早就不喜歡爹了,可爹著實不應該:「奶團子是嫂子拼死也要生下來的娃娃,你這當爹的,沒照看過一天,怎還有臉面對她心生怨懟和憎恨?」
爹的視線終於落到我的臉上,又很快逃也似的移到別處,他有些生硬道:「那就叫念秋吧。」
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名字,可初夏還是喜歡叫我「奶團子」。
其實比起爹同我們,初夏同我與長春才更像一家人。
爹對長春是很嚴苛的,月亮還高高懸於頭頂,長春就要去晨練了,餓著肚子練到日上三竿他才能吃口熱乎飯,可很快又要去讀書,背不出夫子要求背的文章,就要挨板子。
長春起先還會掉眼淚,後來只敢在晚上的時候窩在初夏的懷裏哭,他還像特別小的時候,對著初夏撒嬌:「夏姨,夫子打得我手疼。」
初夏就捧著長春的手呼氣,她說:「沒事沒事,夏姨吹吹就不疼了。」
後來初夏不在了,每逢我摔角還是磕碰了哭鼻子,長春便也這樣對我:「沒事沒事,大哥吹吹就不疼了。」
和初夏相處過的人,最後或多或少,都有了她的影子。
7
可惜皇上不好當。
前朝官商勾結,貪墨成風,整個國家都爛透了。
外戰內戰又都打了這麽多年,如今雖然塵埃落定,可有的是天災人禍——南方蝗災,北方幹旱,餓死的人太多了,瘟疫也爆發了出來。
這年的爹也快二十七了,不算年輕,也說不上老,竟被愁出一頭白發。
這時,北疆的信使帶著他們的公主與整車的草藥和糧食來和親,他們說他們帶著誠意而來,可張嘴分明想要咬去孟夏的一塊肉——他們的公主要成為新的皇後,爹還要割讓十二座城池作為求娶公主的聘禮,同時,為結秦晉之好,也替他們的可汗求娶孟夏的公主。
爹的女兒只有一個牙牙學語的我,可公主卻有兩個,他們求娶的不是初夏還能是誰呢?
暴怒之下,爹手中的杯盞砸破了信使的額頭:「爾敢?」
群情激憤,大殿裏站著的多是當年在軍營裏同爹出生入死的弟兄,他們也都認識初夏,吃過她煮的大鍋飯,,懷裏揣過她烙的鹹菜餅,還穿過她或漿洗或縫補的衣裳。
叔伯們怒目圓睜,也不知道是誰起的頭:「我們護家軍不是孬種,護不住初夏,那就繼續打!」
「就是,陛下,這個條件我們不能應!臣等願率軍北伐,不破北疆,誓死不回!」
「不破北疆,誓死不回!」
初夏的好,叔伯們都記得,心裏都有數。
細皮嫩肉的小姑娘隨軍遠征時甚至還沒及笄,她不會的何止做飯洗衣,可最後為了他們學會的卻遠不止做飯洗衣。
打仗嘛,受傷是常有的事兒,初夏起初被嚇得老失眠,也不知道她從哪裏搜羅來幾本關於藥理的醫書,失眠的時候便抱著醫術啃,手裏頭還納著鞋底。
漸漸地,她就認識了很多草藥,給傷員包紮,救治傷員便也成了她的活兒。
初夏還讀過書,寫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那些年,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又有誰沒排過隊,叫初夏幫忙寫過報平安的家信呢?
可面對叔伯們的憤慨,信使站在大殿中間巍然不動,甚至他的臉上還能浮現出幾分輕蔑的笑意。他直視爹的眼睛,悠然開口:「陛下,你們,果真還打得動嗎?」
「陛下,您是一國之君,切莫感情用事……以一個公主換元和一個修養生息的機會,再值得不過。」
是了,這時候的孟夏還不叫孟夏,叫元和。
萬籟俱寂,所有人都知曉,北疆的求和無異於飲鴆止渴;可所有人也都知道,北疆的信使說的沒錯。
緊接著,眾目睽睽下,初夏緩步走到殿前,她註視爹良久,隨後深深跪拜下去,清脆的聲音響徹了整個大殿:「陛下,臣女孟初夏自請前往北疆和親。」
爹顫抖著聲問:「你可知那北疆的可汗如今多大了?八十有二,別說能當你爹了,當我爹都綽綽有余了!」
北疆的信使說:「還望陛下慎言。」
爹本就是個大老粗,當下又暴怒得跳腳,哪還有余力去顧及面子上的事。
初夏對信使的話也充耳不聞,只回答爹的話:「原不知曉,現下知曉了。」
「你可知那老可汗死了的妃子兩只手都數不過來,女子在那裏算不得
人,父子同享一個妃子也是有的?」
北疆信使又說:「還望陛下慎言。」
初夏在他後復又說:「原不知曉,現下知曉了。」
爹問初夏悔不悔。
少女的眼睛似這世間最美的琉璃,她笑彎了眼,好似心中盡是暢快:「陛下,臣女的娘生下臣女時定沒想過臣女還能麻雀變鳳凰,臣女享得起公主的福,便也擔得起這公主的責,況且……臣女也覺得,以臣女一人換元和一個修養生息的機會,這筆買賣劃算極了。」
大殿裏響起窸窸的抽噎聲,大老爺們全都紅了眼——初夏是個好姑娘,她頂了護國長公主的名頭,可何曾享過一天做公主的福氣呢?
8
爹私底下又找到初夏,他雙目赤紅,說自己後悔了:「我應該同樣也冊封你為我的皇後。」
爹對初夏到底是不同的,他從不在她面前自稱為「朕」。
初夏不曉得自己眼裏的依戀有多明顯,還自以為掩飾得毫無破綻,對著爹冷哼:「我與嫂子有那樣的情分,早就瞧不上孟大哥你身邊女人的位置。」
她又對著爹絮叨起來,長春與我都是娘親的寶貝,也是她初夏的寶貝,爹萬不可叫旁人欺負了我們去。縱使來日爹有了別的女人,生了其他的孩子,也要待長春與我最與眾不同。
「沒有娘親已然是這世上最可憐的事了,孟大哥,以後唯你一人是他們的依靠了。」
她最放心不下的還是我,再三叮囑:「嫂子不怪奶團子,孟大哥你也不許怪她,說到底是你這個做丈夫的不稱職。你若是……若是對奶團子不好,我哪怕在天邊也殺到你面前來!」
後來,夜色寂寥,初夏終於卸下偽裝,她哽咽著說:「孟大哥,要不,你抱抱我吧。」
初夏和親這日,我抱著她的腿不肯松手。
宮女們顧不上別的,齊齊來掰我的手指,只有初夏擔心我會不會疼。
她厲聲喝止住她們,低頭的時候,蓋頭下的眼睛恰好能對上我的眼。
我連話都還不能說利索:「夏姨,你能不能別走?」
初夏卻說:「奶團子聽話,以後要少哭鼻子,平安長大。」
我又求她:「夏姨你能不能帶著我一起走,我不要和你分開,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奶團子的家。」
初夏笑著說:「小傻子,你說的什麽渾話?」
可是她的淚卻落到了我的嘴裏,好苦好苦。
最後,是兄長拉開了我,她說初夏有自己的事要做,所以不能帶上我。
我們爬上了高高的城墻,目光所及,滿城的百姓夾道相送。
我不敢再哭,怕眼淚模糊了眼,看不清初夏遠行的車輦。
可惜,隨著和親的隊伍越行越遠,即便我爬上了最高的觀星台,還是弄丟了初夏的身影。
9
初夏不知道的是護送自己北上和親的隊伍裏也有張強。
她與張強也有好些年沒見了,四目相對的一刻,看著張強飽經風霜的臉,初夏差點兒沒敢認。
「張大哥?」
張強的眼裏有淚花,他哽咽地應了一聲,擡手拭淚時,初夏註意到他長出來的那節袖子打著動物形狀的修補程式。
翌日就要跨出孟夏的地界抵達北疆了,隨行的隊伍有誰舍得呢?
初夏與張強一起坐在帳前的大樹下,張強與初夏訴說自己這些年的過往。
當年被初夏拒絕後,張強失眠了一整夜。
他並不怪初夏——初夏這樣好的姑娘,合該配這世間頂頂好的男子。
可他怕初夏會後悔,怕她求而不得卻尋不到別的棲身之所,張強想,那自己就努力成為初夏的那條後路吧。
他愈發刻苦,卻不貪功冒進,漸漸也開始在軍裏嶄露頭角。
他一直在等一個機會,想和初夏說:初夏妹子,你盡管大膽往前走,我會一直在你身後。
沒曾想再見是這樣的光景,他要護送著自己心愛的姑娘步入深淵。
望著初夏妝容精致的臉,張強突然一把抓過初夏的手腕,迎上初夏澄澈的眼睛,張強說:「初夏妹子我帶你走吧。」
初夏的眼裏也含著淚,她比許多年前還要刁鉆、刻薄,說出口的話一點兒都不好聽:「張強,我之前不喜歡你,如今也不喜歡,以後更不會喜歡你。」
「戲子無情,婊子無義。我們做妓子的,就喜歡一個勁兒往上爬,做那人上人。」
為什麽總是對張強這般刻薄無禮呢?
初夏自己也不明白。
大抵是被愛的有恃無恐,她也知道,不管她如何,張強都舍不得與她計較。
初夏到了北疆,送親的隊伍回來了,但是張強沒有。
他讓人帶話給爹,說自己戎馬半生,以後想為自己活一次。他不敢賭,不敢將初夏獨自一人留在那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
爹問:「他作為我們元和的將軍,北疆如何會留下他?」
侍從戰戰兢兢:「張將軍,張將軍自個兒,自個兒凈了身子……」
我的張強叔呀,叔伯們後來說起他時,總是誇耀他剛強、堅毅。
可這年,他卻為了初夏甘願淪落為一名內侍,充入初夏的陪嫁裏。
10
初夏走後,便成了爹帶我。
他一改之前對我的冷漠,連批奏折時都將我抱在懷裏。
爹說我長得很像娘,但大抵誰帶的久就像誰,他有時候也會說我像初夏。
疲憊極了的時候,他就會盯著我看良久,好像要透過我看誰似的。
爹也越來越像個皇帝了,除了我與長春以外的人都開始害怕他。
養心殿裏,燈火明亮,爹批閱奏章的手始終沒有停。我打著哈欠說:「爹,時間不早了,該歇息了。」
爹卻說:「念秋先睡,爹還早呢。」
初夏剛走的那段日子其實我老哭,現下想到再沒有初夏哄我睡覺,我又難過起來。
我問爹:「爹,你什麽時候能去接夏姨回來,她已經走了一百四十五天,我想她了。」
爹握著筆桿子的手突然不動了,他的聲音分明哽咽:「很快,爹很快就接了你夏姨和張強叔回來。」
其實我是不大認識張強叔的,我只在意初夏什麽時候回。
可爹說很快會接初夏回來,我就知道爹又再搪塞我,過去那一百四十五天他都說很快會接初夏回來,我起初信的時候,開心地逢人便說,我夏姨就要回來了。
我有很多話想和初夏說,拾掇著自己的寶貝打算等初夏回來都送給她。
爹說的多了,我就不信了。
但他們說,爹是天子,金口玉言,爹是不會騙人的。
業連是女人度是時間的長短與孩童是不一樣的所以爹嘴裏說的「很快」和我以為的「很快」也不一樣嗎?
我有些埋怨地看了爹一眼,兀自結束了養心殿。
11
皇宮裏的妃子越來越多,孩子也越來越來多。
好像什麽都在變,又好像什麽都沒變——爹從不曾去抱抱我的皇弟皇妹們,他們也總是畢恭畢敬地喊爹「父皇」,唯我和長春一如既往地喊「爹」。
但是有個人一直沒有孩子,她就是住在延春宮裏的皇後,當年那個北疆送過來的公主。
她被送來和親的時候,其實年紀也不大,好似也才剛及笄,到如今也有二十三了。
我想,她這輩子都不會有孩子,不只是因為她是北疆人,爹從不曾到她的延春宮留宿過。
我本來也是很討厭她的,我恨她換走了我的初夏。
因而,仗著爹的寵愛時常去她宮裏搗亂。
諸如不小心燒了她的衣裳,尋找小貓的時候,不小心撞碎她的琉璃盞。
北疆公主有一雙似乎能夠洞察一切的眼睛,可她總是眼神溫和地看著我
鬧騰,還攔住她氣得跳腳的宮女,不讓人家向爹告狀。
直到有一天,我從她手裏奪過一方繡帕,北疆公主的臉上終於有了別的情緒。
我說這方繡帕正合我意,我要把它拿回去給我的小貓做圍兜。
北疆公主向我撲來,她直接將我摁在了地上,惡狠狠地將繡帕從我手裏奪了回去。
我就知曉北疆人沒一個是好的,這北疆公主裝了這麽久的溫柔和善,如今還不是露出了狐貍尾巴?
可緊接著她就將我從地上拽了起來,聲音冷淡:「你想怎麽折騰都行,唯獨這方繡帕我不能給你……它是我母妃留給我的唯一一件東西了。」
我突然就不那麽想欺負她了。
「皇後娘娘你想家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她。
北疆公主瞥我一眼,隨後搖搖頭。
她告訴我,她的可汗和兄弟姐妹都對她不好,唯一對她好的母妃還被可敦尋了由頭給殺了。
「在我們北疆,哪裏有什麽手足之情,可汗待他的孩子就似養蠱,勝者為王。」
我聽她說得兇險,又開始擔心起初夏來,連著好幾晚都沒能睡好覺,人也跟著瘦了一大圈。
自這時起,我便不再同北疆公主為難,還時常會去延春宮坐坐,陪她說會兒話。
有一天,她突然對我說:「念秋公主,謝謝你。」
我想了想,還是如實說:「我不是為你,我只為了我夏姨。我希望你們北疆人也有人能如同我對你這般,給夏姨幾分善意。」
可惜這時的我看不懂北疆公主眼底的憐憫和她的欲言又止。
12
又過了三年,孟夏總算熬出了頭,兵馬強壯,國力強盛,百姓安居樂業,在外征戰的將士戰無不勝。
爹總算要兌現他「很快」的諾言,叫人帶著談判的信去接初夏和張強叔回來。
我們都在翹首以盼,就連從未見過初夏的皇弟皇妹們也熱切地期盼著。
可信使回來了,身後卻空無一人。
他將臉緊緊貼在地面上,不敢對上爹充滿威嚴的眼睛:「護國長公主和張將軍早……早在五年前就故去了……」
爹的眼睛在瞬間失了焦距,隨後,他猛然噴出一大口血來。
信使說,北疆瞧不上當時的孟夏,因此也瞧不上我們送去和親的公主。初夏乍一到那裏,就受了老可汗非人的虐待。
他已然老得做不了那檔子事兒了,可折磨人的手段卻層出不窮。新婚之夜,誰也不知道他對初夏做了什麽,只第二日眾人瞧見的就是初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樣子。
初夏被折騰得一個月才能下床,可也總是新傷添舊傷,身上沒一塊好肉。
北疆的妃子和皇子公主們也瞧不上初夏,對她肆意羞辱欺淩,逼著初夏鉆褲襠、學狗叫、叫初夏頂著蘋果跑,然後追在她身後放冷箭。
起初還好,鄭強總是幫她周旋,那些受盡屈辱的事情,他都搶著替初夏捱。
可很快,他們就發現了鄭強對初夏隱秘的心思。
於是逼著初夏在大庭廣眾之下與鄭強調情,要鄭強用嘴去解開初夏胸口的系帶,去舔舐初夏裸露在外的肌膚和高聳。
鄭強哪裏會願意呢?
所以他扭頭咬住了離自己最近的皇子的脖子,鮮血四濺,皇子死了,鄭強也死了——這一年,僅是初夏北上的第三年。
信使說:「護國長公主尚因公主的身份還能有一副棺槨,可,可鄭將軍,是被丟進了獵獸場,據說,據說連塊骨頭都沒剩。」
沒有人說話,所有人的眼裏都含著淚與恨。
「殺!」不知道是誰起的頭。
隨後,大殿裏響起了一聲緊接著一聲的「殺」。
「殺!」
「殺!」
「殺!」
這天之後,元和就不叫元和了,爹改了國號,這一年也就成了孟夏一年。
孟夏,夢夏。
第二日,爹不顧群臣的極力反對,再次披甲上陣,一同前去的有已經十九歲的長春,有昔日裏與爹一塊上過戰場的叔伯,有的叔伯也已經不在了,但是他們的兒子接替了他們的位置。
長春在我面前落下大顆眼淚,眼裏有望不到底的兇狠:「奶團子,大哥去將夏姨帶回來。
他們出發那日,北風呼號。
十二年前,送初夏去和親,滿城的百姓跪拜相送。
十二年後,孟夏北伐,百姓同樣擠滿了街道,這一次他們站著,吶喊著:「殺!殺!殺!」
我高站於城墻,望向遙遠的北方:夏姨,你瞧見了嗎?
13
捷報頻傳,據說,護家軍勢如破竹,長驅直入攻到北疆的皇城。
兵臨城下時,北疆新繼位的可汗想要與爹談條件求和。
他說,他們願意歸還孟夏的十二座城池;還願意成為孟夏的附屬國,每年都給孟夏提供大量優質強健的馬匹和許多許多的美人。
爹眼睛眨也沒眨,只吐了一個字:「殺!」
那一日,護家軍各個都殺紅了眼,殺到北疆的皇城血流成河,連空氣裏都是黏稠的血腥味兒。
長春的刀架在年輕可汗的脖頸處,驀地,突然笑了:「你們不配死得這麽輕易。」
長春說,他們要嘗盡初夏所受的苦,要比初夏千倍萬倍還痛苦才算贖罪。
就連老可汗也被爹帶著人從墳裏挖了出來挫骨揚灰。
可我的初夏,我們的初夏,這世間第一好的初夏,終究是再也回不來了。
14
北疆成了孟夏的一部份國土。
爹他們從北疆回京這日,滿城縞素。
百姓們都在為初夏哭,若不是初夏,他們定還要同家人分別,要顛沛流離,要吃盡這世道望不到頭的苦。
更何況,初夏和親時,本是要從民間挑選二十名陪侍的少女的。
可初夏說:「她們都是好人家的女兒,何苦要讓她們一起去受那無妄的磋磨?總歸我也不是正經公主,自也不必真按公主的規格來。」
這十二年真漫長,所幸沒有人忘記初夏。
而這一天,北疆公主也死了。
我本還在思忖爹會如何發落她,畢竟她也是個可憐人,雖然她換走了初夏,可是她同初夏一樣,從來都身不由己。
可她自己就那樣孤零零地死了,用一根白綾將自己吊死在了延春宮。
15
爹從北疆回來後,好似一下子被抽走了所有精氣神。
他不大料理國事了,好在長春很能幹,也很聰慧,甚至於很多事情處理得比爹還要好。
而爹尤其喜歡往歸夏宮跑,但他大抵是有些失望的——歸夏宮裏早沒了初夏,只有一日日成長起來的念秋。
後來突然有一天,爹一覺醒來,就誰也不記得了。
他不記得自己那些當年迫於局勢納的妃子,不記得我的皇弟皇妹們,甚至於連我和長春也不記得了。
但他仍舊愛往歸夏宮跑,見到我時,眼裏有藏不住的喜悅:「阿詞,我就知道你在這裏。」
是了,爹連初夏也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娘親,有一次對我說漏嘴,他說:「阿詞,其實從見你第一面起,你就落我心裏了。可我是個混人,連做好事都不會,前些日子打砸了你的餛飩攤,我難受得同兄弟們打了一架,我心想,呀,完了,你大抵這輩子都不會拿正眼瞧我了。」
過了幾天,他又追在我屁股後頭撒嬌:「阿詞,你怎麽近來都不出攤了,我想吃你包的餛飩了。」
會包餛飩的娘親都走了那麽多年了,皇宮裏的禦廚各個包不出娘親味道的餛飩。
於是到了晚間,阿爹都淚眼汪汪:「阿詞,你同我交心的說一句,你是不是舍不得給我吃你的餛飩了?」
我想起自己那一日都沒享過福的娘親,忍不住插著腰冷嗤:「你日日纏結我給你包餛飩吃,怎從沒想過自己包一頓餛飩給我吃,是我沒教過你嗎?」
娘親教過阿爹的。
所以在臨近十四歲的這一年,我吃到了有著娘親味道的餛飩。
說實話,我當然不知道爹包的餛飩同娘親包的味道究竟一不一樣,可長春吃著爹包的餛飩,埋頭吃出了滿臉淚——我想,大抵是一樣的。
16
爹一直都沒能記起初夏。
直到孟夏六年,他突然就不行了。
長春與我帶著皇弟皇妹們跪在他的床前,我們等啊等,等到燈油燃盡,天空翻起魚肚白。
爹緩緩睜開眼,時隔五年,他的眼裏難得恢復了以往的清明。
爹將長春喚到自己的面前,他絮絮叨叨了很多,要長安好好照顧弟妹,要長安任人唯賢,最後,他瞪著眼,喘著粗氣要長春切記:「不要守成,要興國,要努力走到這世界的前列去……長春,長春你需得牢記,落後就要挨打,我們決計不能再讓別人欺辱到頭上來。
長春,長春啊,你需得牢記,好男兒合該在馬背上打疆土,我們孟夏的女兒絕不和親!」
長春死命地點頭,他脖頸處青筋都爆出來:「爹,我記得了,我們孟夏的女兒絕不和親……兒子會竭力開創太平盛世,叫這天下百姓日日都睡得安穩覺。」
爹笑了,他渾濁的眼睛變得愈發渾濁。
他緩慢掃視著面前的我們,最後視線落在我的臉上。
爹顫巍巍地向我伸出手:「初夏?初夏!」
「初夏……或許,或許……」
或許什麽呢?
誰也不知道,爹的話沒說完,生命最後一刻,他望向虛空的表情那樣難過又遺憾。
17
長春登基,並未改國號。
前所未有的事兒,可竟然連最迂腐的丞相大人都沒反對。
或許,大家都想在夢裏再見一次初夏。
又過了很久,久到同阿爹奮勇殺敵的那些老一輩都不在人世,久到我們這些小一輩都搖身變成了別人的阿爹阿娘。
久到再沒人敢打孟夏的主意,人人都不愁吃穿,天天都能睡個安穩覺。
我帶著自己的一雙女兒從護國長公主的神像下走過,粉面桃腮的女童敬畏著註視人像的臉,與自己的娘親說:「阿娘,今天學堂的夫子同我們講了護國長公主的故事,她可真了不得啊!」
婦人應和她:「是啊,長公主她是巾幗英雄。」
她們漸漸走遠,聲音伴著風吹來:「夫子教我們勿忘國恥,又問了我們長大後想成為怎樣的人。」
「我同夫子說,若是我做不了長公主那樣的英雄,那就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吧。」
18
史書記載:護國長公主,名孟初夏……
洋洋灑灑,數千行。
文末,史官寫:
至於美貌,是長公主最不值一提的優點。
【護國長公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