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
因为频繁去做义工,我接触到了一百多位老人家,他们大部分的年纪都在70岁以上。
人到这个岁数,离别生死,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
有个老人,她寡言寡语,很少说话,因为她的直系亲人在短短一年多,先先后后都没了,先生走了,儿子女儿也走了。这种情况下,换成谁也很难接受吧。她的应对不是倾述,她把孤独伤感都变成了阅读,看各种各样的的书和报纸。她的舍友唱腔很好,以前是在剧院做事的,经常给她唱唱歌解解闷。
有个93岁坚持洗冷水澡的老人家,她的腰背弯曲如弓。她不能穿很厚的衣服,不然皮肤的痒感会很强烈,挠不到,只能一天天忍着。这个婆婆的床上摆着几个公仔,她最喜欢是那只皮卡丘,每天睡醒都要抱一下它。
刚来的时候,她的儿子隔段时间来看她。儿子有严重的腿病,走路走不动,几百米多的水泥路他要走半个小时。儿子一辈子也没成家,很难照顾她,内心压力很大,整天愁眉苦脸的。她说,没关系,妈都知道,哪个骂你不孝顺,让他来老人院找我。是妈自己要来老人院的,不能怪到你的头上。
我还在老人院遇到一个起起落落的爷爷。
当年,义无反顾地放弃舒适的生活,自愿从香港回来,热情满满的搞建设,那时候他才十多岁。
后来当上兵了,海军,当了五六年。期间,因为素质过硬,新兵初登场,就被委任职务。就那样,在刺人的太阳、翻滚的海浪中,踏踏实实,干了好几年。明媚的前程,因为政审过不来(特殊年代的投射,他本身和出身都没问题),在老领导的几次惋惜劝说下,退伍了。
退伍了,沮丧了,又重新燃起斗志。
一路过关斩将,当上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之后教书育人,成家立业,在学校和当地都是有口皆碑的。
后来,十年开始了,学校里第一个被贴大字报被打倒的就是他,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那些纸上写的都是他,张牙舞爪,很熟悉,又很陌生。罪名很好笑,从香港过来的潜在特务……
没办法啊,认了啊,不认过不了,这是个荒唐的年代,认了也打骂,不认也打骂。最惨的,是被自己的学生打骂,那样一副大义凛然咬牙切齿的小屁孩样子,叫嚷着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和帽子,真让人心寒。
一连两个月,睡不好,吃不好,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有一天,他想到了自杀。
得了,熬不住,我不活行了吧。
那些天,他的思想斗争剧烈,身边的亲人都觉出他有些不对劲。
有一天。
门响了。
进来了他的一个学生。
大眼瞪小眼,他感到有些苦涩的愤怒,欺负人都欺负到头顶上了吗,一个当学生的单枪匹马到老师家里搞事情?
等一等。
好像有些不对。
原来,学生是冒着大风险偷偷过来看他的。小的手紧紧握住大的手,颤声说,老师,你要撑住啊,不要自杀。你知道吗?不是……不是所有人都那样看你的。
就这几句话。
把他拉了回来。
后来也恢复了名誉和工作,一晃眼,几十年时间都过去了。
人在老人院,心态平和如水,对伙食对条件,没有半点怨言。自己打趣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嘛要自寻烦恼呢。跟当年的好几个学生保持了联系,大家还会不时过来探望他,接他出去聚餐。
那天,我去探访老人,他的桌上摆着很多的书,还散放了一些笔记本。是的,他有做自己的阅读笔记,称之为打发时间。老人以前是做语文老师的,但外语学得相当好,英语和日语(工作后自学的)都很扎实。
他对我说,人老了,时间就少了,我也不怕哪天就走掉。只是觉得有点遗憾。
我问他,是怎样的遗憾呢,或者可以去试试怎样实现。
他说,实现不了了,我身体不支持我出远门,我前些时候翻译了一本讲日本历史的日语书,我想去那边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地方和环境建设得那么好那么文明。
问他,怎么想到去翻译书呢,是想出版吗(他的学生中有这样的人脉)。
他说,不是,就是锻炼一下脑筋,怕自己的思维变迟钝了。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要多看看书和新闻,睡觉前也想一想,今天学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还不懂的……人不会自我思考,跟死了又什么分别呢。
是这样的。
有的人,25岁就死了。
有的人,85岁依然青春。
(3.6补充一些)
人。
明面上是一生一世。
骨子里是一生一死。
走向是固定了。
生之前的事,我们选择不了。
死之后的事,我们做不了主。
兜兜转转一大圈,好像能做点事情做点尝试的,就是活着这个阶段了。
活着,是一个宏大的话题。
怎样活才算活出了自己的样子和意义,也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
我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哲学研习,我只是千万个路人中平平凡凡的那一类。所以我看待活着的意义,只从普通人的视角和体验出发。
在过去的生活中,我经历过亲人朋友猝然离世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这些人中,有我的至亲,有我熟悉的长辈,也有关系很普通的人,他们的离别,散布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
最初接触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是很疑惑,死是什么?
跟下来,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害怕和紧张状态。
害怕什么?
害怕自己也会死,也会静静地躺在那,一动不动——这是我太婆去世给我的最大震撼,我太婆长我七十多岁,我的童年就是她、托她保管的钥匙、滴水的瓦背和家里的那只大黄狗。明明在她去世前几天,我还经常见到她,并给她送去家里熬煮的鸡汤。那是一个慈祥有韧力说说笑笑的老太太,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
等懂事一点,这样的离别,让我知道了心痛的感觉,知道了个人世界崩塌碎裂的声音。这时候就取了一种逃避的态度,反正横竖躲不了,我就当个鸵鸟,自动屏蔽,不听不看不哭不闹吧——这是我爷爷去世后,我的整体应对态度。
那时,我二十出头。我的性格和处事,受我爷爷影响很大,因为老爸老妈工作忙,我们兄妹几个经常吃住在爷爷家,老人的脾气又很好,处事公允,没有长辈的架子,彼此间有非常多的互动和交集。也是因为这层缘故,老人走的时候,我特别崩溃,我跟他告过几次别,但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收到消息时,他已经不在了。再回去,就是空空的座椅,物是人非。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我意识到鸵鸟这种应对状态,虽然不会给我制造新的伤害,但是它没有带来新的成长。同时,它并没有真正移除掉我对人生人死人为什么活着的顾虑,内在的伤,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变本加厉制造更多的混乱和不安。
就这样。
重重机缘之下,我开始去做义工。
当时就是抱着多体验一下的想法,设想去个两次三次,见证一下医院、老人院的生老病死,「证明」自己不纠结于生死就可以了。
在没有去之前,我把这些地方整个气氛想象得很沉重。

(市桥医院,探访需由公益组织带队安排和院方沟通协商,属于有纪律有质量的集体探访,以免私人空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广州这边有三家专门的临终关怀医院,我有坚持去其中的两家,一个叫市桥,一个叫江南。
相对来说,市桥比江南更特殊一些,它们的六到八楼,收治的都是一些重病和癌末的人,大部分都是临终状态的人。如果不是家属(只是小部分患者有清楚的自我意识)主动提出换院出院,这边的病人会一直在病床上待到最后一刻。
尽管是康宁科,但能知道自己确切病情的人并不多,有些病人会被家人刻意瞒着,并要求医护人员同样保密。类似的人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之前有听到医院的一个主任做公益的线上讲座。据他了解,在他所知道的病人中,有接近六成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有的会乐观地以为自己还能好转,有的则因为一天天的病症折腾,慢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况和处境,毕竟不是所有的防范和白色谎言都能起效的。
市桥这个医院,收治的病人很杂,南北西东都有,以广东广州当地的普通阶层老百姓为主。住进来,一个月五千左右的基础费用,在这里,有住了十年饱受慢性病侵蚀的人,也有当天上午才转进来,下午就推出去的。有特别多陪伴的,家人亲友们默契配合众星捧月一样的,也有长达好几年,除了微信缴费从不露面的人。

我第一次去的也是市桥,这个被标注了生命最后一公里的地方。我陪伴的第一个老人家是一个婆婆,高龄,90岁,中风,左侧身体偏瘫,长期卧床,牙口已掉了好些,说话词句含糊,会有些漏风。老人吃饭的时候,喜欢吃鱼,只是食堂不敢也不可能天天供应鱼给老人家吃。躺在床上的时间多得可怕,等待一条鱼,等待一条姗姗来迟却又出场寥寥的鱼,就是亲人之外,老人的最大日常了。
就是这么一个长期躺床的人,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人,她的心情很平静,她接受了自己的衰老和病痛,并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有什么要避讳的。她只是用她的勺子(她不喜欢用筷子吃东西),等待一条鱼。在7楼里,在四十多号高矮胖瘦的病人中,她是极少数可以自主吃东西的那一部分。能自主吃饭,能不吃流食,是她在生命末期找到的一份力量。这个老人,在同一年的11月,永远走了。再去7楼,再经过熟悉的那张床,我就见不到她了。
有位大叔,早年走南闯北,到海边捕鱼钓鱼,到广西收黑皮甘蔗,到江西赶场子找商机,辛辛苦苦了一辈子,没见过几个大钱。
因为房屋拆迁,获得30多万的补偿。
这一世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结果,好日子没有享受几天,病痛就来了,这个病痛一早就有了,但当时威胁不大,只做了简单的手术,就那样拖拖拉拉成了重病。
看病,吃药,再看病,吃更多的药。
然后确诊了。
癌来了。
短短三两个月间,真金对白银,花掉了二十万。自生病后,子女虽有抱怨,但妻子一直陪着大叔,把原来的工作辞了,专门租了房子在附近做短工。
我们那天陪他。
大叔对我们说,我知道的,我回不去了,我会死在这里。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目光灼灼的望着我,语气十分平静。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痛。你们不知道,那种痛痛起来有多痛……」
时间快到了。
我们要去「开会」了。
大叔也在一旁提醒,差不多了,你们该走了。
然后,他笑笑着看我又看看我的小伙伴。
「下个礼拜再来看我吧。」
大叔好像想起了一点什么,又补充道:
「如果我还没死的话。」
下周再去,病床空空的,大叔走了……
把目光收回老人院。
二楼那个热爱唱歌的婆婆,每次都捧着自己的歌本,等待义工过来陪伴。她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但她的乐感很好,还自行创造了好几首健身歌,歌词取材生动,朗朗上口。
她的同屋是张婆婆,常年卧床,说不了什么话也动不了,是手手脚脚一动都不能动的那种,只有时而清醒时而模糊的神识,时重时轻的呼吸。
但很多老人羡慕她。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家人频繁且固定来看她。
多频繁?
这么说吧,她有七个子女,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轮流来一个陪老人。
固定星期天来看张婆婆的是她最小的孩子,小儿子——这是一个个头十分高大的伯伯,大概有一米八,他每次来了,绝不空手,都带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给他妈妈。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位伯伯留意到隔壁的一位喜欢跳舞的婆婆很少人来探访,每次看到他来看妈妈,总是用羡慕的眼神望着,有时还要走过来,专门望一望他们。
后边,这个伯伯每次来看张婆婆,就专门去隔壁转一转,陪陪跳舞婆婆。
然后他会给跳舞婆婆一只橘子。
一只很大很香的橘子。
每次都是这样……
我见过很多说乐天知命的人,跑去临终病房后崩溃大哭的。
有些事情,你知道和你自己去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碰撞。
同一个陪伴对象,同一小组的两个义工,受限于自己的视野和内在,看到的收获到的,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同理,同一个人,受限于自己的视野和内在,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也可能是起起伏伏相互矛盾的。
就说前面那位大叔吧,你是不是觉得他很乐观很能接纳了呢?
但在我探访前一周,他的状态一直在起起伏伏,说起往事,说起亲友,说起患病的经过,痛哭流涕。一周前,他跟另一个义工小伙伴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包括父亲的酗酒,母亲的去世——不同于父亲,他的母亲只是喜欢喝一点酒,但从不过量,七老八十后依旧保持了这个小嗜好。临走的那天夜里,母亲还喝了点酒,她身体一向不差,没啥大毛病,事前更没有半点征兆,发现时人已经没了呼吸,神态很安详。说到母亲的善终,他很感慨,也很羡慕。
大叔很明白自己的病情,心情也不是长期平静,甚至短短一周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但整体上,他已经从找到自己的调节方法,他接受了自己即将离开的事实。从抗拒、否定到接受,从悲痛、后悔到平静,这是这位大叔的磨练之道,但也有些人是反过来的。这样的逆变,会更折腾。需要找到更多的力量。
所以你看。
人活着,确实不容易,反反复复的,起起落落的,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做。
也正是这样。
你知道了活着活好有多不容易。
然后才会真的发自内心去珍惜,带着自己的韧性去直面那些苦难。
这个世界。
最不缺的就是挫败和孤独。
但也总有一些人和事情会来温暖我们。
传递一只橘子。
是我补充这份回答的意义。
看清生活的真实面目后依旧热爱生活。
是我所看到的活着的意义。
(4.8补充)
整理了自己知道的主要涉及生死观、告别的一部分影视剧和临终关怀者手记、绘本。
有助于提升对死亡、告别的理解、释怀和承载力。
【入殓师】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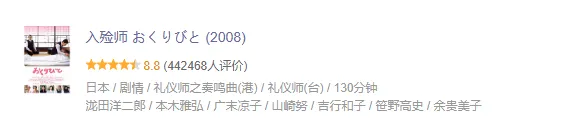
【遗愿清单】(电影)

【遗愿清单】(书籍)
纪慈恩就是资深的儿童福利院和临终病房的社会工作者,体验死亡工作坊创始人,乌托邦临终庄园创始人,书是她本人十年2700小时临终关怀经历得来的触动和成长,很值得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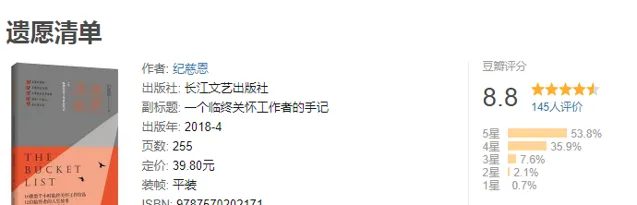
【人间世】系列纪录片

【我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系列纪录片

【死亡医生】(电影,有故事原型,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和尝试)

绘本——考虑到有些人对题材表达和时间比较敏感,想了解,但又不想花太多时间,想看见,但又不想太沉重。
那么不妨试试另一种办法,主要通过画面来展示的向死而生,同时这些绘本也适合跟小孩分享、讲述。这也是我在另一个公益组织跟病房里的孩子们互动的方式,讲绘本故事。当然,每次内容都需要提前报备,尽量给他们带去一些放松,生死观内容的绘本也要择优而从,不一定都能通过。
【有一天】
【当鸭子遇到死神】
【爷爷变成幽灵】
【一片叶子落下来】
【告别安娜】
【爷爷的墙】

在这两篇文字里。
关注点在于如何看待亲友的老去,如何看待自己或亲友的最后一程,分享了我作为旁观者的一些心事触动。同时,还谈到我在临终关怀医院所看到的,一对恩爱夫妻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的感人故事。
对陪伴故事和临终关怀感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留意我的知乎夏花专栏。
我会持续更新。
这是本文的姐妹篇。
做义工的最初考虑和动摇都在里面。
详细记述了早中期探访中印象最深刻的生死故事。
(转载请提前走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