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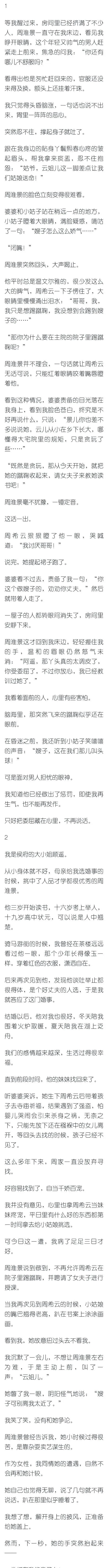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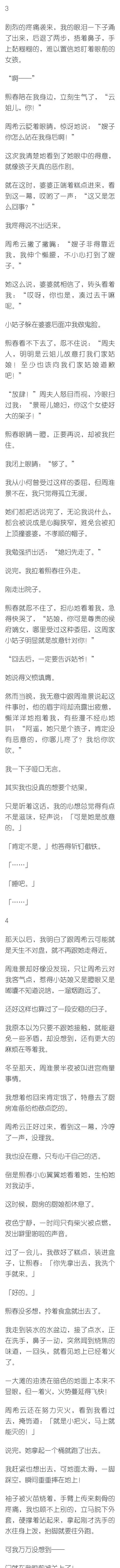
5
我的眼睛猛地剧烈晃动起来,难以掩饰惊恐。
她这到底是要干嘛!
我赶紧走了几步,用力去拉门,可是怎么也拉不开,只好敲门叫:「周希云,周希云——」
可门外,脚步声却越来越远。
狭小的厨房里,热气滚滚而来,夹杂着呛人的烟雾。
恐惧、无助和绝望如同潮水一般涌上心头,我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喉咙被烟熏得直咳嗽,几乎喘不过气来,每一声都艰难无比:「救命啊——救命!」
「啊!」
「姑娘!」
透过一扇门,我听到熙春惊慌失措的尖叫声:「起火了,大家快来!姑娘还在里面呢!」
然而,火焰已经蔓延到门口,无法靠近。
看着火势越来越猛烈,就在我以为注定要在大火中丧生时。
突然听到一声惊呼:「大公子——」
「嘭」的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一个高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看到我的模样时,瞪大了眼睛:「遥儿!」
深冬季节,我全身湿透,头发上还在滴水,狼狈不堪地蜷缩在水缸旁,手里紧紧握着湿毛巾捂住口鼻,听到声音,下意识抬头看去,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嘴唇颤抖着喊:「大哥哥?」
「别怕,哥哥来了!」
顾隅安几步走到我面前,抱起我离开了厨房。
刚一出门,熙春就冲了过来,看到我脸色苍白,手臂和衣袖粘在一起,血肉模糊,眼中含着泪水,声音哽咽:「都怪我,我就不该离开姑娘的!我,我想着天冷,赶紧回去给姑娘拿件大衣来,没想到……」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隅安严厉地打断了:「还不赶快去请大夫!给姑娘披上大衣!」
「是,是!」
温暖的大衣披在我身上,我眼前一片漆黑,只能听到熙春手忙脚乱地去请大夫,她走得匆忙,似乎撞到了什么人。
接着,我听到了周希云明知故问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熙春这会儿哪有时间理她,用力推开她,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疯子!三番五次打姑娘还不够,竟然还想害死姑娘!」
周希云身体一晃,摔在地上,抬头看到被抱着的我,眼神闪烁:「嫂子,你……」
听到她的声音,我全身一震。
顾隅安本来正抱着我往主屋走,听到熙春的话时脚步一顿,看到我颤抖,立刻怒火中烧。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男人几步上前,一脚踢在了女人的胸口:「贱人!」
「啊!」
周希云尖叫一声,转过头就晕了过去!
婆婆得知消息急忙赶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老太太脚步一停,瞳孔瞬间放大,捂着胸口,两眼一翻,差点摔倒,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回过神来,扑向了周希云:「云儿!」
现场一片混乱。
顾隅安连看都没看那对母女一眼,只是心疼地看着我:「哥哥来晚了。」
我摇了摇头,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实在是没力气,慢慢闭上了眼睛。
以前,一个是我婆婆,一个是我的小姑子,我真的不想让场面变得这么难堪。
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想管了。
6
处理完伤口已是深夜,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看到只熙春守在旁边。看到我醒过来,她高兴得泪水盈眶,急急忙忙倒了杯水给我,声音有些嘶哑:「小姐,您醒啦,快喝水润润喉咙!」
我这才听到外面房间有争吵声。
「我妹妹才嫁给你两年,你就让她陷入危险,周淮景,你当初娶她的时候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可能是个意外——」
「瞎扯!遥儿一直很谨慎,这次如果不是为了给你准备宵夜,她也不会去厨房,可你那个妹妹,险些害死她!」
「希云说她对此事毫不知情……」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要么,你直接把那个坏女人宰了,要么你就和你妹妹离婚,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虽然愤怒至极,但怕吵醒我,他们俩都压低了嗓音在争吵。
熙春也听到了,帮我倒了杯水,接过茶杯,眼泪又掉了下来,气愤地说:「安哥儿说得对,姑娘,这周家小姑子真是个难缠的角色,心肠也太狠了,我们绝对不能再和她住在一起!」
我抿着嘴没说话,眼睫毛微微垂下,手指缩了一下,紧紧抓住了被子。
周淮景虽然平时不怎么说,但我知道,在周家人中,他是最疼爱这个妹妹的。
然而——
周希云害得我如此地步,我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那边听到屋里有动静。
紧接着,说话声停止了,顾隅安低头穿过帘子,大步走了进来,看到我半躺在床上,受伤的手臂包扎着,既惊讶又愤怒,缓和了一下语气对我说:「遥儿,母亲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让我带你回家。」
身高八尺的男人面容英俊,眼中充满血丝,显然是气得不轻。
在他身后,周淮景嘴角肿了一块,担忧的眼神直直地落在我身上,欲言又止。
我避开他的视线,轻轻点了点头,低声说:「好,我跟哥哥回去。」
这话刚说完,周淮景的脸色立刻变了。
7
「阿遥——」
他往前走了一步,却被顾隅安狠狠推开,男人瞪大了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我顾家交代吧!」
说完,也不给周淮景说话的机会,命令熙春和我房间里的其他女仆:「你们几个,收拾一下姑娘的东西,走。」
「是。」
几个人纷纷答应。
熙春迅速收拾好了东西,等上马车时,我原本以为周淮景会来挽留,但没想到,直到马车驶出周家,也没见到他。
马车的帘子半掀开。
迎面吹来的风穿透心脏,带来冰冷的寒意。
我的指尖僵硬。
原来在他心里,我的生死并不重要吗?
「姑娘您别伤心。」见我久久没有放下帘子,熙春担忧的声音传来,唤回了我的思绪。
我收回视线,放下帘子,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说不出的失望。
8
我回家休养了一个多月。
手臂上的烫伤不算严重,只是感染了严重的感冒,整日昏昏沉沉。
母亲常常来看我,每次看完离开时都会拿着手帕擦眼泪,无论怎么劝都止不住。
直到接近年末,我的病才有所好转,母亲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坐在床边和我聊天,后怕地说:「你这个丫头,要吓死娘了!」
熙春站在一旁,顺着母亲的话说:「可不就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吓坏了,如果不是那天夫人惦记姑娘冬至日喜欢吃夫人亲手包的饺子,晚上也让安哥儿送,还不知,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话出口,熙春的眼睛又红了,妇人眼里也含满泪水,直骂:「我都听熙春说了,你那个黑心的小姑子怎么忍心把你一个人关在厨房,你从小就身体不好,又是那么冷的水,又是烫伤,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啊……」
说着,眼泪直流。
我心疼得不行,赶紧抱住妇人颤抖的身体,安慰她:「娘,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嗯,好好的。」
妇人用力地回抱住我。
有嬷嬷站在一旁,用手帕擦掉眼泪,笑着说:「夫人,姑娘现在还好好的呢,快过年了,不能再哭了。」
「你说得对。」母亲听了劝,擦去眼泪,正想再说点什么,这时,有小厮在门口传话:「夫人,姑娘,周家来人了,说是接姑娘回去。」
听到这话,妇人眼睛一瞪,突然站起来:「回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差点害死了我的女儿,要怎么处理!」
9
前厅里,周家人都来了。
我到达时,一道炽热的目光立刻落在了我身上。
是周淮景。
他起身想向我走来,但在对上我淡漠的眼神时,又硬生生坐了回去。
周希云跟在周夫人身边,脸色也有些苍白,看到我的眼神,她心虚地转过头。
父亲和大哥早就到了。
至此,两家人才算是到齐了。
婆婆先开口:「景哥儿媳妇,那天的事我也听说了,希云这孩子毛手毛脚的,不小心关上了门,她并不是有意的,但你哥哥那一脚,却差点要了她的命!」
我抬头,突然觉得好笑。
原来是来找麻烦的?
听到这话,顾隅安立刻坐不住了,骂道:「荒唐!你们周家的女人故意害我妹妹陷入火海,就算打死她,也算便宜了她!」
他是当官的,气势非凡。
「你——」
周夫人怒火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但是因为忌惮侯府的权势,最后只能抱着周希云痛哭流涕:「我的苦命女儿啊,我本来以为你嫂嫂是个好人,能照顾你,没想到,人家天生富贵,我们这种人家根本配不上。」
父亲和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我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目光扫过一直沉默的周淮景,心里的失望越来越深。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传来周希云抽泣的声音:「我,我并不是故意要害嫂嫂,只是那天真的很害怕,我以前犯了错就会挨打,所以……」
说着,她跑到我脚边,抓住我的裙摆,看起来可怜极了。
熙春站在我旁边,听到这话冷笑一声:「是啊,你自己害怕,我家姑娘就不怕了,就应该被你关在厨房里等死!如果不是我家姑娘聪明,用冷水浇遍全身,现在恐怕已经不在人世,到时候你还不是随便怎么说?说不定你还会说是姑娘自己不小心点燃了厨房呢!」
周希云的哭声突然停住,打着哭嗝说:「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现场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周淮景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说:「云儿,够了!」
所有人都看着他。
在众人的注视下,周淮景只抬头看着我,眼睛下面一片乌黑,看起来疲惫不堪:「这件事是我周家的错,但是能不能,让我跟阿遥单独聊聊。」
10
他说得非常诚恳。
母亲原本想拒绝,但是看了我一眼后,还是答应了。
我站起身,跟着周淮景走进了内室。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男人心疼地握住我的手,喉咙微微滚动,眼泪似乎都要涌出来:「那时候你是不是很害怕,很疼?」
我紧咬嘴唇没有说话。
据熙春说,他这段时间送来了很多好东西给顾家,只是我还在昏迷中,他无法进来。
可是我不能不生气。
「对不起。」
突然,一滴眼泪落在我的手上,热乎乎的。
我惊讶地抬起头,正好对上男人含泪的眼睛,心里五味杂陈。
「淮景……」
他低下头,紧紧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对不起。
好像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我的心脏,反复拉扯,脑海里那些快乐的日子一闪而过,我终于心软了:「周淮景,我不希望你打死她,不如这样,你打她几板子,把她送到庄子上去,或者我们搬出周家,跟她们分开住,只要她不再来找麻烦,我就不计较这件事。」
这已经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没想到,我的话刚说完,男人突然抬起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阿遥,你明明知道她从小受了很多苦,怎么还能说出把她送到庄子上去的话?分开住?母亲还在,我怎么能不孝顺母亲?」
「可是她要害死我!」
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
如果不是那天哥哥像救星一样出现,现在我可能已经死了!
「她只是害怕,不是故意的,阿遥,她还小,我会惩罚她,但我不能不管她。」
周淮景试图跟我解释,看到我的脸色越来越冷,声音里也带着一丝焦虑:「你以前最善良体贴,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再说,你哥哥已经踢了她一脚,这一个多月,她受伤比你还严重……」
我猛地抽回自己的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要害我,我的哥哥为我出气,我就要原谅她?如果不原谅就是不够善良体贴了?什么叫她受伤比我严重?我差点死在火里!」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伸手想来握我的手,却被我躲开,连日的疲惫和我的冷语,到底让他少了几分耐心:「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计较,我们好好过日子不成吗?」
「这算是小事?」
我盯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话会从他的口中说出。
「如果我的性命都算是小事,那还有什么算是大事?还是说,只有你周家人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眼见我越发激动,周淮景忙站起身,试图揽我入怀,放软了语气:「阿遥,你冷静一些,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和希云都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们哪一个受伤我都会心疼,你何故说这样的话来刺我?」
我后退了两步,冷冷的盯着他。
是。
周希云可怜。
可她可怜,所有人便要一味地纵容她吗?
我做不到。
沉默良久,那句在脑海里徘徊了多日的话到底是脱口而出:「周淮景,我们和离吧。」
11
在今日之前,我从未想过会和周淮景和离。
周家虽不是王孙贵族,可也是书香门第,祖辈是做过宰相的,世代簪缨,是少有的清流人家。
我的郎君,更是这盛京城里惊才绝艳的青年才俊。
我一侯府嫡女,嫁给他虽是低嫁,也算不上委屈。
出嫁那日,闺中的小姊妹还曾羡慕我,能得一如意郎君。
可如今,我忽然觉得累了。
原先我看中他温柔的脾性,懂得顾家,可如今,又恨他这点,他心中疼惜妹妹本没有错,可如今危及我的性命,是断不能容忍了,我们之间,闹到今日这般,他只能周全一方。
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周淮景猛地站了起来,泛红的黑眸里闪烁着震惊:「阿遥,你,你要与我和离?」
我没有作声,算是默认。
肩膀忽然被握住,他明显有些急了:「阿遥,你已嫁给我,离了我,你很难再嫁,难不成你要青灯古佛一辈子?」
若说之前我只是觉得他优柔寡断,到如今,我只觉得自己看走了眼。
我抬眼,直直对上他的眼:「所以呢?你想用此来威胁我?」
他的眸光闪烁着。
我唇角微扯,甩开他的手,转身朝外走去:「周淮景,没有谁离了谁不能活的,我未来如何,与你无关,若你还念我们的夫妻情分就签了和离书,也算是全了两家的颜面,如若不然,你妹妹怕是难逃罪罚。」
身后,男人的拳头紧握着,用力到骨节发了白。
12
那日不欢而散。
听说我要和离,周家人并没有什么意见。
周夫人心疼宝贝女儿,若非理亏,恨不能将我哥哥告上开封府,周淮景一夜憔悴了许多,终于在第五日送来和离书。
看到和离书,母亲却是没有那么高兴。
明明是快要过年,可全家都萦绕在一片愁云惨淡的氛围里。
吃饭时,我心里愧疚,放下筷子,低声说:「爹娘,哥哥,我……」
只刚刚起了个头,母亲便握住了我的手,冲我摇头。
哥哥也看向我,正色道:「遥儿,此事你做得对,那周淮景并非良配,他实不是个能担当的人,若你这回都忍了,将来指不定还要受多大的委屈,哥哥并不能回回都护住你,还不如你就此脱离周家,有道是已入穷巷,不如及时止损。」
一直没有发话的父亲也赞同的点了点头:「你哥哥说的极是,咱们是侯爵人家,你哥哥又仕途顺遂,不比那姓周的差,往后你只管住在家里,照旧是我顾家女。」
闻言,我的心头升起一阵暖意。
我何其有幸,能得此父母兄长。
可话虽如此,但我朝极少有妇人和离后一直住在家中的。
这才几日,外头便流言霏霏。
熙春怕我听了心里难过,在我面前是万万不肯提上一字半句的,可耐不住府里人多嘴杂,我少不了知道情况。
外头都说是我们姑嫂不合,这才和离。
外人不知实情,只当我是那不知体恤小辈的恶嫂嫂,我的名声算是毁的差不多了,往后想要再嫁人,怕是难了。
父亲最是在意门户脸面,可为着怕我伤心,他只字不提。
我反握住母亲温暖的手,缓缓道:「母亲,我想开女学,我自幼饱读诗书,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又何故非得为人妻,不能为人师?」
这话落下,满座皆惊。
13
原本眉头紧蹙的母亲霎时间瞪大了眼睛:「可,可你和离过,怕是会惹来许多闲言碎语——」
父兄也投来担忧的目光。
我直直迎上他们的目光:「母亲,我朝条文都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女子自有选择和离的权利,我又何必感到羞耻?」
更何况——闲言碎语罢了,任他人说去。
我并不放在心上。
嫁人也好。
不嫁人也罢。
都是人生的一种活法,我并不后悔。
若前路走不通,那便换一条路走。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自轻自贱了自己。
对面,顾隅安瞳孔微震,许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良久,青年忽然朗声大笑起来:「好,不愧是我顾家的女郎!」
我弯唇浅笑,郁闷了多日的情绪终于消解。
人总要活下去的。
14
再见到周淮景,已是一年后了。
当今圣上看中女学,虽不能登科及第,可终究算是件体面的事。
我出身侯府,哥哥又仕途坦荡,便是为着结交,也有一些豪门贵族将年纪小的女儿送至我这。
一来二去,从前的事倒是如云烟一般淡忘了。
我本意是不想再嫁,可耐不住母亲总劝。
她每每咒骂,男子能三妻四妾,女子和离了为何不能再嫁,不仅要嫁,还要嫁得好!
我明白她的意思,倒不是觉着女子离了男子就不能安身立命,只是她希望我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为父母的,总希望子女过得好一些,再好一些。
我如今不过十九岁,又不曾有过孩子,她便时常去打听,又将我从家塾拉出去,到处赴宴,硬气说:「有母亲在,你大胆去看!便是没有婚娶过的好儿郎也成,我的遥儿这么好,定不愁嫁!」
我失笑,却不忍辜负了她的好心。
春日里,我受邀参加马球会。
正与一豪门娘子相谈甚欢,忽觉一道灼热视线。
回头望去,原是故人。
一年不见,他清减了许多,身形瘦削,那目光直直的落在我身上,似有千言万语要诉,而女眷席里,周希云穿金戴银,正嘻嘻哈哈的,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我淡淡收回视线。
就在这时,一道矫健的身影自不远处走来,笑着唤我:「顾遥!」
我回眸看去,看清来人,略感讶然。
是谢慕行。
他长我两岁,幼年时曾与我一同读过家塾,他是将门子,酷爱舞刀弄枪,四年前便远赴了边关,说是要凭借自己挣个功名回来,两年前打下胜战,回京参加了我的喜宴后便又走了。
再见面,便是现在了。
与我一同说话的谢家娘子见着他就骂:「你都多大年纪了,成日在外头跑,还不快快来这边坐下!」
闻言,谢慕行笑着挠了挠脑袋,凑到她身边坐下。
谢娘子逮住他便是喋喋不休的同我说:「他啊,是个没头脑的,成日不着家,我都不知给他相看了多少家姑娘,嘿,你猜他怎么说?」
这倒是吊起了我的好奇心。
「如何说?」
「母亲——」
谢慕行黝黑的脸罕见的红了,拦着谢夫人不肯她说,可耐不住谢夫人嘴快:「他说自己是当和尚的命,断情绝爱,拔刀够快!」
我:「……」
谁家和尚动不动拔刀??
见我怔愣,谢慕行急急给自己找补,皙白的耳尖红了一片:「你别听我娘瞎说,有情有爱,拔刀更快!不对,拔什么刀,不拔刀,现在以和为贵!」
我微笑。
谢娘子的视线在我们身上逡巡,哎哟了声,抬眼望了眼马球场,招呼道:「今日天气好,不如你们去打上一场?」
我自幼体弱,将养了许多年,倒不至于连场马球都打不了。
正好也许久没有松动过筋骨了。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周希云也上场了。
她也瞧见了我,坐于马上,仿佛早早把那些龃龉都忘了,笑哈哈的说:「顾遥,你可要小心咯!」
我不欲与她多言,兀自策马。
两队很快开赛。
周希云是同另一个女子一组,两人配合的不错。
但我和谢慕行也不赖。
没过多久,比赛形势焦灼起来。
但就在我弯腰去够马球时,忽觉头皮发麻,余光瞧见一根棍子直直朝着我的头部而来,刹那间,从前被蹴鞠击到头部的痛楚席卷而来,心脏骤缩。
15
但下一刻,预料中的疼痛却没有袭来,反而是一声惨叫。
「啊——」
我的马背上多了一人,强势将我捞进怀里,见我脸色惨白,男人顿时勒住马绳:「遥儿!」
我被谢慕行抱下马背,心脏仍在剧烈跳动。
看台上,周淮景已经冲了过来。
这回他亲眼瞧着,心下陡然失了速,几乎是几步就行至我身边,急声唤:「阿遥!」
我冷汗直冒,余光却瞧见周希云摔在地上,几乎动弹不得。
估摸着是被谢慕行踹下了马。
「哥哥,我疼……」她在呼唤。
听见她的声音,周淮景立刻回头看去,见状,脚步一时摇摆不定,可最后,还是走向周希云,命人叫来担架,送去看大夫。
谢慕行仍抱着我,见着这幅画面,眼眸微暗。
良久,他忽然低头说了一句:「对不起。」
嗯?
还不等我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轻轻将我放下来,猛地冲了过去,逮住周淮景就暴打:「妈的,老子帮了你那么大的忙,你他妈就是对她的!!」
一拳接着一拳,拳拳到肉。
周淮景是文官,哪里经得起他这么打,很快,就有人把两人拉开。
我勉强恢复平静,一抬眼,却见谢慕行双眼通红,在对上我的视线时,他沾血的拳头忽然一拳砸在他自己脸上!
「妈的,老子真是个蠢蛋!」
16
我不明所以,但还是走过去,纳闷道:「你这人,怎么疯起来连自己都打?」
他看着我,就那么看着,忽得别过头,抬手用力一抹:「因为我是个蠢蛋。」
我:「??」
青年黑黢黢的一张脸,五官算得上英俊,是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小将军,可此刻,却在自怨自艾。
谢娘子也过来了,见他嘴角流血,当即叫来了大夫。
熙春也快步跑到我身边扶着我,一场闹剧算是暂时拉下了帷幕。
但不过半日时间,马球会上的事便传遍了上京城。
若说之前是在周家内发生的事,为着和离和那一脚,顾家没有把事情闹得太大,算是饶过了周希云。
可如今,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害我。
顾隅安一纸诉状,连着之前的事一并发作,直接将周家告上了衙门,又连请了两日的假,此事上达天听,圣上大怒。
周夫人是有诰命的,连夜入宫为女请罪,磕破了头,这才免了周希云的死罪,但因教女不善,放下大错,被剥夺了诰命。
周希云被打了二十板子,卧床不起。
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正坐在庭院里喂鱼。
熙春气的眼睛直瞪:「怎么总是这样,姑娘没死那是姑娘命大,怎就不能杀了她!」
我洒下鱼食,眼神望向远处:「她有个好母亲和好哥哥。」
只要是没有出人命,为着她那些年受的苦难,周家人都能替她兜住。
但惯子如杀子。
上一回,是用我和周淮景的婚姻免了她的死,两家也算是彻底断了交。
周淮景是有才,朝堂背景复杂,得罪了侯府,他的仕途并不会好走到哪里去。
这一次,是用她母亲的诰命免了她的死。
周大人拼尽一生为妻子挣来的东西,如今也没有了。
若是还有下一回。
我不知道,周家还能拿什么来护住周希云的命。
17
正说着,就听人来报,说是谢慕行来寻我。
听到这个名字,熙春愤怒的神情一敛,眉眼带出几分笑来,变脸快极了:「那姑娘与谢郎君说说话,我去泡壶好茶来。」
我颇感无奈,只远远的就见青年一身墨色劲装,沿着石子路行至庭院内。
有阳光落在他身上,他的马尾轻晃,一如当年少年意气。
他在我面前落座,低着头久久不语。
我给他斟了一盏茶,明眸望向他,打趣:「什么事难倒能我们的谢小将军?」
他伸手去拿茶杯,一口饮尽了,试探着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半晌,小声说:「我要是说了,你定会恼我。」
「那你便别说吧。」
我慢悠悠的说。
说来也怪,我与周淮景琴瑟和鸣时,在他面前,我也总是端着的,有什么心事都揣在心里。
可见了谢慕行,他为人耿直,说的弯弯绕绕了,怕他听不懂,索性也直来直往。
「那不行。」
我不听,他却来劲了。
我轻呷一口茶,掩下唇角弯起的弧度。
倒是好骗的很。
果不其然。
他眉头微皱,忽而闭了闭眼,一股脑说了出来:「其实,那周希云是我帮着周家找回来的,我原来打听了,说是姓周那小子总花费时间去寻他那妹妹,怕他没工夫陪你,我便特意托人找到了人,给他送了消息,没想到会闹出这样的事,说来说去,若是我当时没多事就好了……」
我喝茶的动作一顿。
良久没有听见我的回应,对面的人坐立难安,颤颤巍巍的抬起头来,窥见我面无表情,眼底流出慌乱:「对不住……害你受了那么多苦,累了名声,我,要不我去给你家当赘婿吧。」
我:「?」
熙春端着茶上来时就听见这么一句,当即喷笑出声:「谢郎君,这赘婿传出去可不好听啊,老将军知道了可不得打断您的腿……」
谢慕行一贯是个厚脸皮的,只这会儿也有些臊,强撑着道:「胡说什么,顾家是侯门,我家是将门,但自古王侯将相,将本就排在侯后面的,我当赘婿岂不是十分合理?」
熙春听他的歪理听的一愣一愣的,最后想了想,竟对我说:「姑娘,谢郎君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你听他瞎说。」
我摆摆手,熙春自然退下。
我正视着谢慕行:「那不是你的错,你不必愧疚。」
诚如他所言,周家人思念女儿,周淮景有大多时间在外寻找妹妹。
找到周希云后,他确实多了些时间陪我。
可凡事大抵难以两全。
「可若非是我,你与他也不至于闹到如今的地步……」
「与他和离,是更好看清了他的为人,就算你不帮着他找,顶多是时间问题,几年后,他总能找到的,到时候也是这样,没什么分别。」
我垂下眼睫,语气不缓不急。
这话落了,对面的人久久没有言语。
我抬眼看去时,却迎上一双透亮的目光。
相顾无言,只得一笑置之。
末了,他犹豫了会儿,又提了一嘴:「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什么?」
「找我当赘婿啊,我走南闯北,什么事都知道,力气也大,什么活都能干,还会做各地吃食……」
「……不行。」
「哦。」
18
其实我能明白,谢慕行对我有几分好感。
只是对于再婚嫁一事,我实是没什么心思。
倒是谢慕行自打回京后,三五日便往我家来,与我的哥哥称兄道弟。
谢家娘子也隔三差五邀请我去赏花赴宴,话里话外说起家里现在只那么一个儿子,长子驻守边疆,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
母亲乐见其成,但考虑我的情绪,没有多提,但眉眼间都是促狭笑意。
我:「……」
头疼。
真的头疼。
又过了大半年,京中出了一件大事。
周家流放了!
晚间吃饭时, 母亲喝了好几口酒,才将听来的消息托出。
脸上却不是高兴, 而是后怕。
「还好咱们遥儿和离的早, 不然恐怕也要遭此祸事!说来周家那女郎,七月里,周家夫人带她去王爷家赴宴, 本意是要为她寻一门好的婚事,却不想,她与郡主闹起了矛盾, 竟失手将人推入湖中,那姑娘命不好, 救上来时已经没气了!」
「那郡主可是王爷王妃的老来女, 老王爷气的当场就要拔剑杀人, 却被周淮景拦住,推搡下, 竟是推了老王爷,这下可是彻彻底底的得罪死了王府, 当晚陛下就革了周淮景的职务,打死了周希云, 判的全家流放了!」
说到这儿, 母亲抚着胸口不住的喘气,显然受惊不小。
我的眸光微晃,可到底没说什么。
父亲叹道:「都是命。」
我顾家没能要她的命, 周家却不以此为戒,好好管教,落得此等境地,也不无辜。
养而不教,父母之祸;教而不善, 父母之过。
19
周淮景流放是在秋日。
秋高气爽的天气。
我没有去看, 与他夫妻一场,不至于落井下石。
只是熙春犹豫着掀帘进来。
见我正在绣花, 嘴唇嚅嗫了下, 转身就要出去,却被我发现:「何事?」
小丫头顿了顿,手指攥紧了:「姑娘, 周, 周郎君他……」
「他怎么了?」
熙春抿紧唇, 从袖中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这是周家郎君入狱前托人带给我的, 说是给姑娘的。」
我的视线下落,定格在那清隽的字迹上。
沉吟良久,还是打开了。
上面只有寥寥一行字。
阿遥, 此生,是我对你不住。
……
我们曾檐下看雪,曾秉烛夜谈。
曾举案齐眉, 曾互诉心意。
可如今。
只化作寥寥只字, 被烛火一烧, 随风散在风里。
熙春静静看着,一时没人再说话。
蓦得。
外头又闹了起来。
有小女使跑过来禀告:「姑娘,谢郎君又来了!还带了许多聘礼!」
他人流放日, 上门求娶时。
损。
实在是太损。
我扶额叹息:「走,去瞧瞧。」
这个泼皮无赖,看来是要赖定我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