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劇照。
關於霸淩的探討,從未停止。很多人覺得孩子被霸淩,是因為本身不夠「強」,但對於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和哲學家赤阪憲雄來說,這種弱肉強食的思維與青少年所處的現實有所偏差,成人更難以窺見霸淩的真相。
在以下對談中,河合隼雄和赤阪憲雄認為,霸淩表面上是欺負與被欺負的對峙,實際上則是由「猜測和偏見」引發的沖突。在群體中,霸淩往往並非由一個人完成,任何人都有可能因為某種難以置信的原因成為「異人」,進而被群體霸淩。

河合隼雄(1928-2007),日本著名心理學家,日本第一位榮格心理分析師,曾任日本文化廳廳長、日本京都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著有【心的棲止木】【大人的友情】【愛哭鬼小隼】【孩子的宇宙】等。
同時,對「好孩子」的單一定義促成了霸淩的加劇,單一的評價標準下,將他人「異人」化的行為會更頻繁,也有更多名目。當談到如何在觀念中消解霸淩時,河合隼雄說:「如果大家能認識到人本來是千姿百態的,哪怕只是父母和教師認識到人多樣化的美,也會有很大幫助。」(相關閱讀:面對校園霸淩,這8本童書陪孩子走出陰霾)
作者|[日]河合隼雄
[日]赤阪憲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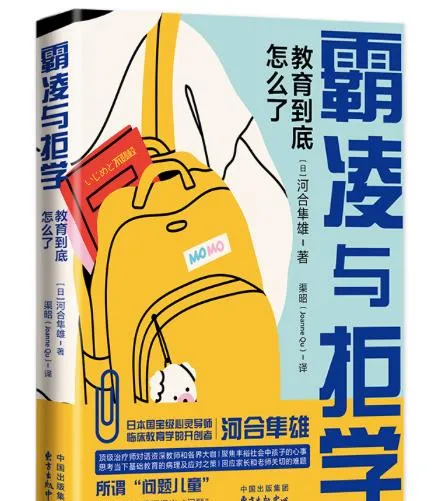
【霸淩與拒學】,作者: [日]河合隼雄,譯者: 渠昭,出版社: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時間: 2024年2月。

小小課外輔導班裏
所見的「霸淩」
河合:我們在臨床教育第一線工作,霸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赤阪先生是一位哲學家,您對這個問題也一定非常有興趣。我想先請您談談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的起因,以及這個問題在您的研究課題中的意義。
赤阪:我從二十大幾開始,大概有十年時間曾在課外輔導培訓學校當教師。那是一個只有附近孩子參加的每個班只有三四個學生的小型輔導培訓學校。
河合:大約是什麽年齡的孩子?
赤阪:多數是小學高年級到初中、高中左右的學生。我當然沒有特別挑選過,不過來的都是些在學校受欺負的、拒絕上學的、態度一貫惡劣的孩子。好像去不了大輔導培訓班的孩子們都集中到我這兒來了。從現在算大概是七八年以前吧,我比較有機會聽得到這些孩子嘟嘟囔囔。
我是比較早就開始註意到「霸淩」問題的,差不多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吧。我就是那時候開始註意到,學生中有人用「村八」或「八分」這些詞的。我納悶他們在說什麽,再仔細聽,他們說的是「村八分」(「村八分」是日本江戶時代後期,村落中實行的一種民間慣例,是在一個村子裏,全村對不遵守村規的人家絕交的制裁行為。有「廢除」「排斥」「被大家排擠在外」的意思。——譯者註)。這就是我遇到的這些根本不可能懂「村八分」含義的孩子,卻口口聲聲「八分」「村八分」地欺負謾罵同學的最初一幕。所以應該說,因為覺得學生的這個說法奇怪,我才開始註意到了學生中的霸淩問題。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的是,被欺負物件不斷地變化這一點。在我非常驚訝時,正好有人受欺負了,所以我就去問當時七八個人的一個小組裏最聰明,運動方面又好,又關心他人的少年。我問了一句「怎麽回事?」就這麽一句話,欺負人的動作竟忽然消失了。我想這應該是我問了以後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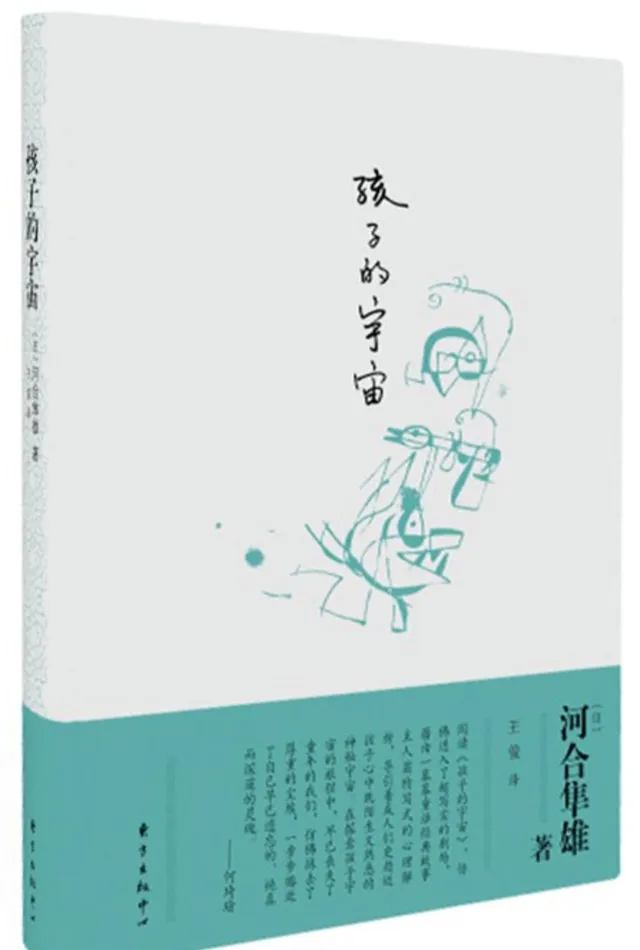
【孩子的宇宙】,作者:[日]河合隼雄,譯者: 王俊,出版社: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時間: 2010年1月。
河合:應該是這樣的。
赤阪:那時候沒什麽經驗,以為說一句「別那麽卑鄙地欺負別人」就能制止這種事。那次的事突然消失後不久,接下來那個愛關照別人的孩子就開始受欺負了。他變得非常憂郁,我當時對此事感覺非常不可思議。
也就是說,團體裏蠻有威信的這個小頭頭,按常規不會受欺負的少年卻也在被欺負。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從感覺到事情的奇怪,到發現了今天的霸淩跟我們小時候的被欺負不同。這樣,我便開始註意霸淩問題了。
河合:因為你在校外輔導培訓班工作,所以能看到霸淩的情況,這一點我很理解。另外,有些人並沒有認識到,現在的霸淩與過去的欺負人並不是一回事。這樣的人會說,欺負人的事,不是早就司空見慣了嗎,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他們認為霸淩是一句話就能控制的事情。這樣去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直接造成了霸淩問題日益增多的局面。而且,連以前不可能受欺負的人,現在也成了被霸淩的物件。
赤阪:而且,霸淩的概念和性質也發生了相當的變化。比如說以前還沒上學的孩子,只要三四個人在一起,也必然會出現欺負人的事情。但常見的欺負人的情景是,比較強壯的孩子為了實作自己的願望,去攻擊軟弱的孩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強壯的孩子對付幾個軟弱孩子的情景居多。可今天的霸淩現象則不然,被欺負的物件往往是一個人,欺負人的卻占多數,有時甚至為整個團體。這種情況與「故意冷落別人」及「村八分」的說法相關聯。當我們能從表面上清楚地看出這些特點時,就知道這種霸淩的性質與之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了。
河合:如果只是弱肉強食的問題就比較容易明白,可今天的霸淩並不是這種情況。現在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霸淩方式也有了很明顯的變化。對赤阪先生來說,您已經認識到了這些變化,並從這方面進一步探索和理解人性問題。
然而,家長和教師其實很難看到霸淩,對此怎麽才能說清楚呢?當然孩子們偷偷摸摸地欺負人也是事實,大人真的看不見。正如一開始您曾提到,課外輔導老師與學生們在一般交往中可以看到一些,可當你想去幹涉一下時,霸淩會立即消失。之前他們也許會把輔導老師當成朋友,你若想引導一下,他們會馬上意識到「那家夥是大人」,對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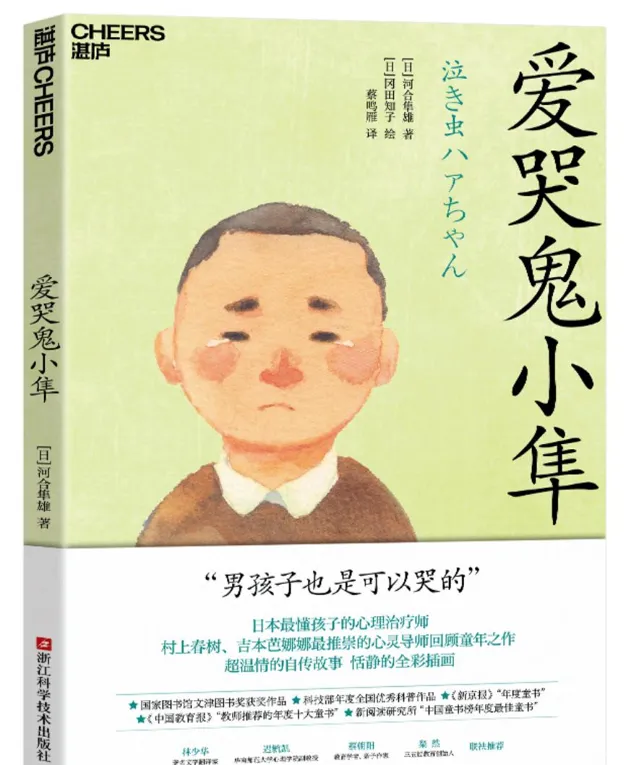
【愛哭鬼小隼】,作者:[日]河合隼雄 著 /[日]岡田知子 繪,譯者: 蔡鳴雁,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 2013年1月。
赤阪:對。所以我只管了一次即以失敗告終了。之後,便采取不直接幹預而進行觀察的態度。這樣,孩子們就會小聲說一些欺負人和被人欺負的事。
比如,有一次,聽到兩個像是初中三年級的女學生在說一件事。原來是說班上有個不順眼的學生,遭到了很厲害的欺負,現在不來上學了,結果住進了精神病院。作為肇事者的這兩個女學生竟然說,「她現在住院了,那咱們今天晚上拿一把花追到醫院去看她」。我從這裏看到了非常殘酷的一幕。
還有,一個像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被人起外號叫沙袋,受嚴重欺負,遭拳打腳踢。他來跟我說這件事,卻不說自己被欺負了。他說「老師,我班上有一個孩子被人起了‘沙袋’的外號,遭到了欺負」,反反復復說了好多次。我後來才發現他說的原來是他自己。
他這樣反復跟我說這件事,其實並不是期待我出面幫助解決問題,而只是為了找到一點安慰。那時候我一直比較註意聽這些情況。不過後來自己工作過忙,就顧不上了,孩子們也不再來跟我說了,以至於後來完全聽不到了。之後,我雖然辭去了校外輔導培訓教師的工作,當時的事還是給我留下了極為寶貴的體驗。這些體驗讓我有機會,從一個輔導培訓班教師的角度對霸淩有了一些觀察。

從受尊敬
到被排除的轉校生
赤阪:從70年代開始到80年代,我碰巧在做有關異人(stranger)方面的研究。當時對我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從一個團體裏被排除出來的人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有什麽內容,起什麽作用這些問題。我將霸淩問題的研究看成異人論延長線上的研究。
河合:請您就異人論的研究向大家作一些說明。
赤阪:傳統上對異人有「流浪及定居雙重性格」的定義。也就是說,假設一個團體具有自己的秩序,就有可能存在與這個團體格格不入的人。或當一個與這個團體持有不同行為準則的「來訪者」來訪時,則會產生各種摩擦。我是從異人論的觀點出發,來討論這些現象的。
霸淩問題在表面上是欺負與被欺負對峙的情景,實際上這並非僅僅是孩子們之間小規模的摩擦。它象征性地表現了一個團體或一種秩序所處的狀況。從某種意義上說,霸淩問題是由種種猜測和偏見引起的。我在自己的研究裏曾把異人分成若幹類。在這些類比中,我總感覺霸淩問題似乎與邊緣人(marginal man)相關。
河合:說到異人,與霸淩恰恰相反。如在民間傳說中經常見到「稀客」來訪的故事,比如弘法大師來訪那樣的故事。這類故事多具有正面意義。但今天的霸淩卻只有負面作用。常常是整個團體一同開足馬力去排除這個存在。

【孩子與惡】,作者: [日]河合隼雄,譯者: 李靜,出版社: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時間: 2015年4月。
然而,這裏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雖然受欺負的孩子被視為異人,但他們其實並非異人,而原本是團體中的一員。所以,他們受欺負的原因並非在於新來乍到,而是本來屬於這個團體中的人突然遭到了欺負。
赤阪:我覺得這一點確實很重要。我們觀察民間故事裏透過「外來客」所表現的信仰就可以發現,他們看上去像乞丐一樣骯臟,實際上同時具有弘法大師那樣神聖性的雙重性格。所以,其中存在著一種相互矛盾的構造原理。比如不招待乞丐就要遭報應,畏懼和敬仰往往兼而有之重疊在一起出現。可在現代,至少在霸淩現象中並非如此。
我對轉校生問題很有興趣,不知在這裏是否能成為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
河合:從某種意義上說轉校生是異人。
赤阪:在少年少女漫畫中,轉校生擔當著很重要的角色。比較多的時候,轉校生在漫畫故事的世界裏會起著拯救團體,或是引領這個團體走向某個新方向那樣的積極作用。所以,他們經常會成為故事的主角。比如【明日之丈】(或譯作【小拳王】)的少年主人公,很顯然是個突然從外地流浪而來的孩子。後來,因為幹了壞事被送進少年犯管教所。在少年犯管教所裏,他接觸到了拳擊,最後登上了世界拳壇頂峰。雖然他的出身、來歷被寫得比較曖昧,可在當今枯燥的學校環境裏,類似這種烏鴉變鳳凰的事情已經很少見了。
在我們的少年時代,轉校生還會像【風之又三郎】裏所描寫的那樣,帶有很強的異國情調,大家會圍過去問東問西,互送禮物,然後互相漸漸熟悉起來。那時候轉校生有著不可思議的魅力,但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同時也會被欺負。
河合:正如你剛才說的,他們具有兩重性。
赤阪:可是,現在的轉校生很難像從前那樣,順利地被團體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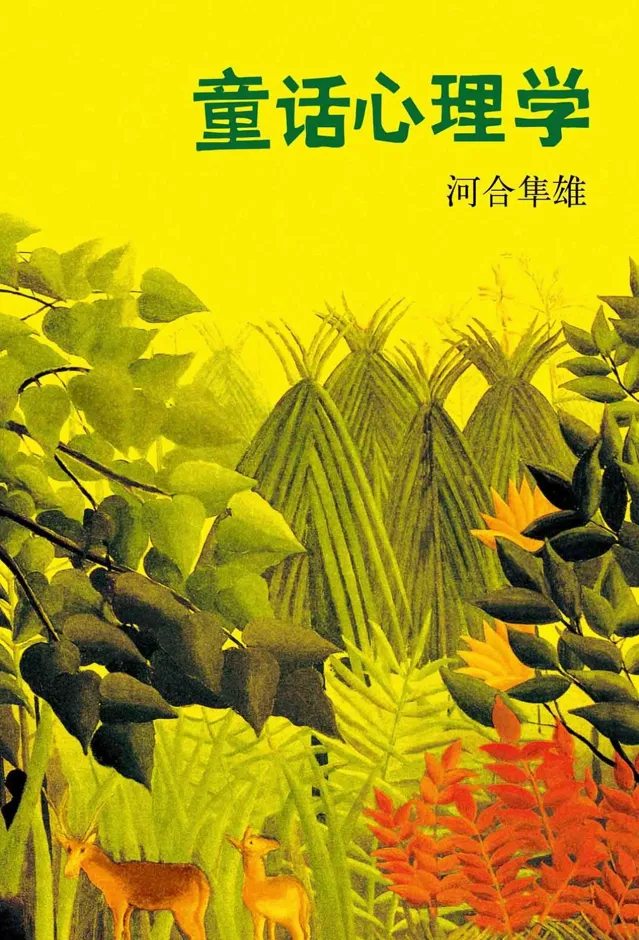
【童話心理學】,作者: [日]河合隼雄,譯者: 趙仲明,出品方: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時間: 2015年5月。
河合:的確很難。轉校生多數要遭到欺負。特別是海外歸國人員的子女,會受到特別惡劣的欺負。其中也有人順利融入新團體,並受大家喜愛,但為數極少。
比如,從海外回來的孩子當然能說一口地道的英語,這樣老師就不開心,因為老師說的是日本式的英語。孩子漂亮的英語一出口,就讓老師氣不打一處來。我說的是一件真實發生的事情。老師對孩子說「我們這兒是教日本英語的地方」(笑),結果這孩子徹底變成了被霸淩的物件。
也就是說,老師的一句話就使一邊形成一個日式英語集團,而歸國人員子女這邊則被大家嘲笑,被起上「怪日本人」的外號。如果換一種方式,比如老師說「你的發音真好,大家應該模仿這位同學的發音」的話,情況就會完全不同。

【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劇照。
赤阪:我在自己的「異人論」研究裏,把異人分為六種型別。第一種是在集團邊緣擦邊而過的流浪人,第二種是從其他集團過來的來訪者,第三種是暫時的逗留者,第四種是被排擠到集團邊緣地區的邊緣人,第五種是回鄉者,第六種是蠻人,這類人被視為野蠻人,常遭到非常嚴重的歧視。
我認為回鄉者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就現在海外歸國人員子女問題來說,具有雙語能力及多種語言能力,這成為他們受欺負的主要原因。
河合:一不小心打破這些分類,就有可能把所有的人都一起並入蠻人一類。不做選擇分類,而一股腦地認為「那個做法奇怪」「這家夥不行」,來勢洶洶。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

均一化與尋求差異
河合:剛才說起可以把異人分為幾類,如果人們心中對周圍的人有類似的區分觀念,那麽即使是比較怪異的、滑稽的或較軟弱的孩子,也會得到相應的評價和認可。現在人們心裏的這種區分卻正在消失,這是霸淩方面的一大問題。
赤阪:您認為這種區分真的消失了嗎?
河合:是的。在我看來,我們對「好孩子」的定義太單一了。如果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好孩子,那麽也就可以允許有各種型別的「壞孩子」。現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大家明確認為只要會學習,成績好就是好孩子。這樣,就很難接受其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各種型別的孩子。
赤阪:我隱約感覺到,均一化的觀點對不同存在非常缺乏寬容性。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學校是一個受到高度均一化管理的團體,完全失去了與不同存在交流的場所和渠道。同學之間即使是微小的區別,也能被視作天壤之別。我感覺正是這個原因,才會出現那種把一些本來只有微小區別的人,硬變成了整個團體不能容忍的蠻人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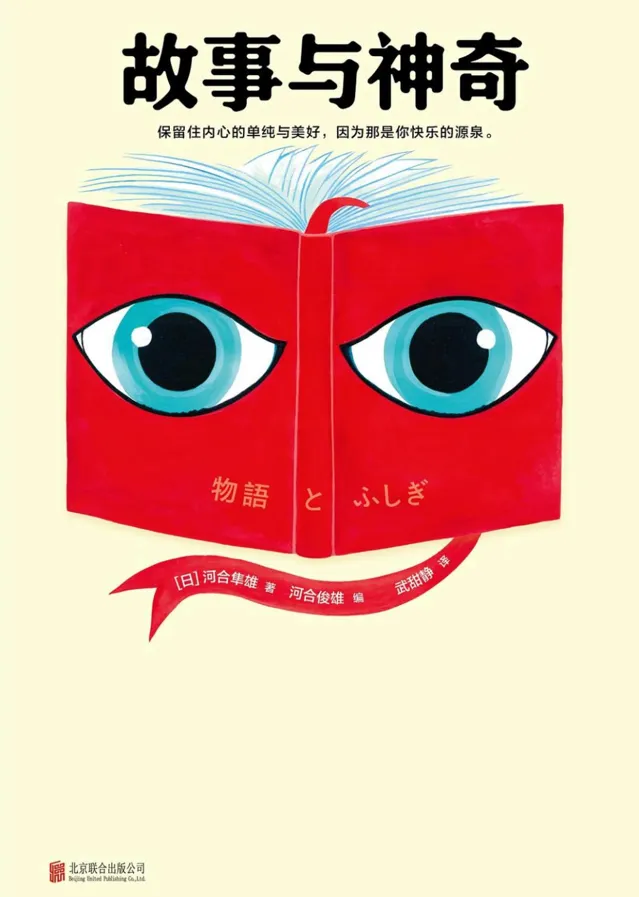
【故事與神奇】,作者: [日] 河合隼雄 [日]河合俊雄,譯者: 武甜靜,出版社: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時間: 2018年8月。
河合:由於均一化是強迫形成的,所以每個人都會承受巨大壓力。本來每個人應該是不同的,可是全被壓制成同等均一的了。因此,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些怨氣。這時候,如果團體內冒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則會千夫所指。
赤阪:是啊,周圍會出現不可想象的巨大敵意。比如,如果大家沒在看同一部電視劇,聊天就持續不下去那種情況。為什麽大家得絕對一致呢,被迫感實在太強烈了。
河合:大家做著同樣的事情,心裏卻一直都有一些不滿和無奈。憋屈在內的那股氣要發出來時,就得有一個人承受下來。剛才提到了異人的分類,如果大家能認識到人本來是千姿百態的,哪怕只是父母和教師認識到人多樣化的美,也會有很大幫助。這方面太欠缺了。現在說到好孩子,清清楚楚的只有一種模式而已。
赤阪:惡果是即使是教科書般的好孩子,有時也會突然一變,而成為被欺負的物件。
河合:成績太好也會引起別人不滿。本來完全不會成為被欺負物件的孩子,也會由於一些偶然因素發生逆轉。

【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劇照。
赤阪:物極必反,過猶不及。
河合:比如,模仿好學生說話腔調那樣的調侃行為。
赤阪:當隔著一定距離觀察孩子們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集體中太孤僻的孩子會受欺負,太陽光的孩子,過於引人註目了也會受欺負。孩子們得一邊細心環顧周圍,一邊不斷調整其間的平衡,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與別人之間的偏差值調節在五十上下。現在的孩子們都這麽磨煉著自己的處事方法。如果對這些能看開一些,勇敢面對,自己就會輕松很多。
河合:我認為剛才提到的這些,實際上是現代霸淩問題的本質。當這些現象的底流部份與青春期問題重疊時,便會引起強烈震動。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霸淩與拒學】一書。原文作者:[日]河合隼雄;編輯:王銘博;導語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合訂本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