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高盛元老師的新作【詩的味道】問世。該書由果麥文化出品,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獲得戴建業、駱玉明、梁永安等多位學者推薦,目前豆瓣評分為8.5分。
高盛元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長期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解讀與傳播,既是青年作家,也是B站知名UP主,被譽為「夢想中的語文老師」。【詩的味道】是高盛元的第二部作品,與【昨夜星辰】類似,該書主體內容立足於高老師的B站詩詞課講義,深入淺出地對十位唐宋詩人的文學作品加以剖析,作者豐沛的情感與廣博的學識在文字中彰顯無遺。對古典詩歌初學者而言,【詩的味道】不失為陶冶詩情的上佳選擇。
12月16日,【詩的味道】新書分享會在鐘書閣上海徐匯店舉行。本次分享會邀請高盛元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就「詩詞的讀法」這一主題展開對談。本文整理自兩位嘉賓的對談內容,經對談雙方及活動主辦方審定釋出。

講座現場(圖片由鐘書閣提供)
選詩:凸顯個人色彩濃烈的切面
駱玉明: 大家讀這個書就知道有詩意的人是怎麽樣去寫書的。談詩最大的問題是有的人談得頭頭是道,但是這個人身上沒有詩的味道。沒有詩的味道也能談很多,比如談格律、談平仄、談用典、談詩歌的流派等等。他可以談很多詩的知識,但是談的都不是詩本身。
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書,高老師選的人物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選擇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我想個人喜歡是第一條的。
高盛元: 在我們的認知裏面,宋代詞的地位要高一些,但如果大家去讀宋代的詩,我覺得它的成就並不在詞之下,只是因為很多很復雜的原因,我們宋詩讀得比較少。市面上好像也沒有比較好的宋詩的選本在賣,唯一賣得比較多的就是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大家可能就對宋詩比較陌生一些。按照我的理想,談完了唐詩之後應該把宋代的詩和詞一起談,但是又考慮到大家的接受情況,所以選了一些大家比較熟悉的,同時也是我比較喜歡的詩人,其實還是有蠻強的個人色彩的。
比方說李白,我選了【少年行·其二】,這首詩我很喜歡。【少年行】不是李白自己獨創的題目,它是一個樂府的常見題目。當然,任何一個作家一定是處在一個很大的文本網路上的,不可能完全沒有前人的傳統,沒有借鑒任何東西。很多詩人在年輕時寫過【少年行】,之後心態就變了,但是李白寫的【少年行·其二】,就是他整個人生的寫照。我希望用現代人生活的視角去給李白一個概括,用「少年感」三個字來形容他的詩歌。暑假的時候大家可能看過【長安三萬裏】,帶火了一句詩,就是他的「輕舟已過萬重山」,我覺得那個特別能體現李白身上的少年感。他到最後還是這樣:只要人生的枷鎖、困境從我身上解除了,我就還可以很瀟灑、很輕松地揮揮手,再見。這就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長安三萬裏】劇照
回來看【少年行·其二】這首詩歌,是他年輕的時候寫的,這種少年感一直貫穿到他的老年。「五陵年少金市東」,讀過【琵琶行】的朋友都知道「五陵年少爭纏頭」,形容那些很紈絝的富家子弟,他們在到處遊逛,無所事事,因為有錢嘛。「銀鞍白馬度春風」,我覺得這個意象特別漂亮,「銀鞍白馬」,很「李白」的一個意象。這四個字不一定是李白的獨創,魏晉的時候很多人也會寫到「白馬」,也會寫到「銀鞍」,但是出現在李白筆下,它就特別「李白」,你覺得這就應該是屬於他的句子。每一個詩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可能並不是他主動地去創造一些詩歌,而是很多的句子來找上他。他寫【俠客行】,「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你看這就是李白的感覺,就是一個少年的俠客,穿梭在春風當中。
李白的詩歌裏面充滿了春天的感覺。每一個詩人有他從屬的季節,李白可能就是春天的詩人,他永遠充滿希望。中國古代有一個傳統,很多詩人看到落花就會不自覺地有一種悲傷。我記得最早聽駱老師講【詩經】裏【萚兮】那首詩歌,其實從【詩經】的時候開始,就有落葉、落花的意象,它和生命隕落的悲哀是聯系在一起的。到唐代,像杜甫寫「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李煜寫「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包括到曹雪芹的【紅樓夢】裏面,林黛玉寫的一首很有名的詩叫【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這種傳統當代也仍然在延續,比方說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小說家叫金宇澄,他寫得非常棒的一部小說【繁花】,裏面寫到很多女性,到最後經過時代的風流雲散,就像繁花一樣隕落了。落花是跟悲哀聯系在一起的,可是在李白的詩裏面落花跟悲哀毫無關系。他說「落花踏盡遊何處」,花開的時候,我來看花開的樣子,花落了之後,我再換一個地方去——「笑入胡姬酒肆中」,去酒吧裏面繼續去開心。他的詩裏面有一種歡樂,而這種歡樂感是一直延續下去的,沒有很悲哀的情緒在。我選這首詩的原因就是它很能代表李白的個性,有一種「少年感」。
在杜甫的篇幅裏面,我凸顯的就是另外的東西了,是他對於人世的一種關註,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遼闊」。大家如果對鉆石有了解的話,會發現鉆石的價值是根據切面的多少來衡量的,如果一個鉆石能夠切出更多的面,它的光澤就更亮一些,價值就更高一些。我覺得杜甫可能就是整個唐詩歷史上切面最多的鉆石,在他身上其實切出了很多不同的面,能夠折射出不同的光來,他會關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杜甫寫得最好的一首詩歌,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對我來說,永遠是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因為他站到一個高度上。大部份人的想法是「什麽時候我能有一棟自己的房子」,可是杜甫他說「安得廣廈千萬間」,什麽時候像我一樣的普通人都能夠住上很好的房子?「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讀到最後我是特別感動的,因為他想象千萬間的廣廈,他想象所有的讀書人都能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個屋子是不被外面的風雨所能摧毀的。可是在千萬間的屋子裏面,他沒有給自己留下一間。他說「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如果你們都有自己的房子住,即便是我在這個破屋子裏面就這樣凍死了,我也滿足。這樣的一種遼闊感,一種對人世的關註,一種對他者的關註,恰恰是今天的很多文學作品裏面稀缺的。很多當代的作家和小說,其實在慢慢退回到一個非常個人的、非常自我的、非常私人化的情境裏面去。批評家蘇珊·桑塔格講過一句話:「所謂作家就是對這個世界充滿關註的人。」對這個世間的一點點風吹草動,作家都能夠有所感,而不應該僅僅停留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我舉李白和杜甫這兩個例子,就是說我不想面面俱到地談他們的成就,我會突出他們身上的一個面向,比方說對李白突出他的「少年感」,杜甫突出他的「遼闊」,李煜我想突出那種「夢幻感」。舉一個例子,有兩個作家和李煜蠻像,一個是張岱,一個是曹雪芹,他們好像生活經歷都差不多,就是一半一半,前半生繁華明麗,後半生意識到這種東西過眼皆空,前半生可能是「紅樓」,後半生就變成「夢」了。所以你看李煜,他寫「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那是他前半生的感覺,張岱會寫【陶庵夢憶】也是一種夢,曹雪芹寫【紅樓夢】,其實也是一種追憶。
駱玉明: 假定我去寫一本提供給普通讀者的談詩的書,那麽我可能就會回避篇幅太長的,怕讀者產生疲倦感,比如【琵琶行】;用典太多的、太艱深的,比如辛棄疾;詩意比較晦澀的,比如李商隱,要選只會選一些字面比較淺的,比如【無題】;最後,一些詩意過於沈重的,比如杜甫的一些詩。這四個都去掉,然後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唐詩宋詞在這本書裏顯示的面貌是不完整的,是浮面的。而高老師選擇講述唐詩宋詞裏面不應該被回避的部份,講得親切愉快,同時也很準確,抓住了一個詩人的特點。我以前看畢加索的畫的時候,覺得畢加索的東西很怪誕,但後來看畢加索的速寫,大吃一驚,就這樣「唰——」一兩根線條,把一個活動的人體表現得非常準確、生動、親切,那真是大師。把一個很復雜的、很不容易表達的東西,表達得很精確,而且閱讀的過程很愉悅,這是不容易的。
談詞:言之有盡,解析空間狹窄
高盛元: 我有一個困惑要向駱老師來請教。其實有兩個人本來想寫進去的,稿子也寫好了,一個是柳永,一個是李清照,但是我寫完了之後就覺得沒有必要——不是說這兩個人沒有必要,而是我寫的內容沒有必要,只是停留在對字句的解釋,寫得很無力。對於詞的解讀,應該怎麽樣去解讀它?或者說,如何能夠看到裏面更深的情感世界?
駱玉明: 這個話題一下子要抓住也比較難。你講到李清照和柳永的詞,它確實相對來說比較難寫,因為詞和詩有個不同,詞是一個情緒展開過程,當中的躍動性比較低,詞人把自己的情緒融入在語言的流脈和節奏裏面,躍動性就比較小,象征性的東西比較少,相對來說節奏空間就沒有那麽大。特別是柳永的詞,主要體會的是語言節奏流動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你自己能夠體會和感受,但是用你的方法去解析它的手段卻沒找到,是這樣的一個問題。那麽換一個方向來說,比如說蘇東坡的詞,空間會大一點,因為在東坡詞裏面沒有說盡的東西多一點,比如「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裏面有很大的躍動,讀者的參與就會比較多,於是乎你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和讀者交流。
解析古詩詞的書,實際上有三者間的關系。一個是作者,在什麽條件下使用了什麽手段,表達了什麽樣的生活經驗和情感經驗,如何用好的語言去體現出來。第二個是解析者,就像是我和高老師,我們解析它的時候並不是能夠保證我們所理解的就是詩人想要表達的,因為詩詞有它的不確定性和空間,還有一些不是語言能表達的東西。我們現在討論的題目叫「詩的味道」,它不是語言能夠表達的東西,它包容在詩歌的形式裏,並不體現在字面上。還有一個是物件,介紹這些東西的時候還要面對物件,那麽去解析一首詩的時候,有時會發現除了詩人所寫的那些東西,能說的很少,不能告訴讀者什麽東西。像李清照或者柳永的一些詞,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似乎就是這些了,一些獨特的、能讓我們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情感經驗坐落進去結合的東西,可能沒有找到——不是說沒有,只是沒有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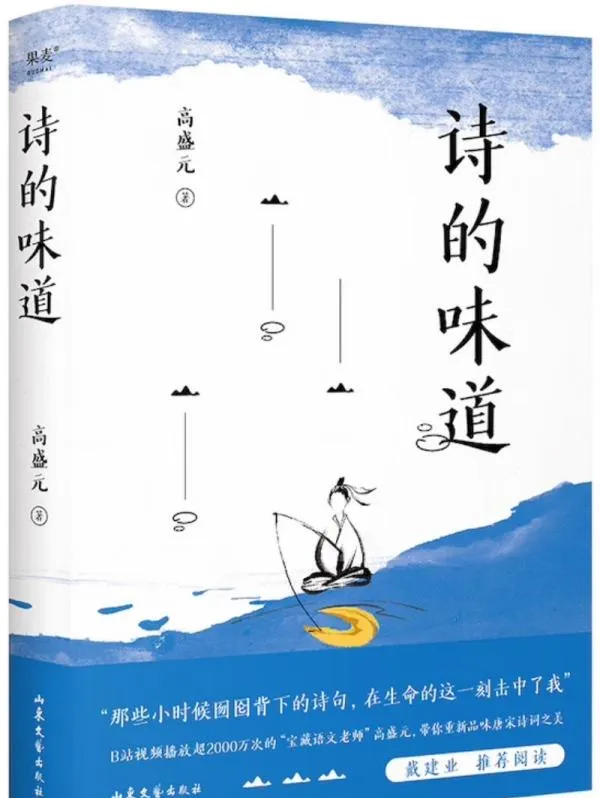
【詩的味道】,高盛元/著,山東文藝出版社·果麥文化,2023年10月版
讀詩:詩的「味道」與意義
駱玉明: 詩的味道是一個非常難以捕捉的東西,它牽涉到讓你去體會一個詩人的生命感受。剛剛高老師講到李白,我有一次上課的時候,在黑板上寫一個跟李白相似的句子,不是古詩,我的第一句寫:高天上漂浮著一些白雲,然後再寫第二句:悠閑猶如浪子的愛情。說李白很輕松,沒有掛礙,永遠不會因生活的壓迫而變得陰塞沈悶。包括他跟朋友在一起相會告別的詩,別人寫的都有很大的傷感的成分,他卻沒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這很輕快的;「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全詩都是非常輕快的。他是一個非常自由自在的、輕快的生命,這就是高老師說的「少年感」。但是這樣的一種味道,你如何在詩歌的結構裏面找到一種方法去塑造?如何很真誠地捕捉詩的味道,並且把它在語言上表達出來?
李白有一句「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別人都不敢這麽寫,只有李白敢這麽寫,為什麽?他很自由,他很相信自己,他覺得這個時候他要這麽說,他就這麽說了。如果單獨說「一杯一杯復一杯」,它不像個詩啊,不停地一杯又一杯,就像兩個酒鬼在不停地喝酒;「兩人對酌山花開」,也不是很像詩,只是想交代一件事情。但是「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詩就出來了,一種快樂的、熱烈的生命的狀態,毫無掛礙的,自由自在的,什麽東西都擋不住他。當然,如果光到這裏,它的味道還不充分,再往下讀「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要醉倒了,你別跟我啰嗦了,我現在沒工夫跟你說話,我要睡覺了。一切世間的拘束,一切世間的規則,在一個詩人那裏是不存在的。這樣就把前面的那種熱烈、那種自在給推上去了。句和句之間的關系是怎樣互相推動的?所謂「詩味」怎麽呈現出來?這是最難做的。一個句子看起來很平淡,但是另外一個句子配上去,它的味道就會出來。
高盛元: 詩意的問題,其實在李白的作品裏面體現得特別明顯。我對他的看法是:天才就是這樣的。杜甫和他就完全不一樣,杜甫是一個後天很努力的學生,一個很努力地、不斷雕琢自己詩歌技藝的詩人。但李白,他好像很多東西就是隨口來的。他有很多的詩,前面幾句話就是在那「瞎說」,就好像運動員要熱身,熱身完了之後他蹭一下就飛出去了,一下子就跑到終點,讓所有人感到很吃驚。比方說【贈汪倫】,他前面說:「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一直到這個時候,我覺得我都能寫,沒有任何的難度。但是到最後「不及汪倫送我情」,你會發現這句就寫不了,一下子把水和情感聯系起來了,完全是一個很天才式的寫法。
之前有朋友問我,讀詩到底有什麽意義?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換一個方式來回答。今天會不會有人問:吃飯有什麽意義?可能沒有人會問這麽愚蠢的問題,因為這是我們的共識,你不吃飯就死掉了,沒有正常的營養去供給它了。可是為什麽問讀詩有什麽意義?或者說讀文學、讀書、文科有什麽意義?因為好多人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存在著,一方面是因為有一個外在的自我,一個物質性的存在,但是其實裏面還有一個精神性的自我。可是在很多的時候,這個精神性的自我被我們遺忘了。
林庚先生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到底什麽是詩人?詩人就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睜大了眼睛去發現,去好奇地觀看這個世界的人,就是詩人。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永遠保持著對世界的好奇。這是詩人觀察這個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們曾經觀察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們曾經好像都是一個詩人。我們曾經有一個非常內在的精神性的自我,他那麽活潑地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可是隨著我們的長大,隨著我們的社會經驗一點一點變得更加豐富,那個精神性的自我被磨損得越來越小,我們就變得越來越麻木,對這個世界不再有感受,也不會去觀察這周圍的、自然的東西了。我覺得這是我們喪失詩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之前在網上看到一個克服焦慮的辦法,就是到公園裏面去抱一抱樹。有一天我就去嘗試了一下,我到公園裏面找了一棵能抱得比較合適的大樹,然後就抱著,閉上眼睛去感受自然世界帶給我的力量。等到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我的旁邊聚集了很多的人,他們非常奇怪地在觀察我。但是在那一刻我是感受到有力量的。我們和古人的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在於這個世界的一花一草落下的時候,我們不會去觀察它,也不會有什麽感觸。對王維來說,「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這會觸動到他的情感。可是今天我們看到一朵花落了就落了,跟我有什麽關系?我還有我的工作要做,我還有我的KPI沒有完成,我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考慮,所以我們就跟自然世界完全地區隔開了。
孔子說要「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我們今天已經不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看到外面的樹,看到外面的草其實已經辨別不出來了,只會有一個總體的認識,覺得這個東西叫「tree」,那個東西叫「flower」,但是它具體是什麽?在古人的世界裏面,每一個都是不一樣的。桃花是桃花,杏花是杏花。他們在辨認這個世界的過程當中,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們迷失的原因很多時候就在於對外在的世界已經不清楚了,處在一個很懸浮的狀態上。
回過頭來,那個內在的精神自我是需要營養的,需要餵養的,這就是讀詩或者說是讀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意義所在。當曾經的那個小孩,他慢慢地不見了,他慢慢地麻木了,他慢慢地對這個世界沒有感覺了之後,可能需要一兩句詩把他喚醒。

李白畫像
駱玉明: 這是很有意思的話題。讀詩的時候,我們在讀什麽?這個世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人和人的欲望互相沖突。我們會計較,會計算,因為要考慮我們的生存,考慮我們的利益,考慮我們的榮耀,考慮我們的成功。人為什麽會精明呢?因為他越來越會計算。在這個過程裏面,我們會越來越瑣碎,或者說一個完整的生命就會被剪碎。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朋友晚上想今天一天幹了什麽?跟誰爭吵了?我上哪裏去逛超市了?我買了什麽便宜的東西了?我報復了誰?或者說我在誰那裏受了氣?一點一點去把它寫下來,你會發現你的生命真的剪得很碎很碎。當生命剪得很碎很碎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起另外的一些東西,就是人生命裏面還有其他的追求,關於永恒,關於無限,比如說天地,比如說道家所講的道,大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或者說佛家所講的心境覺悟。這都是講一個永恒的、超越的力量是否存在?或者它以什麽方式存在?那麽這種抽象的東西,它體現在我們的生活裏是什麽?比如說高老師他就抱一棵大樹,比如陶淵明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條件是「心遠」,要怎麽遠?跟那些世俗的利益和榮耀遠。當你跟世俗的利益和榮耀遠的時候,你會跟另外一個東西近,跟什麽東西近呢?「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你會和大自然近。大自然是我們的生命的本源,而且大自然不僅僅是山、雲、花這些東西,大自然還是那個絕對的力量——大道——的一個呈現方式,永恒之物就是呈現在大自然之中的。所以你去看花看草看樹的時候,其實你在試圖去接近一個永恒的力量。
我們的生命其實有無限豐富的可能性,但是我們在具體的生活環境、具體的歷史條件、具體的利益中的時候,它變得越來越收縮,最後會收縮成一條蟲子。人有的時候活得像一條蟲子,就是在咬食那一葉。我不是說人不要在現實關系當中生活,人不要去爭取物質利益——有人拿本書叫我來題字,我就給他題「多多賺錢,好好生活」——賺錢很重要,沒錢你怎麽過?但是你不要除了「多多賺錢」,下面再寫「多多賺錢」,再寫「多多賺錢」,那生活沒有了。多多賺錢的目的是什麽?是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是什麽?是記得我們的生命有永恒和完美的可能性。
如果把這些問題變成哲學問題,比如說人為什麽要設定一個「絕對者」?康德說上帝是不可證明的,它是人的一種設定。大道也是一種設定。設定這個東西就是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有限,用一個無限來對照我們的有限,讓我們知道我們是生活在有限當中,去產生一種渴望,就是打破我們的有限,使我們的生命展開。這當然可以做哲理的討論,但是它的感性的力量就是來自於詩,它會時時刻刻讓我們知道所面對的無限。比如李白,有一位老師寫過一篇文章,說李白就是小流氓,李白很庸俗,李白拍馬屁。我說這些也都成立。魏顥在【李翰林集序】裏面說李白「少任俠,手刃數人」,他親手殺死過幾個人。這件事情我始終沒有辦法弄明白。為什麽呢?魏顥是追星族,是李白的「鐵粉」,追了很久追到李白,那麽這些話他一定是從李白那裏聽來的,因為他是直接關系。但是這兩個人都是酒徒,一個喝醉酒的人、愛說大話的人,跟另外一個喝醉酒、愛說大話的人說:哎我小時候殺過好幾個人呢!可信嗎?這是個歷史遺案。但是說的時候他肯定很爽,因為你看「少任俠」,這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從來沒打過架就很丟臉,談女朋友都不好意思談的。回到我們的話題,李白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是顯著的拍馬屁的話,李白拍起馬屁和自我誇耀起來,那是昏天黑地的。但是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李白的詩歌給我們創造了一個精神空間,這個精神空間讓我們想起人的永恒、無限、完美和自由,那種對生命的自由的渴望,用非常清爽的、爽快的語言表達出來。那我們可以喚醒自己呀。你就在這些詩裏知道,我原來不是一個毛毛蟲,不是一天到晚啃食那些葉子,啃食那些錢就能活下去的。詩歌會給我們這樣的一種力量。
比如說杜甫跟李白是不一樣的,無論從詩歌的語言、詩歌的形式,李白非常喜歡寫那種超放的,比如說【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起伏很大,非常自由的詩。杜甫最擅長的是律詩,像【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但是他們仍然有同樣的東西,就是對生命的、對世界的視察。我現在七十多歲了,有時候晚上讀杜甫的詩,仍然會眼淚流下來。比如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寫驪山裏面唐明皇和楊貴妃正在花天酒地,縱情享樂,處在一種喧囂浮華的快樂之中,杜甫在往家趕。那裏面有一句,天很冷衣帶斷了,手凍得僵直,打結打不起來,回到家裏發現小孩子餓死了。然後他會想到什麽?他會想到我這個人是有特殊待遇的,雖然是很小的特權,他可以不要服役,可以不要交稅,他起碼是一個小小的官員,而那些比他更差的人,怎麽樣活過這個冬天?於是就有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的句子。這表達什麽呢?表達生命的宏圖、遼闊,不管世界把他壓縮成什麽樣子,這個世界不能夠把我們壓縮成一個渺小的、可笑的、荒誕的東西。這就是詩,詩是生命的真誠,是對於完美的生命的渴望。一個讀詩的人會相信自己,我們不會那麽猥瑣地活在世界上。在我看來詩的意義就在這樣的地方。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