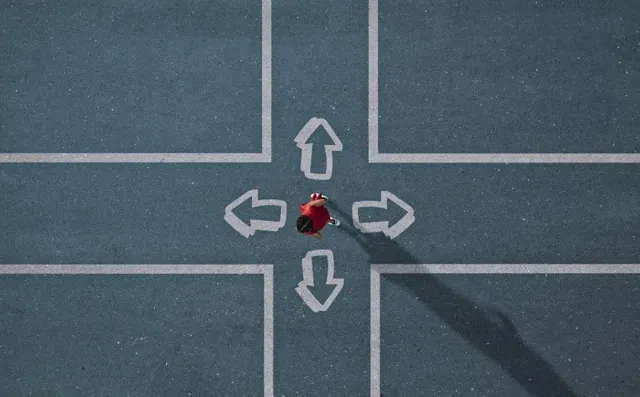
對「小鎮做題家」的研究,來自謝愛磊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 那是2013年,他發現,那段時間,公眾對於農村學子上名校的討論往往止步於一些極端事件,有轟動性的比如馬加爵故意殺人案,還有一些名校農村學子,因為沈迷遊戲直接輟學。 在這些新聞裏,農村學生學業跟不上,還有嚴重的心理問題。 但幾年過去,某天,謝愛磊突然發現,從農村考入名校的學生們又有了一個新名字,叫「小鎮做題家」。 他覺得奇怪,怎麽一開始說他們不會做題、不會學習,後來又變成了擅長做題,甚至「只會做題」?
如今,謝愛磊是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曾經,他也是一個「小鎮做題家」,出生於安徽的一個村子,中考時第一次進城,大學來到上海,而後去了香港、英國劍橋,「做題」給他開啟了廣袤的空間,卻也給了他很多困惑。
開始對農村學子的系統研究後,在上海、廣州、武漢和南京,他分別挑選出了4所「雙一流」高校,向2000名學生發放了調查問卷,並持續追蹤了其中約60名農村籍學生。從2014年開始,5年時間,謝愛磊做了三輪訪談,追蹤這些學生大一、大三以及畢業後的生活狀況。
他的研究數據表明,農村籍學生學業成績並不顯著低於城市學生,新聞中出現的刻板退學情況,只是極端個例。
更大的問題出現在融入名校這個過程中:剛開學不敢加入社團,低年級沒能出校門逛逛公園、去電影院,到了畢業前夕,就業方向尚不明晰。這種沒有準備和提前計劃的局促感充斥在農村學生大學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會後。
這讓謝愛磊想到自己的求學之路。2000年,他考入華東師範大學,來到上海。對他來說,學業壓力並非那麽難以應對,但全新的世界讓他感到壓力:他第一次知道羽球場地中間還有一道網子,男生可以幫女生擰開瓶蓋。他意識到大學和城市有著不同於老家的規則,但這個規則是什麽,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這些晚他十幾年進入高校的農村學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樣的茫然。他也發現,這並非個體的問題,而是一個人群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謝愛磊把訪談到的故事和研究寫成了一本書,今年五月,【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出版。這不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有人質疑他,書裏的內容少了「理論雄心」,語氣過於通俗,大部份篇幅也是引語轉述。在和我的對話中,謝愛磊沒有回避這些評價。定下這個標題,他曾經猶豫過,但他也更希望這本書是面向公眾的寫作。在「小鎮做題家」標簽的背後,謝愛磊想要傳達的,是一族群體的力量,能讓尚處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輕人們感受到自己並不孤獨。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環境也給人比較和反思的空間,而這正蘊含著改變的力量。
生活在一個競爭為主導議題的社會中,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要或多或少經歷「做題」和「探索」的拉扯。相比於傳統的「寒門出貴子」式勵誌故事,當代「小鎮做題家」們在融入現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擾,其實是這個時代生命流動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幹擾,都不能被另一個掩蓋掉。
以下根據謝愛磊的講述與【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整理而成:
文| 李雨凝
編輯| 槐楊
圖| (除特殊標註外)受訪者提供
1
2013年,我正式開始做關於農村學生的系統研究。
在農村學生擴招計劃出台的頭幾年,公共視野裏流傳出農村學生在大學學習跟不上、心理問題也多的新聞。這時候,農村籍的學生們就成了極端事件裏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師們也會覺得這群孩子就是這樣。我就想,我也是農村出身,還有身邊很多同樣農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間地頭跑和玩的,他們的面孔在我的記憶裏又鮮活又明亮,我們和其他城裏的孩子又有什麽不同呢?
那之前的幾年,一些學者已經開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範圍,大部份都局限在高考這一環——入學這種開端的確會比較吸引人關註,但對於過程和結果,還有透過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幫助農村學生實作社會流動,少有人註意到。
我做過大學裏的檔案分析和研究,數據顯示農村學生的學業困難並不顯著。那問題在哪兒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樣,我最初也假設這些學生在經濟上會面臨較大的壓力。最開始的調查問卷要花費一個小時才能填寫完,我還衡量了一下報酬,最終定下了50塊——我猜想,可能農村來的孩子們會因為經濟原因更積極一些。
但收上來問卷之後,我發現,其實在這個時代能考入名牌大學的農村籍學生,已經是原生的中等家庭。一些來自南方的孩子,家族還會給他們一筆考上好大學的獎金。他們中的大部份人都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學習用的書桌,家裏也有電腦、互聯網和洗衣機,他們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於農村同齡人——父親們79%都接受過中學以上的教育。當然,在城市,這個比例是接近97%。
那困擾他們的又是什麽呢?有一次做訪談,我和一位名叫吳潔的學生在學校旁邊的奶茶店見面,剛開始我問她,你的大一過得怎麽樣?這只是一個破冰的問題,但她沈默了很久,眼淚也跟著流了下來。理智告訴我這是一個能問出更多回答的機會,但作為一個同樣從農村走出來的人,我在情感上選擇了支持她。就這樣,第一次的對話很快結束了。
其實,相比於農村的同齡人,吳潔已經擁有了一個相對不錯的人生座標。在我的訪談中,一些學生會表示,自己說不清楚家裏有幾畝地,因為「家裏人從來沒有讓他下過地」。他們的父母願意在教育上花費時間和精力,一些家庭為了實作讓下一代「跳出農門」,甚至會出現全家托舉的情況:母親去縣城陪讀,家裏的其他人則全部投入務農或者打工。因此,他們中的多數都來自原生的重點高中,這也是進入精英大學的先決條件之一。
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學為節點來看,「跳出農門」的勵誌故事顯然成立。既然學習上沒有大的問題,經濟上的困難也不大,吳潔的眼淚又來自於哪裏?談到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的區別時,她說,是「我永遠也不會變成他們」。訪談中,我發現,一些學生在面對這樣的訪談時局促不安,有些會極力隱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說漏了嘴,說出了方言。
在後來很多訪談裏,農村籍學生們都會談起這種初入名校的不適感。在很多農村考入名校的學生看來,大學是一個「人情」變冷的地方,老師不怎麽管,上課時PPT是主力,「上完課就離開了」,同學們也在各幹各的。一位學生曾在訪談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學一起出門,自己騎著自由車載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邊的觀念」,同學應該理所應然等他一下,但是,同學很自然地先上了車。這位同學感到郁悶,他最後把這件事歸結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與鄉村地區的一種觀念交換。」
在第一次見面草草收尾後,我和吳潔在學校的咖啡館又約了第二次。剛開始,她為上一次的「失態」向我道歉,但等我們開始交談後,她又開始默默流淚。她告訴我,這一年的大學生活中,她沒有太多變化,因為心思依舊還是放在學業上。相比於學習,她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擾:「在與同學的相處與聚會中,總有難以名狀的隔膜。 」
還有一個學生,反復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來」「朋友圈很小」,覺得自己的大學「不完整」。這些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大一參加各型別學生組織的比例和大二成為學生幹部的比例都明顯低於城市籍學生;在學生會等半官方學生組織的參與方面,則低於城市籍學生14個百分點。
這種無法適應、無法融入的感覺不會大到沒辦法繼續生活,也許只是比別人每天多在圖書館呆一會兒、少去幾個社團,或者多幾頓一個人在食堂吃的飯。但也許這些細枝末節的不同加起來,就足以讓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年輕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
他們往往學習成績不錯,很多甚至還成功保研、考研。但這種情感上的困擾會成為一個持久的陰影。甚至有的同學,在畢業、入職後的跟蹤訪談中,依舊會反復提及。
有別於勵誌敘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個名為「985廢物引進計劃」的討論小組中曾廣泛出現。借用社會學家卡拉貝爾在【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中所描述的:農村籍學生所在的校園,並不是城市學生們所在的那個精英大學。隨著這樣的討論聲音漸高,現在這群孩子又有了一個新名字,叫「小鎮做題家」。他們曾在學業上花過相當多的時間,但除此之外,非學業領域的探索並不總是順利。
從最開始的社會新聞主角,到「小鎮做題家」,這種轉變令我感到困惑,怎麽一開始說他們不會做題、不會學習,後來又變成了擅長做題,甚至「只會做題」?
透過研究,我發現,雖然這兩條敘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徑庭,但內裏都在講一個關於適應和融入的故事。勵誌故事和情感困擾,其實是一個人生命流動故事的一體兩面,他們相互存在,相互幹擾,並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個掩蓋掉。

圖源劇集【你好,舊時光】
2
在很多訪談中,我會在這些學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出生在義務教育普及之前,那時候的辦學體制和現在不一樣,每個村的村小都要靠村裏自行出資,老師們很多都是老教師的孩子,初中上完沒有考出去,就來接班,給我們上課。在村小的生活很簡單,上課時,聽老師用方言講課,下課後,語文和數學課本是我能讀到的不多的書。
到了初中,學校比小學建得遠,每天都要走幾裏地上下學。那時也正好碰到中師(註:中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們回來充實教師隊伍,雖然他們還是不說普通話,但好歹受過師範訓練。中學讀完,我的語文也已經比村小的老師們好了,他們看到我在村裏幫著其他孩子補習,劃分段落和句子結構,會來問,愛磊,你是怎麽分出來的?
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沒有出過農村,中考時才第一次到了市裏,第一次見到那麽多的汽車。在高中,第一次聽到老師用普通話講課。我能聽懂,但不會說,很長時間,班裏其他的同學都叫我「小啞巴」。我經常聽不清楚,也不會主動問,懷疑是自己耳朵有問題,經常摳耳朵,最後都摳破了,還是哥哥帶著去看了醫生。
我從來不參加班裏同學組織的校外聚餐,也沒和大家在外面玩過。有同學送了我一個小掛件,問我,你知道這是誰嗎?我從小在村子裏只看過黑白電視機,裏面只有兩三個台,我在中央一套看過幾次機器貓,看到掛件上也是一個日本小男孩,就說知道,是康夫(註:大雄的舊譯)。同學說,不是啊,這是柯南。我還是不太相信,說,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後來上了大學,我第一次看柯南,發現和那個掛件長得一模一樣。
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個切實的共同目標,我們都要成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們穿著一樣的校服,去同一個食堂吃飯,也要做一樣的練習冊。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統一性,我把這個稱為「機械團結感」,在這個意義上,歸屬感很強。我學好普通話之後,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學對我說,他很羨慕我學會了說普通話。留在村子裏的同學們,到了大學還在講方言,別人一下子就能聽出是哪裏人。
但等很多年後我開始做研究,一位學生告訴我,如果自己一個人兀自走在村裏的話,可能已經不會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對土地的感情,家鄉人會說你叛變了。」
2000年,我參加高考,是我們學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來說,我應該沖刺一下頂尖的名校,也想過報復旦大學或者南京大學,但老家人都說,不要出省,就報安徽大學。老師鼓勵我沖一把,但班裏有同學傳小話,說頂尖的大學都有優先錄取名額,你不知道就是沒有你的份兒。現在我當了大學老師,也組織過招生,知道根本沒有這些規則,但那時,這些資訊差產生的謠傳也會被我當作是事實。
放棄了頂尖大學後,我開始遵循村裏的經驗,看師範類的學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學校好,只覺得華東師大的「華東」聽起來地理上比北師大的「北京」大一點,而北師大沒有首師大好,畢竟後者名字裏都帶「首都」。就這麽選出來了華東師範大學。至於選專業,英語在專業列表裏排得靠前,我也順手寫在了前面,於是就這樣到了英語專業。
等開學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國家就開始實施招生並軌,取消了師範類和非師範類教育在收費上的區別,專業填寫的順序,也有優先級的區分。
到了上海,即使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鋪墊,我發現,大學還是另一個世界。我的英語口音很差,初中老師的英語讀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學老師問我,你的音標是哪裏學的?我說,沒有學過音標。等大學老師開始放什麽VOA、BBC的節目給我們練轉譯,我腦子轉不動。有一個新聞我印象特別深刻,是美國一個街區有一起槍殺案,周圍鄰居的窗戶都緊閉著,沒有一個人嘗試去阻止兇手。我不理解,村裏都是熟人,哪裏來的仇恨、槍和兇手呢?我很沮喪,生詞我都查了,但連在一起,我還是無法理解。
學業方面的適應問題一開始會比較明顯,但學習就像做題,其實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份,生活則是更大的問題。
同學們去打羽球,我也跟著去,第一次知道了羽球還有場地,場地中間還有網子。看到男女同學一起玩,男生們體貼地幫女孩擰開了瓶蓋,表現得「紳士」,這些都不是我的「常識」。
有過幾次這樣的經歷後,我開始關註我和周圍的區別,也產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發現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顏色有關,我感到無所適從,但城裏同學穿布鞋,他就不會有這種心理。後來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這些規則應該是什麽樣的:穿什麽顏色、什麽樣式,消費水平該是多少,吃飯應該花多少錢。我對正常的物價也沒有概念,比如這頓飯是50塊,那是貴還是便宜?我心裏沒有這個標準,因為我平時都吃兩塊五的蓋澆飯,裏面沒有肉,比50塊便宜太多。
參加學生會競選,每個候選人都要上去發言。這是一個推介自己的場合,我應該去講我自己是誰,可以做些什麽。但我當時第一次接觸競選,別人教的重點也沒學明白,上去就講了一堆之前組織得不好的地方。
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得罪人。後來,我做訪談的時候,學生們告訴我,他們大多都選擇了生活部。我當年競選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運怎麽就如此相似?生活部的工作瑣碎具體,這裏打一點雜,那邊幫一下忙,用不上什麽特長。有一個學生跟我講了好久自己參加學生會的經歷,最後總結,「做個好人就好了。」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半夜在校園裏走,我覺得我不屬於這裏。

圖源視覺中國
3
但訪談過這些比我晚十幾年上大學的孩子,我意識到,我是幸運的。
我成長於一個社會分化逐步發生的年代,開放的紅利也在同步展現著,在我上大學的年代,城鄉之間的差距並沒有那麽明顯。趕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上海開會,我去做轉譯誌願者,當時官方都是用外事標準接待我們。到了高年級,我開始做一些兼職和零工,手頭也變得寬裕起來,蓋澆飯也能點四塊五有肉的版本了。
得益於此,我記憶裏的大學時光稍微浪漫一點,也允許存在漫無目標的中間狀態。當時,學校沒有門禁,我從一個人半夜在校園溜達,逐漸變成了和同學們一起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探索,也會半夜騎著自由車,一路騎到外灘看夜景。那時候中國剛剛入世,一時間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進來,我們也走街串巷找英語社團要放映的碟片。
但我訪談的這一批年輕人,他們是社會城市化與現代化高速開發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流動」與「變化」幾乎貫穿在他們整個成長軌跡中:很多人小學一二年級在家門口上,三四年級就要到隔壁村,這就是村小的「撤點並校」。等到了中學,一部份的家長會想到把孩子往鎮裏和縣裏的中學送,這就是之後的「村小衰敗」。等到了高中,那個時期民辦學校還可以去農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績好的學生便透過擇校進一步來到市裏的高中,縣鄉的好生源流失,師資力量也不足,這又來到了關於「縣中塌陷」的討論。
教育改革、社會分層,加上人口流動,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這一代孩子的成長經歷,外部的環境不一樣了。教育這個領域出現了更加豐富的變化,大家都被裹挾著向前跑。城裏的家長拼命投資英語課、興趣班,但從小鎮和農村出來的孩子沒有這些。到了大學,就會發現,有些困難也授權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長久以來的東西,其中的差異並不能被消弭掉。
現在,我帶公費師範班的學生,其中有很多來自農村,我看著他們參與社團活動,要精通Photoshop,要會寫社團釋出的公文,還要參加結構化面試和無領導小組討論,一些社團還要求穿西裝。我問從小鎮來的孩子們,你們怎麽辦?他們告訴我,在去面試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著網上學到的經驗在面試中開玩笑,但他不知道什麽時機合適,第一次「風趣」得挺成功,第二次出來就被刷掉了。
借用社會學家卡拉貝爾在【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中所描述的:農村籍學生所在的校園,並不是城市學生們所在的那個精英大學。名校裏的城市籍學生擁有更加豐富的文化資本,他們會參與高雅文化消費,也有外出旅行的經歷和自由。這樣的文化環境令視野開闊成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於成績本身,對待知識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態度。
沒有去過博物館、劇場,也沒有上過興趣班的童年也許擁有另一個程度上的溫情和質樸的快樂,但遺憾的是,對於適應名校的環境而言,這樣的成長經歷不足以成為通向未來的階梯,而被戲稱為來自過去的牽扯。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識到,這些年輕人面臨的一些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他們的努力不夠,不是他們的向往不夠,而是社會結構局限了他們的嘗試。
經過了大一大二這一階段的沖擊與受挫,到了高年級的農村籍學生們,在訪談中展現出了一種共性傾向——對社會能力的「自我低估」。
在我的訪談中,有一個叫沙翰的學生,雖然在班上成績名列前茅,但總是會說自己「死讀書」,相比其他人「不夠靈活,學東西特別慢」。到了大三,他「每天過得和高中差不多,還去上自習,不上自習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會做的寫作業,他剩下的時間的大頭都用來勤工儉學,社交圈很小。
沙翰高中時很少看課外書,這讓他在看書時總還是像做題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別人一個小時能讀完的小說,他可能要花費一天。同學們聊動漫、體育、音樂和歷史,沙翰總是會感嘆,別人「見識不一樣,更開闊」。
另一位叫鄔子航的學生告訴我,在高中自己可以「專註學習」,但到了名校,優勢開始變得不明顯,自己還不合群:運動天賦不是很好,也不會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大家嗨」。
他開始感覺孤獨。他拒絕了同學們的打球或是唱K邀請,對於參與學生組織,也總害怕面試,擔心會被拒絕。另一位學生聊起社團參與時,也直接說:「我不太適合去管理別人,我認為,這個方面……我可能不需要。」
「內向」、「局限」、「單調」,這些形容詞構成了一種特殊的關於自身性格、見識和素質的定論。農村籍學生們會以城市學生的狀況為標準衡量自己,背後是文化資本積累的不同,這種經年累月的差距難以逾越。

4
開始任教、帶學生之後,經常會有一些農村籍學生過來問我,說老師,我該怎麽辦? 我也說不出什麽可復制的成功經驗,只能給他們講我的故事。
博士時,我從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學術環境又和我以往見過的都不一樣,我的導師是個美國人,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粵語。以前我經歷的教學多是上課,在這裏,導師鼓勵我們作出回應,敢於質疑。我又開始新一輪的適應。等後來去劍橋做存取學者,還有正式的晚宴,學院的大人物都會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張長桌上,手的左邊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後是甜點,我也挺窘迫的。
在這些變動中,我是怎麽適應的呢?其實我只是想,我從更遠的地方一路走來,現在有機會和大家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也是一件足夠驕傲的事。
在研究中,一些學生也作出了像我一樣的探索。我追蹤的學生,第一次訪談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是大一,是各種情感最震蕩的時候,第二次訪談定在大三初,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會有變化,有一個女孩子在訪談快要結束的時候告訴我,老師,我們不能往後拖,因為等下我還要去上鋼琴課。有些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後會更加註重打扮自己,有的學生像我當時一樣,去做家教賺錢。還有很多人去遊玩原生的公園,因為公園一般都免費,又是一個和學業無關的地方,往往就成為了農村學生探索城市的開端。在這些嘗試中,和城市學生的差異和融入障礙可以逐漸消除,那個做家教的學生,後來還能和同學們一起參加party。
訪談進入到高年級,我也會聽到一些不一樣的聲音。有學生會說,其實專業課裏也有水課;一些人從早到晚關註績點,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假學習」。還有一個學生很有個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學裏的事。他已經在思考這個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當然,在最後的就業選擇上,城市學生的初始薪金還是會比農村學生高。較城市學生而言,農村學生在社會意義上更好工作的機會更少,很多人不在意專業是否對口,選擇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訓機構工作。
為什麽農村學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機會更小?訪談中,我發現「經濟安全性」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我2012年博士畢業後,有一段時間特別想去頂尖大學,確實也曾經有這樣的機會,但出於收入的考慮,我最後還是沒有去。
那時候我很迷茫,如果沒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繼續做下去,就要「內建幹糧」。我接下更多的橫向課題去賺勞務費,只能靠不睡覺去完成。一開始,我把計劃列到晚上10點,後面又把時間放到12點,又再延長到2點。後來我發現,同事也不睡覺,都是秒回信件,我又把計劃列到早上4點,有一段時間幹脆不睡了,做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騎自由車去學校,食堂都還沒有開,我就先去辦公室備課。
這段經歷給我的直接影響,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術。但我沒有辦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沒有兩全。
有人說小鎮做題家的中年就是「回歸均值」,我現在年齡稍微大一點,才覺得成長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個階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現在,我也到了「均值及之下」,收入能養活自己和家人,每月買點書,讓自己吃飽一點,順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點,這就足夠了。
人生過了四十,我去過上海、香港,又到英國轉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還是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你薪資多高?你地位多高?後來我找到了自己的應對方法,我說我錢不多,也沒有什麽級別,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幾年裏,想象不到我會在以後去到這些地方、見到這些東西,我覺得很開心,也很滿足。
這個時候我已經覺得,「不適應」才是一種常態,能慢慢開啟和適應自己的「不適應」,也是一件可以驕傲的事情。

謝愛磊在劍橋
5
研究成果發表之後,一個研究生曾經找到了我的辦公室,他說我描述的情況他也都經歷過,他也曾經覺得是因為自己性格不好,才導致了不合群,看完書,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獨自一人,原來發生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釋得通」,他覺得釋然很多。
我特別開心,這就是社會學上講的「集體的智慧」,讓本來屬於一個群體當中的人能感受到集體的力量,也能原諒自己身上的一部份,開始自洽起來。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認為都是自己個人的原因。
其實,在世界範圍內,寒門子弟進入名校之後的問題都在上演著,類似的情況從南韓到坦尚尼亞都在發生。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很多的國外研究並不區別學業適應和生活適應,即假定寒門子弟生活在一個不重視學習的環境裏,因此,他們進入大學後,在學業和生活上都會出現適應問題。學者保羅·威利斯就在【學做工】裏指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學習好等於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階層身份,因為你屈從了主導階層的話語統治。
在研究持續進行的同時,我的女兒也開始了她的中學生活。雖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題的思維也變成了一種有更多適用場景的範式,無論是我們現在講到的「大學生活高中化」,還是關於「上岸」的討論。越來越多來自城市的孩子也會自稱為「做題家」,做題、做對題成為了我們生活的常態。在定稿之後,我特意把研究拿給她讀了一遍,她看完後畫了一張名為【我們不一樣的童年】的插圖。更廣泛的現實生活裏,所有人都在期待孩子往右,但實際上,現狀是把他們向左拉的。

【我們不一樣的童年】 謝香宜繪
上述已經在我過去十年訪談裏發現的苗頭,在現在這一代學生中應該會體現得更明顯。我曾經幫老家的孩子填報專業,但讓我揪心的是,現在每年村裏能上好大學的反而沒我們那時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這一代的學生面臨競爭更激烈的外部環境,不同文化之間的分層與邊界也會越來越清晰,他們需要積累更多的文化資本,才能實作更大程度的向上流動。
我們也在做一些解決問題的嘗試。像是帶公費師範班,班裏多數都是農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們有的表現出怯生生的樣子,我都會鼓勵他們多去探索新的環境。平時看到有展覽,我會準備一些票給學生們;每學期,我都要求每個人都要單獨和我聊一次;還有一個名為「師友計劃」的長期計畫,就是每學期讓班上的學生跟系裏的老師一個個吃飯,碰到有要求餐桌禮儀的,還能順便帶著他們去認識一下。我當年也是什麽都不會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現在,我也能給我的學生們講一講,這都是可以被認知的。
因為定向師範生的原因,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必須按規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師。因此,每年剛開學,我都會問學生,你們的職業規劃是什麽樣的?學生們第一次聽都覺得奇怪,說我們回去之後當然是做老師,這沒有什麽選擇。我就繼續問,你們有想過要做什麽樣的老師嗎?作為老師,你們又面對的是什麽樣一群孩子?這回他們不知道了。
前年,我帶了學生們去粵東西北做調研,他們訪談的學校,都是未來他們要回去工作教學的地方。那次我們一共調查了17000多名學生和3000多名老師,這使得他們在正式開始工作之前,就有機會去觀察自己未來的教學場所和物件。現在縣城中學裏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音體美師資力量的不足,還有學生們對手機的過度依賴,這些他們都能親眼看到。我會把之前的提問再問一遍,這是一個不斷修正、準備和磨合的過程。
學生和我碰面時,很多人都還會帶著一個相同的問題來找我——如果探索失敗了會怎麽樣?我一般會回答,人生還很長。我也會講自己的經歷,講現在還在困擾我的事。我從他們這個年紀一路走來,花了更多的時間,走了多多少少的彎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獲。
一位已經當了家長的朋友告訴我,她童年是用土竈燒飯生火的,但考到城市之後發現,這裏都不用土竈,她就自卑。等她自己在城市站穩腳跟、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後,幼稚園說讓家長組織表演,其他家長都吹拉彈唱的,她什麽都不會,過了很多年,那種自卑感又出現了。
轉折發生在一次幼稚園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機,大家也不知道怎麽生火。這時候,這位家長站了出來,她小時候練習過那麽多次,她知道底下要告空,要通風進去,火才能旺起來。在其他人都束手無策的時候,她兩三下就成功了,那個瞬間她特別自豪,這是過去生活在多年後送給她的禮物。
也許我們都會發現,等到了生命的另一個階段,重新回過頭看,很多當時特別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淚水的事情,都會變成成長的過程。很多年長的朋友都告訴我,一些現在看上去像是鴻溝的東西,會在時間流逝中慢慢消散掉,這與成長有關,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在兩個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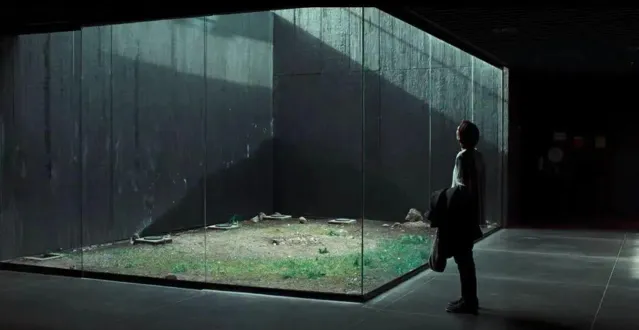
圖源電影【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