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李沁樺 張奕丹 江西新余報道
順著江西省分宜縣的縣城大道向南,起伏和緩的山脈在厚厚的雲層下一路綿延。山脈盡頭處的鍛壓廠社區內,推開兩扇鐵門,可以看見兩棟不高的小樓。這就是德仁苑,一個專為困境兒童設立的福利院。

余暉中的分宜縣德仁苑。
德仁苑的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串故事,包括這裏的校長黃梅生。
有的孩子年幼失怙、母親離家,有的孩子生下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也有的孩子雙親入獄。負責照顧這些孩子的老師們,有的從鄉村的窮小孩一路攀升成為縣城小學校長,有的在丈夫車禍去世後照顧一對雙胞胎,困難重重。
在德仁苑這個小家裏,沒有人會對他們的故事感到驚訝。17年裏,從這裏走出去的348個孩子是彼此的兄弟姐妹,黃梅生是他們的「校長爺爺」。黃梅生說,「照顧好一個缺愛的孩子,少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可能比多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貢獻更大。」
1
一棵白楊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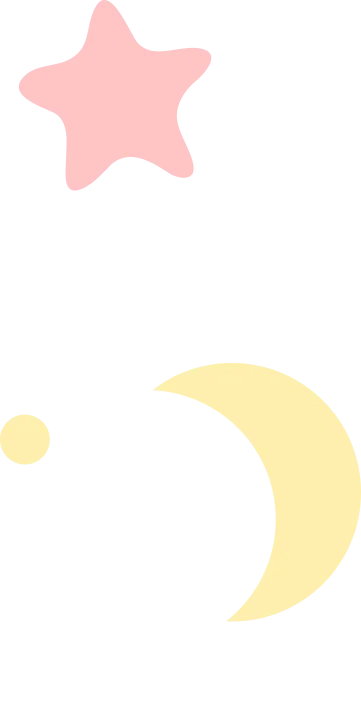
11月9日是黃梅生65歲的生日。孩子們給他畫了手抄報,祝他生日快樂和身體健康。有一個孩子給他疊了十顆紙星星,每一顆開啟來,裏面都用稚嫩的筆觸寫著「生日快樂」。黃梅生把那些五顏六色的小紙條握在手心裏,收進櫃子裏,蓋在一大堆紅色的榮譽證書上面。

孩子們為黃梅生慶生。
從18歲做代課老師開始,黃梅生一路做到當地的小學校長和縣教育局副局長。他的人生經歷以10年為單位,10歲前家境貧困甚至要挨餓,20歲當老師,30歲當中學校長,40歲調到分宜縣教育局任副局長,同時兼任分宜縣第一小學校長。到了快50歲,2008年,他創辦了德仁苑,多了一個「校長爸爸」的身份。
榮譽紛至沓來,他的櫃子裏漸漸堆滿了厚厚的紅色證書: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建設先進工作者、江西省勞動模範、全國關愛留守兒童百名愛心校長,以及2017年的「中國好人」。他把這些證書一股腦堆在一起, 「太多了,沒收拾整理,實在有點不好意思。」
黃梅生不愛笑,兩簇灰黑色的眉毛總是緊緊地皺在一起,久而久之,眉心已經有了一道深深的豎紋。但是和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會蹲下來,笑著和他們說話, 眼角的魚尾紋會一根根綻開 。銀框眼鏡下,是沈靜的、略顯疲憊的眼睛。
他總是感到累,尤其是這幾年。從2000年去一個「野孩子」家裏家訪開始,到建成德仁苑,再到今天,他看過很多事實無人撫養的孩子投過來的目光,「怯生生的、孤僻的、迷茫的,那些沈默的註視沈甸甸地壓在心上。」

德仁苑的一個孩子,從小由爺爺帶大。爺爺去世後,她站在家門口想爺爺。受訪者供圖
一開始,他也和所有人一樣,每隔一兩個月就拎著米和油去家訪。但是這些孩子們生活在原本已殘缺的原生家庭,偶爾的看望和一點錢,一旦斷掉,像拉伸的橡皮筋一樣,只會讓一切關心和幫助彈回原處。黃梅生還記得,有一個孩子年幼喪父,由爺爺奶奶撫養長大。他去家訪,看到一家人吃飯,孩子父親的黑白遺像就擺在飯桌上。他的心揪在一起,把孩子抱在懷裏,問:「你想爸爸嗎?」小孩擡起頭來,一臉是淚。
黃梅生想做一件大膽的事。他要把這些家庭殘缺的孩子們聚在一起,為他們建一個新的家庭。困難擺在面前,他沒有錢也沒有地。對於他想照顧的這些孩子,由於孩子們尚有親人在世,不能算作孤兒,但實際上無人照顧。在2019年民政部出台【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之前,這些孩子的定性存在政策空白。黃梅生一遍遍地跑縣裏、市裏、省裏反映情況,為孩子們爭取資金,用他的話來說,是「去化緣」。
2008年,黃梅生希望的契機終於來了。一些來自上海的企業家準備在分宜縣當地建一所希望小學,黃梅生對他們說,「你們把這筆錢給我,讓我去建一所不一樣的學校。」
34個,這是第一批進入德仁苑的孩子的人數。每一個孩子,都是他親自走泥路挨個探訪核實過,認為家庭情況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黃梅生說起那些被篩選下去的人,眉頭皺得更緊。他嘆了口氣, 「沒辦法,我的能力只能養這麽多孩子。」
動工前,工人要把工地上一株營養不良的白楊樹挪走。黃梅生自掏腰包,花了100元錢把樹買下來,「希望這棵樹能夠保佑孩子們,保佑德仁苑。」

2008年,德仁苑院子裏的白楊樹。受訪者供圖

2024年11月,德仁苑院子裏的白楊樹。
16年過去了,白楊樹長成了一棵二十多米高的大樹,亭亭而立。孩子們去上課,黃梅生喜歡一個人坐在樹下的長椅上,聽著風搖動樹的葉子。
2
另一個「張桂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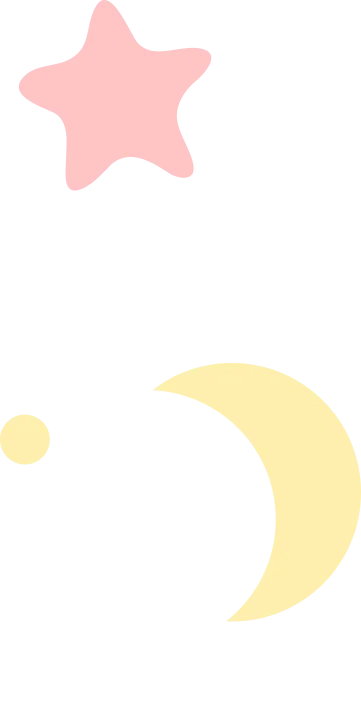
德仁苑剛建起來的時候,質疑的聲音很多。一個有大好前程、即將退居二線的「教育官」,為什麽平白無故地幫助一群不認識的孩子?
黃梅生覺得,「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過那些孩子」。他始終認為,作為一個老師,沒辦法不管孩子,哪怕那些是會偷會搶的「野孩子」和「窮孩子」。
不僅僅是貧窮。在偏遠的鄉鎮,有孩子的家只有四面土墻,墻上還掛著孩子父親的遺像。政府撥下來的低保金和救助款,一大半變成了大人麻將桌上的賭註和嘴邊的煙卷。孩子沒人管,也不知道被人愛是什麽感覺,像野草一樣瘋長。黃梅生想,如果不把這些孩子救出來,去愛他、教育他們,讓他們走一條正確的道路,未來社會上不就多了一個走上歧途的人嗎?
黃傳庚是黃梅生在當中學老師時的學生,他大學畢業後回到分宜縣融媒體中心工作,也是最早關註和報道黃梅生的記者之一。2008年,德仁苑動工的時候,他也在現場幫忙,「那時候黃校長開始招生,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這裏來,家長心裏都沒底。」
每隔半年,黃傳庚都會回德仁苑走走,看看孩子們過得怎麽樣。2020年後,受疫情影響,原本出資的上海德仁基金會不得已斷掉了資金援助。他原本想,可能德仁苑就這麽散了。事實上,該基金會在江西設立了4所專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建造的「德仁苑」,3所均先後關停或更名。 只有黃梅生的分宜縣德仁苑,活了下來。
「靠的是黃校長咬牙堅持下來的。」德仁苑所有人都這麽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黃梅生既是德仁苑的校長,也是發言人。每天的重要任務就是接打電話,他要和愛心企業、愛心人士溝通捐贈,和地方政府檢查單位匯報情況。

德仁苑的愛心捐款箱。
這兩年,時不時會有網絡博主探訪,拍德仁苑和孩子們的影片,黃梅生也磕磕絆絆地學會了用微信和抖音。他把套用的字號調到最大,面對滿屏跳出來的訊息,一個字一個字手寫回訊息,「非常感謝您關心關註德仁苑的孩子們,愛心滿滿!」
講電話的時候,他會慢慢地踱步,從德仁苑的院子這頭走到那頭,再折返回來。大多數時候,他每天的微信步數顯示都是一兩萬步,多的時候,比如暑假去每一個孩子家裏家訪,他可以每天走上三萬步。他走路的步伐邁得很大,如果落後兩步,就只能看到他瘦小但板正的背影。
這個身影要扛起整個德仁苑。孩子們的日常起居由生活老師負責,2010年就在德仁苑工作的晏紅衛是整個家的「大管家」,走到哪裏都帶著兩個手機和一大串鑰匙。同樣在這裏待了十幾年的,還有負責做飯的鐘秀花。丈夫車禍去世後,只留下一雙年幼的雙胞胎兒子,她本來以為自己「沒希望了」,但是黃梅生收下了她,還收下了她的一對兒子。
鐘秀花給黃梅生送了一面錦旗,上面寫的是「情深似海」。錦旗幹幹凈凈的,就像那顆「為了孩子的紅心」。

鐘秀花和孩子送給黃梅生的錦旗。她的兩個兒子在今年考上大學,從德仁苑邁入了大學。
還有今年剛加入德仁苑的生活老師黃艷青和種菜工袁誌毅,他們就住在空的學生宿舍裏,和孩子們同吃同住。袁誌毅早年在國營墾殖場當工人,「種了一輩子的菜」。看到德仁苑發資訊招人種菜養雞,他走過來面試。黃梅生跟他說,咱們這裏的薪金不高,他說他不怕。黃校長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愛孩子嗎?」他就知道自己來對了地方。
「你知道張桂梅的那個電視劇,我每一集都守著看。我就覺得我們的黃校長就是那樣的,只是規模沒那麽大,沒那麽出名。」袁誌毅說。
有媒體問黃梅生,你覺得自己和張桂梅比怎麽樣?
黃梅生搖頭,「我不願意成為張桂梅,太多的榮譽,我已經不需要了。」他辦德仁苑的目的,從來都不是再多培養一個大學生,而是少一個為社會添亂的人。「我的孩子們可以成為老師和軍人,可以成為科學家,也可以只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3
一件不簡單的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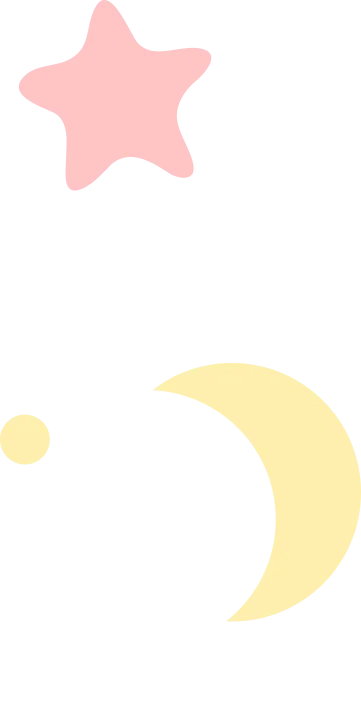
每個重返德仁苑的人都會感嘆,不論過了多少年,德仁苑似乎都沒有變化。
一批孩子長大走出去,另一批孩子又會走進來。有的家庭,姐姐、妹妹和弟弟三個孩子都是在德仁苑長大的。從外表上,很難在孩子們身上看到德仁苑的烙印,他們和所有同齡孩子一樣天真活潑。
11月的江西冷風凜冽,但德仁苑的孩子們每一個都臉頰紅彤彤的,飽滿潤澤的小臉上都是笑容。「孩子們營養要好,每一頓飯,食堂有剩飯和剩菜,我才能知道他們吃飽了。」黃梅生每一次都這麽叮囑。
德仁苑的墻上,貼著這樣一句標語,「容易的事天天做就不容易,簡單的事天天做就不簡單」。
吃飯、睡覺、學習, 這些孩子們的小事,都是黃梅生的大事 。每個周末,會有前來捐款捐物的好心人,也有誌願來給孩子們上課的老師和心理咨詢師。他們中的大部份人,和德仁苑的孩子們已經認識了四五年,甚至更長。「我想我有這樣的能力,就可以為孩子們做一點小事。」這是他們共同的想法。
在孩子的自習室,兩個大姐放下東西正要離開。2020年,她們知道黃梅生為孩子們做的事後,每隔一兩個月都會來,SUV的後備箱裏,塞滿給孩子們吃的糧油、零食和牛奶。每次她只會略略坐一會兒,再靜悄悄地開車離開。「有人捐點物資,會拉個橫幅,看起來很拉風,但是我覺得沒必要。」
來了三四年,孩子們會靦腆地笑著叫她們「阿姨」,只知道她們一個姓楊,一個姓季。「我們文化水平不高,幫不了太多忙。」她不好意思地笑,「現在的社會,做點好事其實不是那麽容易。」退休後,她隨大流每天和人搓麻將,但麻將桌逐漸變得枯燥,內心總想「做點事」。她開始接觸公益,感覺自己終於走上了一條「正確的路」。
楊大姐也有兩個孩子,她相信黃梅生是真正為孩子著想的「好人」,是因為一個細節。「有一天他去外面吃酒,帶了喜糖回來。就好像我們小時候的父親,小孩子知道了,全部湧過去,叫他‘校長爺爺’,朝他撒嬌要糖。」

黃梅生去海南出差,給孩子們帶回來幾個椰子嘗鮮。受訪者供圖
說起「爺爺」,黃梅生眼皮耷拉下來,搖搖頭,停頓了很長時間。他說話的語調一直高昂且鎮定——四十年的教師生涯,讓他在日常生活中也習慣像課堂講課一樣說話——一下低落了很多,他想起了自己的兒子,以及兒子的一雙兒女。「我是這些孩子的校長爺爺,但不是我的孫子孫女的好爺爺,我其實深感虧欠。」
現在他看起來還是和17年前沒什麽兩樣。飯後在路邊散步,看到有小孩落單,他一定會走過去,蹲下來摸摸孩子的頭,問「你叫什麽名字」和「你在學校有沒有聽老師的話」。去做報告演講,他只挑距離德仁苑一個小時路程的地方,其他都推辭掉了,「因為孩子們需要我在身邊」。
黃梅生的愛人笑著說,「可能他這個人,註定就是只能當老師的。」
他會和孩子們一起例行做社區衛生,把周邊社區地面上的垃圾掃得幹幹凈凈。德仁苑門口的布告欄上,貼著從2008年到現在,他和孩子們每一年的合影照片。孩子們吵吵嚷嚷的,快樂地在這些全家福裏面尋找自己。

2008年,黃梅生和孩子們。受訪者供圖

2024年,黃梅生和孩子們。
「校長爺爺,那是你嗎?那個時候你的頭發還是黑黑的。」一個男孩指著老照片問。
「是啊,那個時候我還很年輕。」黃梅生突然有點感傷。 他彎下腰和孩子們笑著說話的身影,和過去的歲月重合在一起。那是他花了17年的時間,做成的一件「不簡單的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