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馬克斯·韋伯誕辰160周年。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特別策劃「以韋伯為誌業」紀念專題,邀請國內外研究韋伯的專業學者撰文,發掘韋伯對於現代社會之意義。
再沒有哪一座德國城市比海德堡受到過更多的贊美,也再沒有哪一座城市比海德堡更當得起「德意誌之心」的稱號。歌德曾說,「我把心遺忘在了海德堡」。這座位於德國西南部的小城,不僅因為內卡河畔的美景和山腰上的老城堡而博得遊客的青睞,更因為舉世聞名的海德堡大學成為德意誌文化的重鎮。建立於1386年,海德堡大學是神聖羅馬帝國建立的第三所大學(晚於布拉格大學和維也納大學),也是德國境內最早建立的大學。從建成之日起,海德堡大學就成為培育學術心靈的搖籃,從這裏走出過哲學的領袖,包括黑格爾、雅斯貝爾斯、哈貝馬斯等,也走出過科學的先鋒,誕生了超過五十位的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
在這一串耀眼的名字中,馬克斯·韋伯身處其間亦是毫不遜色。與馬克思、塗爾幹同為社會學的奠基人,今天的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系正是以馬克斯·韋伯的名字命名。韋伯的母親來自於海德堡地區的望族,韋伯也在海德堡度過了他的童年、大部份學生生涯,海德堡也是他長期居住和任教的地方。韋伯生命中的三位「紅粉佳人」,包括他的妻子瑪麗安妮和兩位情人,也都是在海德堡去世。而韋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不像哥哥那樣在多個城市間輾轉,而是長期在海德堡大學任教,今天的海德堡大學經濟學系就是以阿爾弗雷德·韋伯冠名。今天的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在貝格海姆校區的同一棟樓裏,講述著那個風雲變化的時代和一段不平凡的家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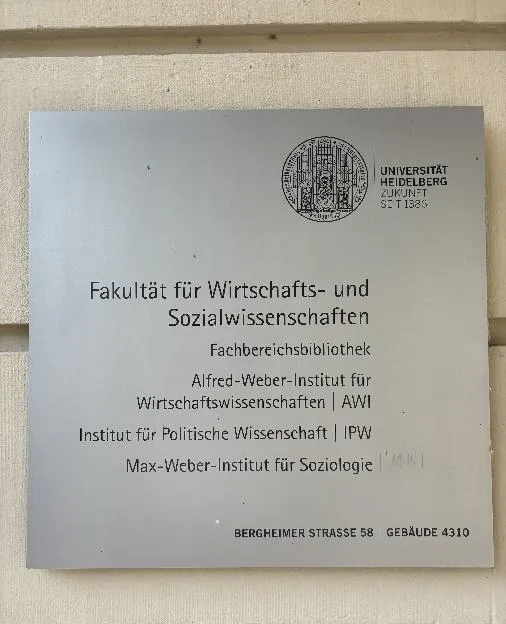
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銘牌

海德堡大學貝格海姆校區(作者攝影)
今天,韋伯的墓就矗立在海德堡的「山庭」公墓。墓碑上刻著韋伯夫人為他選定的墓誌銘:「世上再無這樣的人;世間的一切不過爾爾。」後一句話出自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在這一作品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導下不斷得到他所渴求的智慧與知識,同時也不斷失去自我,乃至懷疑這一切的進步意義何在。這是德國浪漫主義的一個化身,尼采曾說德國的浪漫帶著一種粗野。這正是德國思想界在十八、十九世紀根深蒂固的一種特性,黑格爾如此,馬克思也是如此,韋伯更是如此:越是進步,我們失去的也就越多。馬克思一邊稱頌資本主義大工業帶來的強大生產能力,一邊深刻批判資本主義工廠對工人的剝削和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韋伯將理性化標記為現代社會的前提,又憂心忡忡於完全理性化的社會結構(韋伯重點談到的是官僚制)會讓社會喪失活力,落入「鐵籠」(帕森斯語)。出於打破這種「鐵籠」的需要,韋伯設想現代社會依然需要「克里斯瑪型(charismatic)領袖」的出現。韋伯不曾料到,這種構想很快釀成了苦果。

作者在海德堡韋伯墓前
韋伯的這種雅努斯式心態是彌漫在青春期德國的一種普遍心態。韋伯出生於1864年,普魯士對德意誌的統一已經箭在弦上,俾斯麥的文韜武略使普魯士的統一之路通暢很多,最終在1871年實作了德國的統一。雖然韋伯的一生都是一個堅定的自由派,甚至得到了「資產階級的馬克思」這一稱號,但韋伯對於魅力領袖的憧憬同樣是他政治理想的重要一部份。一戰後,德國成立了威瑪共和國,韋伯加入了威瑪憲法的起草委員會。當時的委員會裏有著各種政治派別,在艾伯特總統的領導下,威瑪憲制被設計得相當復雜。韋伯對於這種極其理性化的官僚機器充滿警惕,因此,在他的力主下,威瑪憲法賦予了總統一職相當大的權力,韋伯設想總統可以超越議會直接代表民意,並在議會無能的時候成為推動進步的真正力量之源。可以說,韋伯將自己對於「克里斯瑪型領袖」的想象在這一刻凝聚在威瑪共和國總統這一角色上。同時,韋伯堅持在憲法裏加入第四十八條「緊急戒嚴令」條款,賦予總統宣布緊急戒嚴、並越過議會采取緊急行動的權力。天意弄人,這一條款後來被希特勒的納粹黨利用而建立獨裁統治。韋伯未曾料到,一戰後民族主義情緒熾盛的德國選出了一個保守的容克軍官興登堡做總統。1934年納粹黨利用「國會縱火案」說服了興登堡,興登堡簽署【保護人民和國家的總統法令】,該法令是這樣開頭的:「為了抵禦共產黨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參考德國憲法第48條第2段,頒布以下命令。」其內容實際上廢除了民主制度,威瑪憲法中規定的多項政治自由與權利「停止適用」,「故對人身自由權、言論自由權,包括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郵政、電報和電話私密權的限制得以允許,若未另外聲明,根據傳票搜查住宅、沒收財產及對財產加以限制亦不受法律約束」。
因此,有學者戲言,韋伯的早逝或許是一種「幸運」,這避免了韋伯不得不直面納粹黨的崛起——部份地由他自己釀成的苦果。甚至有學者直言,韋伯的「早逝」確保了他在科學萬神殿中的位置——這話影射的正是韋伯的同事兼競爭對手,維爾納·桑巴特。桑巴特由於影影綽綽的親納粹和反猶立場,在現代社會學領域幾乎湮沒無聞,只有思想史學家還會對他青眼有加。桑巴特生於1863年,比韋伯長一歲,同樣是在柏林開始自己的早期學術生涯,也都從施莫勒那裏得到指導和「幫助」——姑且稱之為前輩的「幫助」。桑巴特早年是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專家,對於【資本論】的解讀也曾得到恩格斯的稱贊,但很快,桑巴特認為馬克思在解釋資本主義起源時遺漏了重要的「精神性」因素。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能夠出現的關鍵是從需求滿足型心態轉變為逐利心態,其中特定人群的企業家精神至為重要。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現代資本主義】中指出了地中海城邦和威尼斯商人的角色,在1911年出版的【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中直言猶太人的逐利欲望驅動了資本主義的出現。也是在這條戰線上,韋伯和桑巴特進行了長期的辯論,首先是哪個群體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做了貢獻:韋伯說是新教徒,桑巴特則說是猶太人;其次是誰對這種「唯心主義」解釋版本擁有優先發現權。1904年首次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韋伯就已經頗有些底氣不足地宣稱這種優先權,他只是在註腳裏宣稱自己的想法來自幾十年前就已經在課堂上表述過的內容,並且後來不斷否認自己受過桑巴特的啟發。克斯勒認為這種辯駁不會有結果,因為韋伯拿不出實際證據。
從後世參照的情況來看,無疑是韋伯贏了,但桑巴特在世的時候,桑巴特才是那個德國學術界的執牛耳者。桑巴特逝世於1941年,曾繼承施莫勒的德國社會政策協會主席一職。但桑巴特的政治立場一直很成問題,這也導致他的身後聲名飽受爭議。他的【猶太人與經濟生活】受到兩種極端的評價,一部份猶太人認為桑巴特將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歸於猶太人是對這一群體的褒揚,桑巴特還為此得到美國猶太人協會通訊會員這一榮譽,另一部份猶太人則認為桑巴特將猶太人描繪成貪婪成性、專門放高利貸盤剝他人的守財奴形象,強化了反猶主義的刻板印象——弗蘭茨·歐本海默正是這樣認為的:桑巴特就是反猶主義立場。實際上,也的確如此,桑巴特對猶太人的描繪得到了納粹黨高層的認可和青睞。納粹黨漸成氣候之後,桑巴特寫了一本熱情洋溢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來闡述社會理想,這本書的學術成分不高,可以說是德國歷史學派所一貫持有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宣傳手冊。納粹黨在1933年上台之後,部份黨內高層也曾興奮期待這位學界巨擘成為納粹黨的金字招牌,但吊詭的是,桑巴特很快在1936年解散了社會政策協會,避免這一德國規模最大的社會科學家聯合會為納粹黨所利用。
桑巴特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中大力鼓吹一種「德國社會主義」,聲稱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階段已經過去,現在需要一種包含「德意誌國家精神」的「社會主義」來為民族創造未來。如果看看韋伯早年的【民族國家與民族政策】和一戰後的通訊,我們也可以找到類似的蛛絲馬跡——韋伯身上的民族主義情緒並沒有少多少。然而,我們必須避免刻舟求劍式的魯莽判斷。那個時代,經過兩個世紀的追求,德國才找到自己。李斯特為了德意誌的統一和富強奔走終身,歌德高喊「德意誌在哪裏?我找不到她!」統一後的德國,既無英國那樣的憲政傳統,也無法國那樣的中央集權歷史,仿佛剛走入青春期,熱血狂躁,急於為自己找到位置。韋伯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底色之上也難免塗有一絲對強權領袖的盼望。
另一位試圖引導德國的思想界巨匠是斯特凡·格奧爾格。韋伯的人生已經相當多姿多彩,格奧爾格的人生路更是不遑多讓。格奧爾格被譽為「歌德以來,寫詩最好的德國人,尼采以來,活得最純潔的德國人」。他1868年出生於德國西部萊茵蘭地區的一個葡萄酒商人家庭,很小的時候就展現出過人的領導才能和高超的語言天賦。成年後的格奧爾格過著相當瀟灑的生活,圍繞他自己組建了著名的「格奧爾格圈子」,其中大部份是他的弟子和朋友,有很多人後來成為著名的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比如曾寫出歷史名著【國王的兩個身體】的康托洛維茨。韋伯也曾一度與這個圈子過從甚密,但很快退了出來。根據施魯赫特的說法,韋伯並不喜歡格奧爾格那種具有相當程度個人崇拜的圈子文化,其中彌漫著一種若有似無的精神寄生關系,但是,韋伯也從格奧爾格圈子那裏獲得了大量關於克里斯瑪型支配類別的靈感——韋伯將格奧爾格圈子視為克里斯瑪型組織的一個典型。格奧爾格用一種古希臘式的酒神文化統領他的圈子,並在他與弟子之間也培養出了一種柏拉圖式的情感關系。沒錯,格奧爾格是個同性戀者,並認為對於年輕美男子的愛慕是人類最神聖的一種行為。在圈子裏,他是無可爭議的「大師」。也正是由於這種風格,有時很難說那是一種純粹的戀愛關系,這也成為格奧爾格後世爭議的一個焦點。
格奧爾格的詩歌作品風格明確,充滿貴族氣質和古希臘精神,同時很多作品也飽含著對強大德意誌的呼喚和對一個「秘密德國」的向往——雖然他祖上是法國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才搬到德國西部。「秘密德國」既是他的一首詩的名字,也是他建立過的一個神秘精英組織。在「大師」和「弟子」們眼裏,「秘密德國」不曾存在,當下也無,卻「永恒存在」,那是一個美學意義上至高無上的國度,精神高貴,詩歌和哲學將引領民族前進。在格奧爾格的指導下,前面提過的康托洛維茨曾寫過【佛烈德利赫二世大傳】——據說,這本歌頌德意誌皇帝的厚厚傳記是希特勒和戈培爾的心頭好。納粹黨也的確向格奧爾格發出過正式邀請,還想設立一個以格奧爾格命名的詩歌文學獎項,但都被他拒絕了,格奧爾格迅速逃到了瑞士,不久就在那裏去世。盡管格奧爾格圈子對德意誌精神的呼喚、對魅力人物的無限向往都讓很多納粹人士引為楷模,但很多人忽略了格奧爾格圈子的精英主義和歐洲主義傾向。看看格奧爾格圈子崇拜的人物,實際上是超越狹隘德意誌概念的那些人。格奧爾格圈子與納粹的張力後來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鬥爭。康托洛維茨1933年在法蘭克福大學做了一場題為「秘密德國」的報告,直斥擁護納粹的青年;格奧爾格有三個親近的弟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施陶芬貝格兄弟,他們在1944年籌劃了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但行動失敗,施陶芬貝格兄弟被槍決——槍決前,他們高呼「秘密德國萬歲」。

波特倫·謝弗德教授在格奧爾格紀念館進行講解(作者攝影)。謝弗德教授的父母曾是格奧爾格圈子的成員,教授本人長期資助位於賓根的格奧爾格紀念館,並贊助詩集出版。
本文所談到的三位主要人物,韋伯、桑巴特和格奧爾格,都或多或少經受了要為納粹崛起負部份責任的指責。二戰後,這種「精神清算」鋪天蓋地,將黑格爾、尼采都一並列了進來,其範圍如此之大,以至於德國思想史的每一部份似乎都以某種方式要為這種災難負責。幸或者不幸,韋伯都不用親身經歷他的朋友桑巴特和格奧爾格後來經歷的那些「糟心事」。在韋伯最後的十年裏,他一邊為德意誌的民族事業和自己的學術事業殫精竭慮,一邊在自己的情感生活裏釋放激情。除了早早結婚的瑪麗安妮之外,韋伯長期和米娜·托布勒保持著關系,後來還瘋狂地愛上了艾爾澤·雅菲——這位女士,同時與馬克斯·韋伯和阿爾弗雷德·韋伯這對親兄弟保持著戀人關系,而艾爾澤·雅菲的合法丈夫正是艾德加·雅菲——和馬克斯·韋伯、維爾納·桑巴特一起編纂【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的同事,也是阿爾弗雷德·韋伯在海德堡的同事。即使在已經移風易俗的今天,韋伯與情人們的關系恐怕依然令人瞠目結舌。大度的韋伯夫人似乎接受了這一切,韋伯去世後,三位女士組成了「遺孀軍團」,一起生活在海德堡,最後都逝世在這裏。
「世上再無這樣的人」。我想,這並不僅僅是對韋伯個人非凡創造力的肯定,也是對那個時代特殊背景的一種表達。我們再也找不到那樣風起雲湧的時代,也不再面臨那樣的問題——或好或壞。韋伯的思想是在德國的時代條件下形成的,也是在與同行者的思想碰撞中產生的。今天的社會可能不會再碰到一模一樣的問題,但黑格爾告訴我們,「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就此而言,韋伯的思想仍然是後人解決新問題的充滿活力的靈感之泉。
姜宏(海德堡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