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9日,在南京先鋒書店舉行的「如何讓大眾重新愛上文學閱讀——芮塔·菲爾斯基作品共讀會」上,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但漢松、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範昀、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張德旭以文化研究領域的傑出學者芮塔·菲爾斯基【批判的限度】【文學之用】【現代性的性別】 三本著作為引,就文學的作用、批判性閱讀的範式以及被文學所激起的各種情感等話題展開對談。下文為對談速記整理稿。

對談現場
芮塔·菲爾斯基其人與轉譯引進緣起
張德旭: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這本書就是菲爾斯基的【批判的限度】。菲爾斯基是維珍尼亞大學英文系教授,知名度極高。這本書在西方的影響力可以透過幾個數據看出來,第一個就是在Google Scholar上被參照了2000多次,然後在美國讀書網站Goodreads上面也有三四百人打分,打出了4分的超高分數。
但漢松: 菲爾斯基在文學批評領域是一個非常有建樹、聲望卓著的大學者。長期以來,我們國內的文學出版,對於美國這一批50多歲的本土女性批評家的關註其實是不夠的。
南大社之前做了好多文學批評理論書的引進,更多的是關註歐洲學者,尤其是法國學者,而且主要是男性學者,所以我有幸來主持這個書系的時候,我就發願我們能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把文學批評的另外一些聲音介紹到國內來,給那些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讀者一些新的資訊。菲爾斯基其實是我們的首選,因為她在我們這個圈子裏面真的非常有名,但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她比較適合「出圈」,因為她的文學氣質和一些典型的英語系比較陽春白雪的教授是不太一樣的。因為菲爾斯基還是希望能夠有一種社會願景,就是把文學批評做到一個更廣泛的讀者群體當中去,或者更具體地說,她希望文學批評不再是象牙塔裏面的東西,而是能夠與我們的日常文學閱讀發生關系。
菲爾斯基其實不是美國人,她是英國人,但是英國工人階級家庭出身,完全是靠獎學金去到了劍橋,所以在這樣的學校裏面,她其實感覺到並不是特別能融入,她說她不喜歡牛津劍橋,因為她覺得這裏面都是一些富家學生。從一開始,她對於社會批判,對於女性意識,是有高度自覺的。後來她的學術起飛期實際上是在澳洲,她在澳洲一所大學師從一位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者,在那之後她來到了美國任教,現在在維珍尼亞大學長期執掌教鞭。
她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身份是美國頂級文學批評雜誌【新文學史】的主編。大家如果熟悉中國的學術生態的話,大概也知道如果你是【中國社會科學】或【文學評論】的主編,其實你在學界的地位應該是非常高的,那麽菲爾斯基相當於不僅僅是一位老師,還是美國文學批評界的領軍人物,透過這本刊物組織了大量的專刊討論,所以她是能夠引領美國批評思潮的卓有建樹的學者,這是第二個我覺得她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個選她的原因是她的語言非常好。閱讀她的英文原文,你會感覺到一種酣暢淋漓,一種非常縝密的語言的暴風驟雨。所以我是蠻被她的思想,也被她的文字所征服的。她的這本書不僅有學術的內容,而且它本身的語言就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沒有那種匠氣,沒有那種特別雲裏霧裏的東西,具有高度的分析性,但是修辭能力又很強,然後她的詞匯量真的是非常大,所以我在轉譯的時候也感覺到一種暢快,因為學術語言居然有這樣的文學性,其實是我沒有想到的,我也很願意把這樣一種風格寫出來的文學批評傳遞給大家,因為我們已經讀了太多轉譯過來的社科圖書,它的每個字你都知道,連起來你就不知道它在說什麽,但這本書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批判有哪些限度?
張德旭: 一提到文學,我們總覺得文學應該批判什麽,抨擊什麽,揭露什麽,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彰顯文學的價值。菲爾斯基覺得這只是文學批評的取向或者一種進路,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是當前的西方,尤其是1950年以來的西方文學批評,主要被這種批判的基調所主導,但是外國也都在檢討這種批判的基調,也就是近10年來,有各種期刊雜誌,還有召開的各種年會,都在探討我們當下的閱讀方法,想從批判的這種模式、窠臼中解脫出來。
這本書英文名叫The Limits of Critique,所以批判是有很多限度的。菲爾斯基在書裏,尤其是在導言裏提到了最重要的一個限度:它已經成了一個基調。大家一提到文學批評,就覺得應該在文本中去發現文本與政治合謀的地方。那麽菲爾斯基覺得,除了作為主導的元話語的地位,批判還有什麽別的限度,以至於我們現在必須改變這種基調,讓別的方法也融入文學研究者甚至普通讀者的視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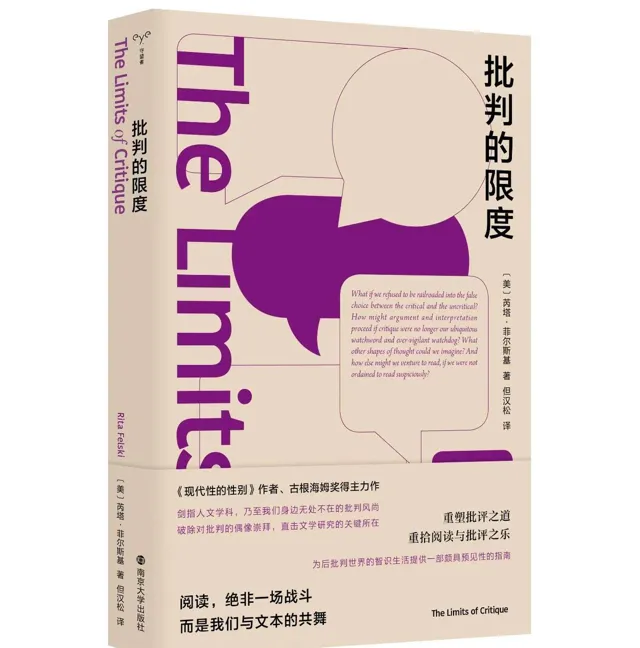
【批判的限度】
但漢松: 其實這本書不需要特別專業的文藝理論訓練,或者是理論知識的積累,你就能夠看出它講的道理是什麽。菲爾斯基實際上是從一種所謂的閱讀的現象學出發,這種現象學就是把一些概念、一些先入為主的理論的假設都懸置了。當我說你的批判有問題的時候,我並沒有去說你的理論的具體內容,或者你的某一概念、你的思想體系就一定是錯的,這不是菲爾斯基說的話。
菲爾斯基主要是看出了不同批判類別的學者,在接觸文學文本的時候,他們有一種共同的感性風格,這個感性風格通常是被視作不存在的,但實際上又隱而不顯地在場,這個東西是什麽?這個東西就是懷疑,她稱之為懷疑的闡釋學。
一些學者在看到一部電影或者一部小說的時候,首先覺得自己需要去懷疑他的審美物件,他無形當中戴有一個福爾摩斯式的人格面具,他的不信任,從他翻開這本書的第一頁就開始了,甚至還沒有翻開書,他就已經有不信任了。這種不信任是什麽?不信任主要是認為這本小說、這個電影的語言表層其實是有所隱瞞的,在它的下面,在它的後面,總之在某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有一個隱秘的犯罪現場,有一些它秘而不宣的東西,甚至有一些見不得人的東西,這樣一個由懷疑精神驅動的文學研究者,其第一要務就是將真兇捉拿歸案,就是要在文學中揭開他的謊言,然後把裏面更真實的東西帶到我們的視野之下,所以有了這樣一個共同的懷疑心理。懷疑成為一種慣性,批判的問題就出來了。
馬克思有一句話,叫懷疑一切。當我們去懷疑一切文本的時候,會帶來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萬一你懷疑錯了怎麽辦?萬一人家是無辜的怎麽辦?萬一人家不是像你想的那麽壞,怎麽辦?這其實就是菲爾斯基要掰扯的第一個問題,當我們把批判視為去暴露一個秘而不宣的真相,或者一個罪案現場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先入為主地對別人做了一個有罪推斷,而這樣一種有罪推斷實際上是非常刺激、讓人暗爽的,一旦你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慣性,這種懷疑的習性就會讓我們對文學缺乏其他的感性、其他的情感、其他的情緒。
菲爾斯基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懷疑,因為懷疑是人前進演化而來的共同心理。但是如果只有懷疑。如果只有批判,如果只有揭露,如果只有解構的話,它會抹除很多其他我們本可以與文學建立的關系。所以這個邏輯我想我這麽簡單一講,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這是批判最主要的限度,就是這樣的批評方法帶有某種特權性,帶有一種有罪假定的不合理的、過激的特征。
如果說我們按這樣一個情緒心態去讀文學,後面就會帶來一系列後果。一個主要的後果就是你不需要讀文學文本,基本上就可以有結論了,菲爾斯基管它叫自動駕駛。我相信大家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就是說你看一部作品,你嗅探出來,覺得這個導演應該是一個「大直男」,或者說他是我們女性主義不喜歡的東西,我們基本上還沒有看他的作品,就已經感覺到裏面會有一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這樣的話你實際上就沒有真正去欣賞文本,你主要是滿足於對它進行某種定性定調,或者是一個標簽式的解讀。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對於文學如果是以懷疑來驅動的話,漸漸地,我們就對文學就缺乏了愛,因為你要懷疑它,你怎麽還能去愛它呢?你怎麽還能夠信任它?其實這個已經變成了不僅僅是普通讀者,尤其是專業讀者的一種流弊。
大家可以去捫心自問,我們有多少文學系、英文系的同學,已經能非常熟練地寫出一篇文學批評的文章,甚至是專著,但是你對於文學的愛卻羞於啟齒,或者你沒有感覺到你有必要去談論這種愛情,你認為談論這樣一種感覺,談論你對文學文本的眷戀是一件不成熟的事情,你還是成為一個偵探比較酷一點。這是菲爾斯基說的第二個這種閱讀方法的問題。
第三點我覺得可能更本質一些。一旦這樣的批判思維成為主導,甚至成為解讀文學作品時的預設選項,那麽實際上對於文學在這個時代的功能,我們是沒有辦法去為它做出有力辯護的。因為那樣一來,文學作品無非證明某種社會科學理論或概念的證據。你想知道那個時代有一些什麽邪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找一本小說,這小說裏面就是罪證,小說人物的說話方式、它的主題、它的結尾正好證明了那個時代權力的某種在場或者是某種共謀。
那文學能幹嗎?文學就像一個pH試紙,它只能去測試這樣一些歷史性的東西,文學就被降格到一個次要的位置。對於我們真正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和熱愛文學閱讀的人來說,這其實是一件蠻可悲的事情。
所以菲爾斯基寫這本書有一個更大的語境,就是文學閱讀現在正迅速邊緣化,而且那些研究文學的人不熱愛文學,那些不熱愛文學的人,在課堂上教大家怎麽去閱讀文學,怎麽樣以不閱讀文學的方式去拆解文學,久而久之,更加沒有人知道我們為什麽要去讀文學作品,我們為什麽要浸淫在文字當中,最後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歷史決定論。這種歷史決定論就認為文學作品和其他事物一樣,都不過是由歷史最終來決定的產物,它是被動的,它是被塑造的,只是因為有這個時代,有這樣的一個社會,有這樣一個權力關系,才必然會產生這樣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可不可以去改變這個時代?文學作品可不可以去超越這個時代?大家就看不到了,所以這是非常消極的,而不是一種更加具有積極性的對文學本體論的建構。那菲爾斯基其實在批評方法上,同時也是在所謂的歷史主義認知上,希望能夠做到一些波瀾。
張德旭: 範昀老師也出版了一本專著名為【批判的限度】,但是我註意到範老師的英文書名叫The Boundary of Critique。limits好像有一點譴責的感覺,有點負面的色彩,但是boundary指分界,就是說這個是界限,界限以內的是批判可以做的事情,而這個界限以外是批判做不到的。所以不知道範老師對批判的態度是不是也是比較同情的,或者說您在書裏是怎麽理解當下西方這種文學研究的批判的?
範昀: 我之所以用限度而不用局限,是因為限度裏麪包含著某種空間隱喻,就是說我其實是想給批判提供一點保留,我始終覺得批判還是好的。那麽我覺得批判可能有三個含義,可以放在三個語境中去理解,一個是文學領域的批判,第二個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批判,第三個是我們經常講的一般性的批判。那麽我主要先從第二個領域開始講,批判,是當今人文社科幾乎所有領域都在玩的一個遊戲。
那麽我覺得它主要的問題是什麽?第一個是那些做批判的人會說自己其實關心的不是文學,而是政治。我從他們關心的角度來說,他們所承諾的政治事業其實並沒有取得成功,他們批判的資本主義依然很有活力,尤其是最近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他們所反對的右翼保守勢力,接二連三獲得了選舉的成功,所以在這點上其實是蠻失敗的。
那麽為什麽失敗?我覺得這裏面會有第二點問題,就是批判不夠批判,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種建制化了的批判,它是像時尚一樣,彌漫於所有人當中,沒有任何同儕壓力的一種批判。一般我們做批判的話,你其實是要獨立的,你需要勇敢,你需要別人不同意你,但是現在這些人做了批判,大家都很安全,而且還會暴露出很多矛盾,比如說你要關心底層,但是你寫那麽佶屈聱牙的文字,你怎麽讓普通人看得懂?然後你在某種程度上透過批判,實作自己事業的順利。所以我覺得菲爾斯基有的地方寫得蠻刻薄的,她說批判是度過中年危機的有益方式。大多數文學學者,包括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其實都是以波希米亞的姿態過布爾喬亞的生活,而他們對這種不一致性,我說得重一點,偽善性,甚至是習焉不察的。
然後第三點是包括我的社科的同事們,他們都認為其實這種模式在智識上非常懶惰,只要有一個規範就可以形成批判,好像規範就像幾何的全等三角形一樣,當這個世界不符合全等三角形,我就批判它不符合全等三角形,沒有任何跟現實之間的回應,給自己的思想也沒有造成更多的壓力。這是我覺得人文社科界的通病,然後進入文學領域,就是扼殺文學的獨特性,他們會把文學當成文化文本去解讀,也就是說在二三流小說和一流小說之間其實沒有本質的差異,因為它們本身都是同一個社會文化的產物,這裏面全都包含了意識形態,無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還是暢銷的二三流小說,它們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那麽文學的教育功能、在教化上的意義基本上都被消解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大型的critique本身,是在特定時期內由強烈的政治沖動而形成的一套批判話語,其實跟我們一般所說的批判還是有所不同的。其實我覺得一般的批判不能是一套理論或者說是一套綱領,它應該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它是一種人的心性,就是說你在跟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你能夠做出獨特的判斷,而不是那種陰謀論。
張德旭: 我感覺範老師的立場跟哥倫比亞大學的Bruce Robbins的觀點還挺相似的,因為【批判的限度】出來之後,這本書最大的批評者就是這位羅賓斯教授,他也是覺得批判沒有走到極端,而是遠遠不夠。因為他認為,尤其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產生以來,到現在,文學作品裏已經內含了批判。這是文化學者都預設的一種文學內涵。所以如果我們文化學者,甚至我們大學裏的文學研究者不去批判,可能會導致與商品文化、商品社會相媾和,和權力產生共謀,所以羅賓斯強調還是要繼續批判。
菲爾斯基在這本書裏反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種簡單的決定論,強調多重決定論,她參照拉圖爾的ANT理論,即行動者網絡理論,根據這個理論,一個事情或者一個文本的出現都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比如說我們喜歡讀哪本書,它背後不是權力的運作,而可能是我們父母喜歡這本書給我們推薦的,或者是我們小時候家裏邊恰恰有這本書,或者是我們上學的時候,課程大綱裏有這本書,所以我們與一本書的相遇其實不完全是政治的運作或者與權力的共謀。那麽文學批評也應該透過不同的因素去批判,而不應總是立足於階級、性別還有種族這些角度。
不過羅賓斯認為雖然因素確實非常多,但重要的因素只有幾個,而且因素之間還是有等級的,有的因素發揮的作用更大一點,而有的因素可能就沒有起到那麽關鍵的作用,而他覺得階級、性別、種族在當今仍然是至關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這個是學者之間的一種分歧,但我覺得他們沒有本質的沖突,包括剛才範昀老師提到的批判的限度,其實不是說批判已經走到頭了,像拉圖爾所說的油盡燈枯了,而是說大家的批判力還不太夠,尤其是專業文學研究者,好像只是把自己埋在舊紙堆裏,寫一些無關痛癢、不會改變社會現狀的文章,其實文學研究者可以做到更多。所以我們現在讀一本文學作品的時候,也會想一想可不可以透過描述對文學的熱愛、這種激情或者是其他的正面角度來取代原來以懷疑為基調的批判。
如何進行「後批判閱讀」?
但漢松: 菲爾斯基的基本觀點並不是說批判就全然是錯的,她只是說不能用批判作為認識文學的唯一路徑,我們應該多模態地容納多種情感、多種方法、多種認識論,是這樣一個兼收並蓄的閱讀,因此菲爾斯基肯定不會說我再給你一個方案,那不就是跳到自己的坑裏去了?所以她更加鼓勵的是,你可以有你的理解,比如有的人註重審美,有的人註重情感,有的人註重形式,還有的註重文化闡釋。大家都沒有哪一種是需要排斥其他人的,大家可以在一個闡釋的共和國當中不斷貢獻自己的想法。但這其實是一個願景。因為現在的西方也好,國內也好,大家更多的還是一種比較簡單化的流於俗套的批判模式。那麽它的根子其實還是在於左翼70年代以後所謂的文化研究的轉型,或者是身份政治。我們不再去強調一種宏大革命了,我們強調的是每個種族、每個族裔、每種身份,他有他獨特的生活經驗,那麽這種生活經驗是其他人必然理解不了的,於是我們批評文本該怎麽批評?如果你是女性讀者,你就要去強調我們女性的經驗一定是那些男演員、男編劇、男導演所無法捕捉到的,既然他肯定無法理解我們、共情我們,那麽他必然在他的作品當中要露出破綻來,於是我們就去抓到他的罪案現場。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我今天從網上打印了一篇【漫長的季節】的劇評,它就講【漫長的季節】塑造了這樣三個帶有濃重爹味的男性角色,指的是王響、馬德勝和龔彪,然後褒揚他們所形成的男性共同體,就這三個人總在一起玩,總在一起判案,這三人不是親兄弟勝似親兄弟,然後都在謳歌他們三個人,仍然是一種男權中心視角作祟,盡管刻畫了女性被壓迫和損壞的社會境況,但是這個電視劇對女性情誼的貶低和所包含的女性互害情節,仍然不失為一種潛意識的厭女。男人都是好的,男人都是互幫互助的,但是裏面的女性就互相出賣,給彼此下套,所有的女性都處於一個邊緣的、不健康的陰暗視野中。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菲爾斯基不是特別喜歡的出於身份政治的批評,因為它已經假定了,如果一部作品的女性視角跟男性視角不均衡,它就一定是有某種隱形的厭女癥,或者說是男權中心主義在作祟。所以如果你以這樣的方式去看【漫長的季節】,你可能看了兩集就想棄劇了。
但是這麽一部電視劇,除了有男性視角、男性敘事,其實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它有音樂,有剪輯,有道具,有整個故事講述的方式方法。如果我們看了這部電視劇,卻只盯著說男的聲音多還是女的聲音多,男的是主角還是女的是主角,我們其實就和更多這部電視想去特別真誠地經營的那些東西擦肩而過了。如果我們再有一點點耐心,你其實會發現這裏面所謂的王響、馬德勝、龔彪這樣一個男性共同體,確實是一個男性視角,但它並不是對男性視角沒有批判的,他們在裏面的「爹味」最後其實都倒向了某種對自我的反思和某種社會上的失敗。而因為這樣一種批評的自覺,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這是一個男性中心的文本,不能先入為主地去做這樣的判斷。我再舉另外一個可能會得罪一些人的例子,就是【你好,李煥英】。
【你好,李煥英】大家都看過,票房高達22億。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電影。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說,它非常討喜,女性導演,講的是女性的故事,還是母女之間的深厚情誼,跟【漫長的季節】在設定上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也是在講工廠大院裏的生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裏面完全是女性視角或者是女性視角為主,它其實就比較受到大家普遍的認可,覺得這是一部有進步色彩的電影,是一部好看的電影、感人的電影。
但是恕我冒昧,看了這部電影之後,我真的覺得裏面的很多細節、故事的講述挺粗糙的。大家可以看到豆瓣影評裏面有些人說得還是很準的,它好多都是小品拼湊出來的,一種小品的表演感非常濃,然後裏面的表演說實話也說不上很自然,有非常多刻意的橋段,尤其是打排球那一段。
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你看到了女性視角在中心,但其實它的文學性可能就會比較弱。那菲爾斯基是希望我們不要以一種簡單的身份政治,或者是你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來先入為主地對文學文本做判斷,而是要多把自己放在一個可以被文學影響的位置,文學是可以伸出一個勾點,把你hook住的。那麽懷疑文本的同時,你也要懷疑自己,你也不要把自己放到一個過於超然的位置上。我們現在很多影評人、劇評人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太超然的位置上,覺得自己可以俯瞰它,可以去對它進行一個整體性的解讀,但實際上我們與文學的交流是在很多層面上發生的,我們要看到這裏面的復雜性。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是菲爾斯基特別推崇的後批判閱讀。所以後批判閱讀不是一個具體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種意識,更多的是一種審美的多元性,更多的是一個批評者或一個讀者與文本的狀態或空間關系。
張德旭: 後批判的意識或者是這種精神沒有套路式的樣版,可以讓我們拿來就用。我們從側面也可以看到這種後批判的閱讀方式是非常困難的,反而要求我們對文本的敏感度極高,才可以說出一點有道理、有價值、有意思的結論。菲爾斯基在【批判的限度】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就在247頁,她說我們批評家「不是像老鷹一樣翺翔在高空,批判性地或不動聲色的凝視下方的遙遠人群」,而是應該像螞蟻一樣「跋涉前行,驚嘆於隱藏在深草中的復雜生態圈和各式各樣的微生物。這就意味著要放慢腳步,放棄理論捷徑,關註同伴行動者的話語,而不是用自己的話語來撤銷它們」或者覆蓋別人的話語。「換句話說社會性不是一個預先的存在,而是行動,它不是一個隱藏在表象領域之下的隱秘實體,而是多個行動者之間的持續的聯結、斷聯和重新聯結。」所以我們讀者在讀的時候應該放任自己在文本的深處跋涉、感受,去擁抱一切我們能接觸到的或者是落到我們身上的東西,或者落到我們心坎裏的感悟。
範昀: 剛才但老師提到【漫長的季節】,我馬上就想到了在豆瓣上看到今年暑假的電影【封神】的一則短評,大意是,為什麽只有爹而沒有媽?我確實是還蠻感慨的。我跟但老師其實差不多都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其實是逐漸地去遠離一種道德主義的文化,因為原先的時代對人的要求太高,反而會造就很多偽君子。我們逐漸覺得文學在幫助我們更好地去理解這個世界。這些年來從我在網上的體會來看,我覺得大家的道德審查意識越來越厲害了。一部作品有的時候你沒有辦法把這樣的一個局部拿出來,作為對整個作品蓋棺定論的標簽式的理解。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文學批評多多少少需要對這樣的現象負一點責任。
我們對待文學要更有平常心,其實就是多多少少要回到普通讀者的視角,因為普通讀者對文學的需求也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想從中求知,有的是想獲得純粹的快樂,有的作文寫不好,想學學人家的文筆,有的是想學習一下思想境界,有的甚至是把它當成某種信仰去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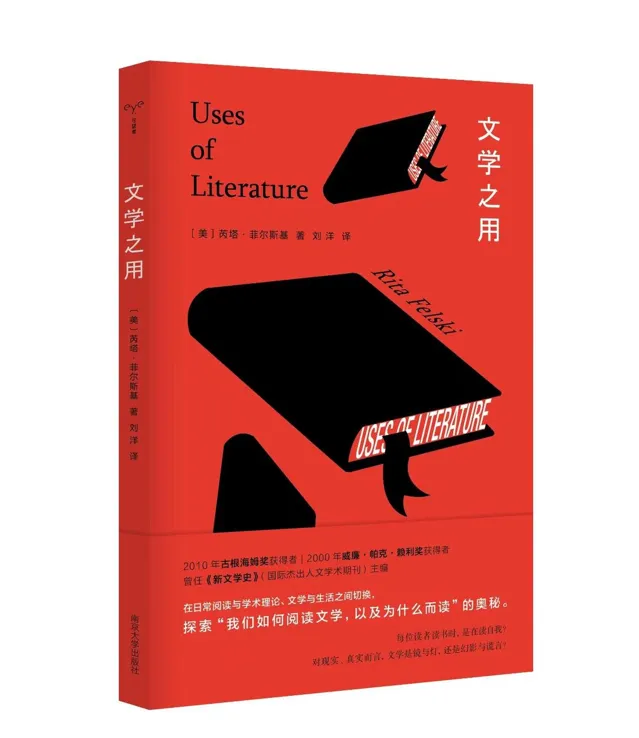
【文學之用】
菲爾斯基認為要走向後批判,我們需要增加更多的理論概念,這點我其實不是很同意。她在【文學之用】中說我們要搞新現象學,然後在【批判的限度】裏,她說我們要用拉圖爾的ANT理論,那麽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是所有的事物,不僅是人,而且是物,都有它的能動性,就是說你要把文本當成一個有靈魂的東西,你要去關心它,你也要對它進行回應,不能頤指氣使地去把它當作罪犯,或者說當作沒有任何靈魂的客體去審判。其實我覺得我們讀文學就是交朋友、向文本學習的過程,我覺得其實可以用一些更常識性的概念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麽菲爾斯基個人的批評其實做得不是特別多,那麽我能夠找到的一個案例在她的【現代性的性別】裏,她把19世紀文學放在一個更豐富的譜系中去理解。比如說最核心的一個文本就是【包法利夫人】。納博可夫認為包法利夫人只是一種非常糟糕的讀者,把文學的故事當成真事去理解,自己投入進去,而且看的都是二三流的小說。那麽納博可夫做的是一個純的形式分析,其實這種形式分析背後所強調的一些內容可以被女性主義借鑒,就是說其實這代表著包法利夫人是在消費文學品,在19世紀巴黎消費主義興起的時代,包法利夫人讀文學的方式跟她去超市裏買東西、買各種各樣奢侈品的方式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在這個語境中,女性被物化了,那麽傳統的女性主義一般會做這樣的解讀,就是說女性只要是喜歡消費都是不好的,都是整個男權結構的受害者,包括讀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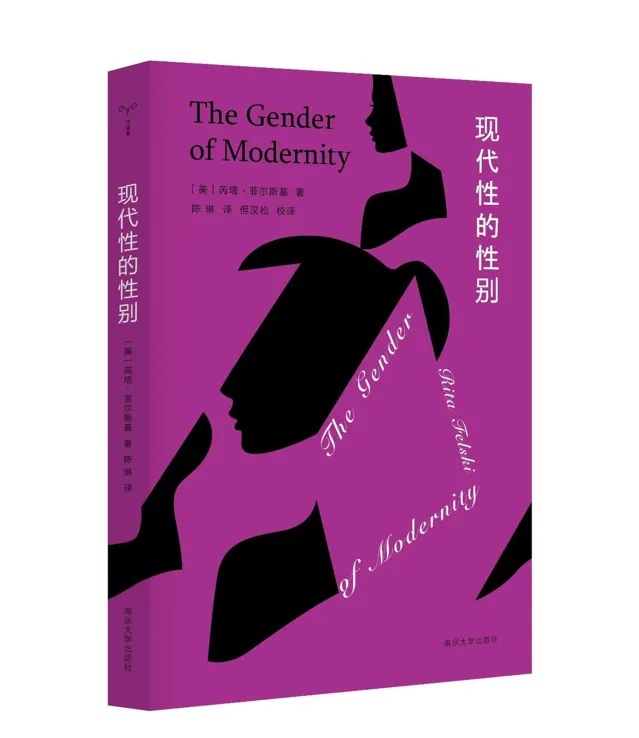
【現代性的性別】
那麽菲爾斯基的批判性,在我看來就是她喜歡說出不一樣的理解,她提出,消費為什麽就一定不好,消費的行為本身是不是也包含著一種有限的反抗,有限地想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有自主性的這樣一種訴求?菲爾斯基沒有規定別人應該怎麽去閱讀文學作品,這是她比較習慣的進入文學的方式,這種進入的過程我覺得大家也都看得懂,也會獲得啟發,這個事情有正面有反面,大家可以去更復雜地思考這個問題,不要特別簡單地看到物化就覺得是不好的,這對人的思維來說是一種僵化,所以菲爾斯基願意把這些問題處理得更加復雜、靈活一點,這是好的。
如何讓大眾重新愛上文學閱讀?
張德旭: 現在面臨的一個困境是閱讀的人好像比較少,文學閱讀者好像越來越少,因為我們現在要刷抖音、小紅書,每天好像很難給文學分一點時間,那麽其他的非文學研究者,比如說上班族或者是非英語專業的同學,他們為什麽要閱讀文學?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如何讓大眾喜愛文學,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任務或者目標,包括我們做大學教師、教文學的老師也很難讓學生去愛上文學。那麽我想問一下兩位老師,在當代21世紀大家壓力這麽大的內卷時代,為什麽要走進文學,以及普通讀者如何能夠愛上文學?
但漢松: 我們題目好像是如何讓大眾重新愛上文學,還不是愛上文學,是重新愛上文學。它其實包含了一個假設:曾經我們愛過文學。這個不難理解,比如說在19世紀小說興起的年代,那個時候沒有電影,也沒有電視,沒有電腦,小說是最強勢的一個文化載體。所以小說家那個時候可以成為整個國家文化趣味的引領者,這個是不足為奇的。所有有知識的人、有教養的人,家裏面都會藏有很多小說,那一本小說出來會成為整個一代人不斷去談論模仿,甚至去習得的物件。
現在為什麽大家好像不太讀這種所謂的文學小說,也不是不讀小說,還是讀小說的,讀那種修仙文、總裁文、穿越文,甚至我的一些大學同事都在看這些書,我就質問他們,我說你教亨利·占士的,怎麽能夠看網絡文學?他說我上完一天課真的很累,亨利·占士的句子太長了,我就看這些不過腦子的東西,放松一下。
有一個特別著名的美國藝術評論家叫格林伯格,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先鋒與刻奇】。他有個觀點很有意思,他認為並不能夠說在當下社會,刻奇就是萬劫不復的邪惡的存在,然後先鋒是至高無上的最光明、最光輝、最燦爛的東西。文學和大眾文學其實也是這樣一個情況,我們必須承認,嚴肅的文學作品、好的文學小說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邊緣化了,而且它必然邊緣化,就是你不可能再去像從前那樣,就是80年代乃至中國剛剛改開的時候,那個時候譯林社要引進一本什麽陀思妥耶夫斯基,你掙20塊錢你可能拿10塊錢去買,而且都要搶,那個時候新華書店都要排隊的,又進了什麽外國小說趕快去搶,拿到書,大家都快把書翻爛了,然後都去瘋狂傳閱,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這樣一個資訊時代,在快節奏的加速時代,我們整個註意力的模式已經改變了,我們人腦已經不太適應去長久閱讀一部漫長的小說,我們沒有那麽多註意力了。那麽在這種情況下,閱讀文學小說其實已經成了一種很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教文學,這個是蠻沮喪的,尤其是在英文系、在中文系是非常沮喪的,老師也不讀真正的文學,老師讀文學是為了寫論文,是為了發表,是為了評職稱。學生也不讀文學,學生偶爾讀文學也是因為要寫作業,為了刷績點。除此之外,大家不會主動去讀,所以怎麽去愛上、重新愛上文學,我想我今天不會在這裏做一個烏托邦式的呼籲,說大家都給我把小紅書、抖音刪了,全跟我一起去讀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去聊菲爾斯基也好,或者聊批判也好,我們其實只是想講,大家不要以為只有流行文學,只有那樣一種快速的所謂的消費式的閱讀,才是閱讀。
我們曾經還有過一種悠長的、綿密的、深入的、投入情感的閱讀,這種東西也許它不再是我們生活中的主導,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它徹底忘記,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的某一些時刻,或者我們應該訓練一小部份優秀的、有天資的讀者成為好的文學閱讀者,那麽他們可以去傳播文學閱讀的愉悅,他們可以在豆瓣寫下更好的書評和影評,他們可以將來再去當老師,可以向更多的年輕人傳播閱讀之美。總之它被邊緣化了,但是我認為它應該像古典音樂一樣,像古典學一樣是延綿不絕的,它是我們社會一個邊緣的存在,但它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存在。因為我無法想象,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沒有人願意再去讀好的文學性小說,這樣的一個時代可能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時代,因為它意味著我們不僅註意力潰散了,而且我們無法真正地去消化吸收和欣賞復雜的東西。
對於復雜性的熱愛和欣賞,我覺得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僅僅是藝術教育、人文教育,而且是公民訓練非常重要的組成部份。如果我們所有的閱讀都是看微信上的推播文章,5行加一張圖片這樣快速的、流動的碎片式閱讀,那麽我們的社會就沒有辦法產生一批合格的公民,能夠對社會的復雜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辯論,他們只會去站隊,他們只會去情緒性地宣泄和咆哮,他們只會被別人領著去發出同樣的聲音,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未來,是一個我不想去的未來。
所以我一直說我們的文學教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食古不化,或者是一種懷舊式的東西,而是說越是在這樣的時代,我們越應該訓練我們的閱讀,不要讓它徹底退化,不要讓它徹底消失,這個是我的願景。
範昀: 20世紀50年代,自電視誕生以來,就不斷有人開始問這個問題了,大家不願意做紙面閱讀,尤其是在數碼時代,閱讀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身邊的朋友、我的家人都不喜歡看書的,就不用說文學了,就不喜歡看書,也不喜歡關心什麽事情,有的時候覺得聊天也沒有能夠聊得比較投機的人,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就先不談。
要讓大家愛上文學,基本上不是我們能做到的事情。首先這就是一個大的時代趨勢。我自己的老師輩,他們能夠在80年代的某個清晨四五點鐘連夜排隊,據說新華書店到了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從北京進過來的,那時候杭州書很少,書店要早上7:30才開門,你隊先排著,剩下幾個人跑步,因為冬天。那就是饑餓感。
我看拉伯雷的【巨人傳】裏面也是這個意思,對知識的狂熱、饑餓感會促成一波文學熱。我覺得文學熱一方面是跟資訊的匱乏有關系,另一方面跟時代病有關系,就是說大家心裏是空的,有的時候需要這個東西。那麽我剛才講的就是說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文學熱跟特定時代的這種匱乏有關系,跟這種虛無感有關系。
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確實能跟文學競爭的精神產品太多了,比如說我去年輔導的碩士生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文學在年輕人的愛情中其實也差不多結束了,年輕人現在怎麽談戀愛的?他們基本上是去訂閱一些心理學的APP,還有談戀愛之前先去知道一下這個人MBTI是什麽,就是說心理學話語完完全全擊敗了浪漫主義的愛情話語。
我們這代人對愛情的憧憬完全都是文學塑造的,我們看那麽多【愛在瘟疫蔓延時】【呼嘯山莊】,等等,就說你對男女之間這種感情的向往也好,恐懼也好,都是跟文學相關的。但是現在年輕人不需要這個東西,因為他們需要更安全,需要掌控自己的生活,而文學其實沒有辦法幫助你掌控生活,它反而會讓你的生活變得非常動蕩,就是因為它有各種可能性、各種復雜性,但是科學意義上的心理學確實是有辦法去做到這些東西的,它提供的是一種效率,所以我覺得這本身就是個非常大的時代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每個時代其實不需要去鼓動,照樣有文學讀者,因為文學提供的那種東西,我參照一個德國哲學家本雅明的概念,文學能夠傳遞一種經驗,這種經驗是其他的所謂幹貨、知識資訊所沒有辦法取代的東西,就是說它其實是傳達一種感受,只不過我們這個時代,大家對共享創意的需求遠遠超過了對這種感性意義上經驗共享的需求。就是說大家不會去交流我們的經驗體會,我們更願意去交換資訊,你知道了什麽,他知道了什麽,你能夠教我哪種技能,那種感受的交換其實是變得越來越深了,但是我覺得文學教學和文學閱讀最核心的東西其實就是感受。我記性很差,讀完文學我基本上都會忘記,但是我唯一能記得的就是那種感受,但這種感受其實有的時候又蠻難傳達的,但大家還是要交換這種東西,有這種東西跟沒這種東西,我覺得還是不一樣的,尤其是我覺得從科幻小說的發展,就感覺得出大家對未來不大有信心,一般科幻小說都是末日情節,世界上發生的那麽多事情,帶給人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那麽我覺得文學在你比較脆弱的時候能夠加強你自己。他寫的可能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但是沒關系,傷心的故事也能夠給你力量,這就是文學跟一般社會新聞意義上的悲慘最不一樣的東西。其實我也怕空談這樣的問題。從我個人這些年的體會來講,我覺得文學最重要的還是從個體意義上去理解它的價值,就是說它能夠幫助你加強自己,讓你想涉及更多道德的復雜性的問題,去探尋什麽是好的生活。
那麽另一方面我在芝大訪學合作的導師努斯鮑姆,她更強調的是,文學在加強個體的同時,能夠幫助你成為公民,可以因而讓我們的社會生活變得更有共識,變得更有活力、更加強健。這個都是很空的,但是我覺得都是要透過大家的閱讀去體會的。
張德旭: 文學閱讀這種經驗不是資訊的獲得,對我們每個個體,尤其21世紀這種碎片化時代的個體至關重要。我們帶著這種文學閱讀的體驗,跟另外一個人相遇,我們交流我們這種隱蔽的、隱秘的思想或者情感,這樣的話才有可能達成某種深度的交際。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