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巍(章靜繪)
維特根斯坦這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是每一個哲學研究者都繞不開的人物。而普通讀者也往往聽過一些來自他的著作的金句,或是了解一些他作為天才的怪癖。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樓巍長期從事維特根斯坦研究,著有【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註解】,譯有【哲學研究】【論文化與價值】【藍皮書和棕皮書】。他最近出版了【維特根斯坦十講】(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5月版),用十堂課解讀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在接受【上海書評】的專訪時,他談到了語言在維特根斯坦哲學中的意義,以及維特根斯坦式的思考方法對我們的啟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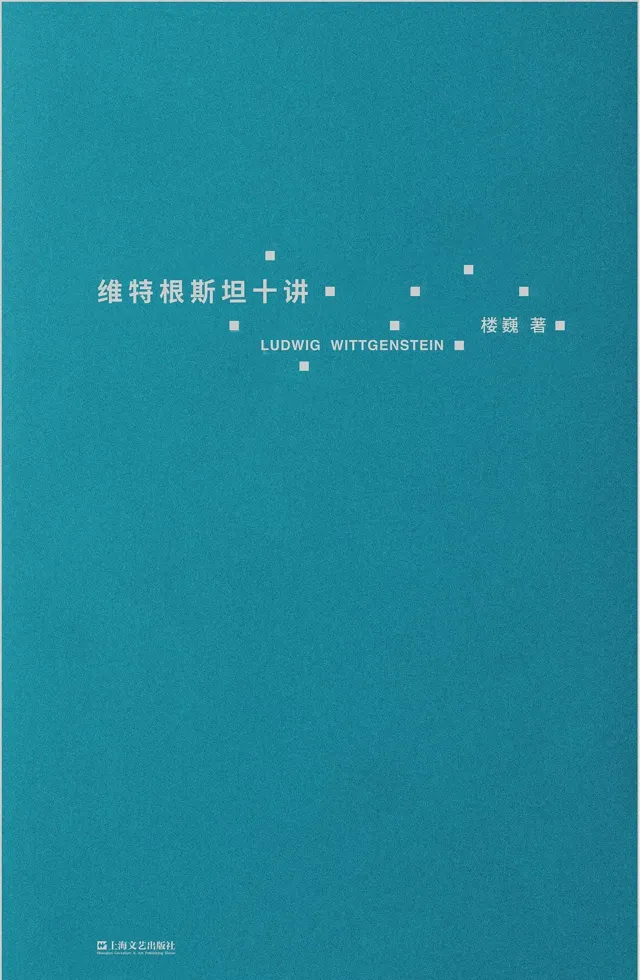
【維特根斯坦十講】,樓巍著,光塵/藝文誌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32頁,68.00元

維特根斯坦
能否請您談談寫這本書的緣起,以及維特根斯坦的現存著作是一個什麽狀況?
樓巍: 我做維特根斯坦,平常都是跟研究者打交道,交換觀點,相互商榷,時間久了,就想跳出研究者的小圈子,給大眾寫一本簡明通俗、框架性地介紹維特根斯坦哲學觀點的書。2013年,我在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書,給研究生講維特根斯坦,每年大概十六次課,我挑了其中一部份,重寫一遍,就有了這本【維特根斯坦十講】。
說到維特根斯坦的現存著作,其實在他生前只出了一本【邏輯哲學論】,英文版出版於1922年,此外就是一篇名為【一些關於邏輯形式的評論】的文章。1951年,他去世之前,任命裏斯為遺囑執行人,安斯康姆和馮·韋特為其作品保管者,這三人都是與他關系親近的學生。馮·韋特還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將維特根斯坦的作品存於何處,寫於何時,內容為何,講得很清楚。維特根斯坦除【邏輯哲學論】外的其他著作,都是在他去世之後,陸續由這些學生代為編輯出版的。維特根斯坦不喜歡寫結構完整的長文章,總是在筆記本上寫下一段段評論,這些評論構成了他的所有手稿。在這些手稿的基礎上,他曾讓打字員制作過一些打字稿,在此過程中又不停地對原內容加以修改和編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213號打字稿,即所謂的【大打字稿】。
編輯、整理維特根斯坦著作的過程是漫長的。首先出版的是最為成熟的【哲學研究】(1953),該書的第一部份是維特根斯坦親自編輯過,已經形成打字稿,明確想要出版的。之後,編者對剩下的手稿和打字稿進行編輯和整理。英國比歷克威爾(Basil 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的十四本英德對照的維特根斯坦著作集,從最初的【哲學研究】,到最後的【關於心理學哲學的最後著作(第二卷)】,中間間隔了四十年。除此之外,比較有代表性的文集,一個是德國蘇爾坎普(Suhrkamp)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八卷本德文版維特根斯坦【著作集】(Werkausgabe),另一個是200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與挪威卑爾根(Bergen)大學維特根斯坦檔案館共同編輯推出的電子版【維特根斯坦遺著集】(Wittgenstein’s Nachlass: The Bergen Electronic Edition),包含了他全部的手稿、打字稿、口述的筆記,都轉成了可以機讀的電子格式,全部在網上公開。這個專案的負責人是卑爾根大學哲學系教授、維特根斯坦檔案館館長皮奇勒(Alois Pichler)。這套電子文集對研究者而言雖然很有用,對大部份讀者來說都過於專業了。
自從雷·蒙克那本傳記【天才之為責任】中譯本出版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一股「維特根斯坦熱」,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維特根斯坦作為天才的人生經歷散發著獨特的魅力。我們應該怎麽理解他的人生態度?
樓巍: 我總結了維特根斯坦的四個精神特質。一、他對音樂和機械——也就是所謂的「鋼琴與鋼鐵」——一生都很喜歡。二、他厭棄矯揉造作的人與事,例如不少哲學著作的文風。三、他對精神生活保有一種純粹的熱愛,願意投身其中。四、他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抱持一種批判和疏離的態度。理解了這四個精神特質,差不多就理解了維特根斯坦的全部人生。我在【維特根斯坦十講】的第一講「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中有詳細討論,可以參考。
有意思的是,維特根斯坦對不少哲學經典是不屑的,對哲學史也很漠然,他愛讀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還喜歡偵探小說和偵探電影。他本人的閱讀興趣是怎樣的?這與他的哲學思想之間有怎樣的關聯?
樓巍: 像弗雷格、羅素這些與他同時代的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是感興趣的,讀得也多。弗雷澤的【金枝】,很厚的大部頭,他讀得很仔細。你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這些作家,奧古斯丁、帕斯卡這些哲學家的著作,他都愛讀,他也讀柏拉圖。而黑格爾他從來就不喜歡——黑格爾讓他抓狂。當然,像我們國內所提倡的,研究哲學先系統研究一遍哲學史,這個習慣維特根斯坦肯定是沒有的,原因很簡單——他喜歡從哲學根基處去把握問題。我們從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觀點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過去的很多哲學其實是一種誤解,例如,形而上學的命題其實就誤解了語言的邏輯。籠統說來,他對很多的早期哲學都持這種否定的態度,而在他自己所處的時代,他認為很多哲學是一種「哲學病」,正因如此,他對系統性地研究哲學史是不感興趣的。
維特根斯坦曾經非常強烈地想要移民去蘇聯,這該怎麽理解?
樓巍: 維特根斯坦在劍橋的時候曾經跟別人說,他自己內心深處是個左派。不過,他不是那種清談式的沙龍左派,而是身體力行。他捐贈了所有的遺產,因為他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偶然——因為偶然,他才成為一位大富翁的兒子。他追求的是一種必然性的人生,這種必然性在於,你只有對社會或者對某個共同體有貢獻,你才能有一口飯吃。他去清苦的奧地利山區做小學老師、去修道院當園丁助理,就是想要透過勞動來獲得屬於自己的生活資料。在他看來,當時的蘇聯就代表這種他認為符合必然性的生活,與他所厭惡的歐洲資產階級的生活是不同的。
提倡邏輯實證主義、進行分析哲學研究的維也納學派或維也納學圈,受到【邏輯哲學論】很大的影響,不過維特根斯坦對他們的看法似乎比較微妙。我們該怎麽理解?
樓巍: 維也納學派或維也納學圈的成員中,像石歷克和魏斯曼,維特根斯坦和他們的關系都是不錯的,會定期一起討論,魏斯曼也曾經寫過一本與【邏輯哲學論】很像的書,試圖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解釋清楚,只是篇幅要厚很多。你想要去了解【邏輯哲學論】,看魏斯曼的書也挺有幫助的,相當於對維特根斯坦做了詳細的展開,然後補充了很多論述,又覆寫了一部份內容。維也納學派雖然有個宣言,其實更多像是一個松散的小圈子,很難說是一個整齊劃一的學派,像紐拉特、卡爾納普這些成員,思想都不太一樣。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提倡科學精神,對傳統的形而上學——也就是在他們看來說不清楚的東西——是嗤之以鼻的。相當程度上,他們是透過哲學來回應二十世紀物理學和數學的進展,像卡爾納普就很明顯,他的哲學是完全科學化、分析性的。
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學派是不太感冒的。就以石歷克和魏斯曼為例,維特根斯坦認為這兩個人對【邏輯哲學論】只理解了一半。維特根斯坦確實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出,有意義的語言只能去言說世界中「可能的事實」。然而,在石歷克和魏斯曼看來,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宗教、倫理和美這些不可言說的領域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維特根斯坦的意思是,這些領域不存在事實,所以沒法言說——語言的功能就到此為止。按石歷克和魏斯曼的想法,美、道德這些人類歷史上真正重要或者說有價值的東西,就一下子給去掉了。這就是維特根斯坦不喜歡維也納學派的原因,在他們看來,不可被經驗驗證的美和道德都是不重要的,而維特根斯坦恰好認為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語言的作用是有邊界的,語言比較humble,它只能做它能做的事情,一些更為重要的東西恰恰是語言不可說的。
有一個經典的說法,就是存在「早期維特根斯坦」與「晚期維特根斯坦」之分,現在又有人提出,還存在一個「轉型中的維特根斯坦」,一下子制造出了三個維特根斯坦。對此,您怎麽看?
樓巍: 現在還有一個「最後階段的維特根斯坦」,真要細究的話,維特根斯坦大概有五個。雖然很多人肯定不會同意,但是在我看來,維特根斯坦只有一個——早期、中期、後期都是一樣的。他自己跟學生說過,他的思想成型得很早,二十歲之後就沒有再變過。對我而言,雖然維特根斯坦後來處理的問題與早期不一樣,他思想的核心實際上沒有變化。讀【邏輯哲學論】的時候,我可以看到,很多層面上維特根斯坦那種很微妙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和【哲學研究】是一致的。
我們應該怎麽理解【邏輯哲學論】?它在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之中占據著怎樣的地位?
樓巍: 【邏輯哲學論】觸及了很多弗雷格、羅素曾經研究過,但是沒有解決,或者說在解決的時候遇到困難的問題。維特根斯坦最終解決了這些問題。所以,【邏輯哲學論】實際上很多內容是在回應羅素和弗雷格,但是,把這些哲學史的東西去掉,它自己的框架是:「語言是世界的圖畫。」這樣一來,這個世界中可能的事態都包藏在語言之中。同樣的道理,語言就被封閉在了一種跟世界的描畫關系之中。既然被封閉在了這種描畫關系中,很多東西都不可說了,它只能去言說世界中可能的事實。在這樣一個語言系統之中,它有基本命題,有邏輯常項(比方說,「如果、那麽」),然後借助這些邏輯的勾點,構造成一個越來越復雜的語言系統。世界中可能的,語言中也是有意義的;世界中不可能的,語言中也是無意義的。理解了這個描畫系統,你就會發現,倫理、審美和宗教領域不存在這種所謂的事實,因為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說法,事實都是偶然如此的,其反面都是可能的,比如我是一個男的,這是個事實,但我也可以是個女的,這在邏輯上完全沒問題,所以它是偶然的,而美學、宗教和倫理領域並沒有什麽事實(事實都可以有反面),比如「人不該作惡」的反面即「人應該作惡」,無論怎麽說,都是不成立的。
以這樣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宣布他解決了所有哲學問題,因為以前所有的哲學著作都在使用這樣一種語言,按照他的想法,這種語言肯定是誤解了語言的邏輯,或者說其實是無意義的語言。他認為,以前的哲學試圖用語言去說宗教、倫理和美,而這些東西其實是無法言說的。
維特根斯坦說過,邏輯是思想的本質,然後您也提到,對早期維特根斯坦而言,邏輯是使思想、語言和世界處於完善的秩序之中的東西。對此,我們應該怎麽理解?
樓巍: 這個就比較復雜了,我試著簡單表述一下。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裏說過,思想把它的法則同時頒布給了世界和語言——一股濃濃的德國哲學的味道。對他來說,語言就是思想的表達,思想可能是我們內在的東西,語言是外在的、公然的東西。世界中可能的情況都是可以被思考的,所以,思想同時把它的法則頒布給了語言和世界,這樣一來,就使得它們處在一種完善的秩序之中。這裏「完善的秩序」其實是說,在語言中可能的東西,在世界中就可能,在世界中可能的東西,在語言中也就可能。任何一種可能的情況都對應著一個有意義的語言,而任何一個有意義的語言都對應著一種可能的情況。我們可以舉開車為例,你在路上行車,左轉是打一種轉向燈,右轉是打另一種轉向燈,直行就不開燈,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可能的情況了——你又不可能飛起來,對不對?這三種情況,在汽車轉向燈這種表達系統中可以完善地得到表達,接下來不可能出現它不能表達的情況,因為交通規則早已規定好了,汽車轉向燈的表達系統中只有左轉燈、右轉燈和不開燈這三種符號,然後這三種符號也只對應左轉、右轉與直行這三種情況,所以,它是一個完善的表達系統,不存在某種可能的情況,這個表達系統無法表達,或者表達系統表達了出來,汽車無法執行。實際上,語言和世界就處在這樣一個關系之中,只是這種關系要復雜得多。
哲學史上存在一個從關註本體論到關註認識論再到關註語言的演變過程,維特根斯坦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樓巍: 我書裏參照了哈克(Peter Hacker),他是牛津大學教授、最有影響力的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詮釋者之一。哈克評價說,維特根斯坦給了哲學一個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語言學方向。對符號和語言的重視,可能從羅素和弗雷格就開始了,在維特根斯坦這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最重要的就是語言,他甚至將整個世界都收納在了語言之中——在【邏輯哲學論】中,他這樣說過:這個世界所有可能情況收納在一套有意義的語言(基本命題的總和)以及它的相互組合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維特根斯坦是哲學的語言轉向最為關鍵的決定性人物 。
您提到,羅素想要理解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簡直是絞盡腦汁。為什麽對羅素這種大哲學家而言,理解維特根斯坦會那麽困難?
樓巍: 我始終覺得,羅素(以及弗雷格)無法理解【邏輯哲學論】,恰恰在於他們認為語言是沒有界限的,語言應該是全能的(almighty),我難道不能用語言來表達任何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嗎?維特根斯坦恰好相反,他認為語言是有界限的。我隱約覺得這是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最大區別,羅素對語言所抱持的想法是極為樂觀的,而維特根斯坦則非常悲觀——他們之間存在這種精神特性上的根本不同。很多人對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恩怨很感興趣,我認為,他們其實沒有什麽恩怨,維特根斯坦對羅素很尊重,他對羅素的哲學觀點批評很多,是因為他比較了解。我在第九講中,總結了他們的哲學路線存在哪些根本性的不同。
說到這兒,讓我想到您在【維特根斯坦十講】的第九講提到休謨的農場主問題,其中也涉及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的批評,能請您展開講講嗎?
樓巍: 這涉及歸納的問題。比方說,你相信明天太陽會升起,如果有個人問你,你憑什麽這麽相信?其實你能給出唯一的回答是:因為以前太陽每天都升起。如果一個強烈的懷疑主義者問你:就算太陽以前每天都會升起,憑什麽明天就會繼續升起?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從今天到明天,你是沒有一個跨越的通道的。這就是歸納的問題:你憑什麽用一件事情以前經常發生來作為它接下來還會發生的根據呢?我們很容易設想它接下來不發生,對不對?
那麽,這個時候該怎麽辦呢?羅素對此的想法是,一件事情以前經常發生可以作為接下來發生的根據,他認為我們的語言遊戲有一個理性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他的歸納原則(principle of induction)。維特根斯坦恰好相反,在我看來,羅素提出的歸納原則,簡直被維特根斯坦駁斥得體無完膚。他認為,不需要為我們玩的語言遊戲辯護,試圖給它提供根據是沒有必要的。我們為什麽要玩這個遊戲?我們為什麽這麽玩這個遊戲?這些都不需要解釋。我們之所以會說,一件事情過去一直發生,接下來還是會繼續發生,其實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是這樣玩這個遊戲而已。
維特根斯坦之所以認為,語言遊戲或者說我們的語言是沒有基礎的,或者說不需要辯護和解釋,原因其實很簡單:解釋語言也需要使用語言,那麽,你怎麽解釋你用來解釋的語言呢?他認為,用語言解釋語言這種事情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一條不歸路,就相當於一條小狗自己追自己的尾巴一樣,這是追不到的。
這就來到了一開始您說的,維特根斯坦認為很多哲學都提錯了問題,或者說,是一種對語言的誤解。
樓巍: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你如果實在想這麽玩哲學,那也可以,你就這麽玩吧,只是,你不要把它當成一種嚴肅的哲學。所以他說過,哲學可以完全由笑話組成。你也可以把哲學當作一種脫口秀來玩玩。
那句經常被參照的名言,「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沈默」。您吐槽說,大家不斷地參照這句話,但是又不斷地誤會。對這句話的準確理解是什麽?
樓巍: 「凡是不可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沈默」,這句話指向的是宗教、倫理和審美這些更高的領域,換而言之,它是有一個具體指向的,不是可以隨便參照的。維特根斯坦想說的無非就是,這些更高的領域,我們是無法言說的,語言能夠處理的僅僅是語言範疇之內的東西,而【邏輯哲學論】就是在處理這樣一個問題:究竟什麽是語言範疇之內。我覺得,維特根斯坦這句名言就好像一根結束了所有討論的手指,它指向的是劃定的語言範疇之外,那些不可說的、更高的領域。
前面聊了很多【邏輯哲學論】,關於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以及【藍皮書和棕皮書】,您打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說維特根斯坦關於語言的觀點,從【邏輯哲學論】到【哲學研究】以及【藍皮書和棕皮書】,就好像從「光滑的冰面」回到了「粗糙的地面」,對此我們該怎樣理解?
樓巍: 大家不是都說,【邏輯哲學論】與【哲學研究】是對立的嗎?維特根斯坦自己也說,不要把他的前期思想和後期思想放置在一起出版,這好像就體現出了一種對立。那麽,我索性就直接把這種對立總結為「光滑的冰面」和「粗糙的地面」。
後來還有一個比喻,可能更好。維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學認為語言是「可能的事實」的圖畫,把語言當作一種無差別的、單一化的、抽象的東西,這就像是透過地圖去看城市,無論重慶還是上海,從地圖上看,其實都是一樣的,都被縮略成了點和線。而維特根斯坦後期的哲學,我認為是一種在城市中散步的感覺,這樣一來,你會看到更豐富的細節和更粗糙的顆粒,在上海行走和在重慶行走肯定是不一樣的,對吧?於是,你就會發現,語言的各個領域是很不一樣的,例如形容詞和名詞就很不一樣。
說到比方和舉例,您在書中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而且有些例子本身就是維特根斯坦自己用過的。比如,他向學生總結他的教學目標,就參照了【李爾王】中的句子:「我將教你看到差異。」維特根斯坦透過什麽樣的方法來教學生看到差異?
樓巍: 一般人提出一個觀點的時候,這個觀點的根據或基礎,其實往往是一些語言使用的例子。對這一類觀點,維特根斯坦就會給出更多的語言使用的例子,透過這些例子讓你知道,其實你這個觀點是不全面的,或者只是一部份性質。所謂「看到差異」,可以簡單理解為讓你看到那些不一樣的東西。你看不到差異,就會覺得語言是一樣的。你看到差異,就會覺得每個詞都是一個工具,不同工具的用法是很不一樣的。比方說,像「羅素」「蘇格拉底」這樣的詞都對應著一個人,在此基礎上,我們會覺得,是不是所有的詞都應該對應一個人或一個東西。這就是看不到差異。
實際上,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一開頭就提出,很多詞沒有這個對應的東西,比方說數詞,「3」這個詞對應什麽呢,我們無法找到某個跟它對應起來的東西,然而,它似乎又可以對應任何三個東西,三頭牛、三杯水,等等。這裏我們就可以發現,沒有對應的羅素這個人,「羅素」這個詞是沒有意義的,而「3」這個數詞和「羅素」就不一樣。再如形容詞,「紅色」對應什麽呢,我們也無法找到一個跟它對應起來的東西,但是,所有紅色的東西都可以被它言說。又如「今天」這個詞也沒有什麽與它對應的東西,難道它就沒有意義嗎?顯然也是有意義的。維特根斯坦就是以這種方式讓我們去看清楚,詞語在我們的語言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前面提到,每個詞都是一個工具。維特根斯坦就舉過一個例子,他說詞語好比操縱桿,每根操縱桿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但是你拉動這根操縱桿是開啟離合器,拉動那根操縱桿就變成踩下剎車了,基本用法是很不一樣的。
有人提到,維特根斯坦雖然致力於反對形而上學,可是他的著作後來成為一種新的形而上學,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樓巍: 因為維特根斯坦自己說過,傳統意義上的哲學是徒勞的,試圖透過這種哲學尋求答案的人,就像是被困在透明的玻璃瓶子裏的一只蒼蠅,試圖透過撞擊瓶子的側面來逃脫,而他的哲學就是要給玻璃瓶子裏的蒼蠅一條出路。於是,就有人評論說,維特根斯坦號稱要把蒼蠅從玻璃瓶子裏面放出去,可是他不也是陷在自己那個體系裏嗎?他自己不也是一只瓶子裏的蒼蠅嗎?這肯定是不對的。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特點是什麽?他的哲學的特點是,永遠以語言實際上如何被使用為前提。我們的生活一直在變,語言的用法也會變,實際上,維特根斯坦並沒有建立起一套一勞永逸的理論體系。所以,他的哲學是開放的。在我看來,他其實是提供了一種做哲學的方式或者說思考的方式,而這種方式是可以真正被實踐和套用的。
維斯根斯坦這種開放的哲學作為一種方法的意義,能否請您談一談?
樓巍: 記得以前有一則新聞引發了轟動,一位筆名叫陳直的農民工(其實「農民工」這個說法有點誇大其詞了,那時他是廈門一家工廠的工人)轉譯了一本【海德格爾導論】,想要出版。很多人質疑說:一個農民工,懂什麽海德格爾?這個時候,用維特根斯坦的方式,我們就可以反問:說陳直不懂海德格爾的那些人,他們自己懂不懂呢?他們憑什麽說陳直不懂海德格爾呢?假設那個質疑的人是一名大學教授,一般人會覺得,大學教授肯定要比農民工更懂海德格爾。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繼續往下問:為什麽一個大學教授就一定更懂海德格爾呢?因為這個教授是被專家評出來的嗎?被專家評出來的人就一定更懂海德格爾嗎?你用維特根斯坦的方式追問下去,什麽叫「懂」海德格爾,什麽叫「更懂」海德格爾?誰來評判」懂「不」懂「海德格爾?這些問題一旦提了出來,其實很多東西就被解構掉了,就好像一個繩結松解開了一樣。本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這種質疑,好像也就接受了,確實,一個農民工,怎麽會比大學教授更懂海德格爾呢?往往在最淺表的層面上,我們就停止了追問,可是,如果你繼續追問下去,可能這個節結就被解開了,然後情況也就發生變化了。
我覺得,這就是維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他自己也說,他是一個商人的孩子,商人做生意,總是要把事情搞定,用他的原話來說,就是get things done,他的哲學也是一樣——要把事情搞定。這其實不是我們日常所理解的做哲學的方式,日常所理解的那種做哲學的方式,其實就是,你提出一個觀點,我又提出一個觀點,大家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互相商榷,把它搞成一個紅紅火火的圈子遊戲,大家都來玩。而維特根斯坦不一樣,他喜歡把事情搞定,就到他那裏為止,把事情徹底聊清楚,聊完你就得到了治療。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種治療哲學。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