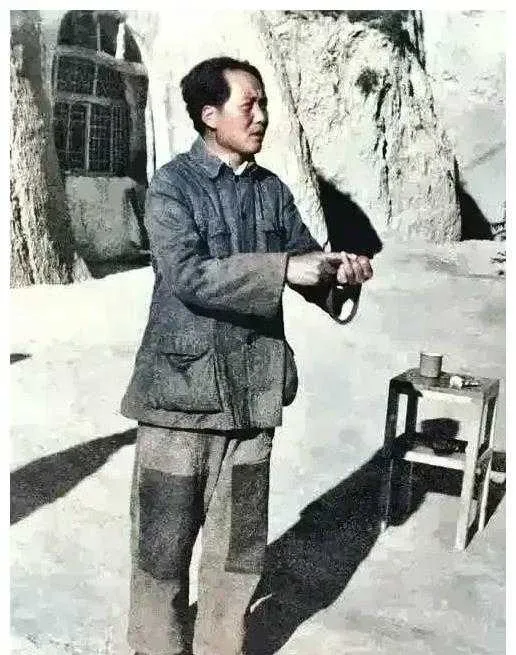「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
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
我住在一個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裏。
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 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
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