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故鄉,或許是走不出自己心的皈依。
一
走了半生的路,卻始終沒能走出故鄉的土地。
故鄉是什麽?故鄉是黃昏的老屋,風雨飄搖而溫馨永存;故鄉是門前的老槐,枝葉飄零卻生命旺盛;故鄉是潺湲的小河,默默無語但川流不息;故鄉是散發著青草香味的泥土,變遷不盡可氣息氤氳。同樣的意思,我在另外一篇散文中做過同樣的表述,只是,那時說的是祖籍。
祖籍而故鄉,故鄉而祖籍,無非就是那片曾經生活過的土地。
做夢時,永遠是在故鄉。夢中的自己,沒有年齡,也沒有身體,只是一個概念,一個和誰一起做事、說話,或愉悅,或驚恐,或緊張,或舒心的存在。夢中的故鄉永遠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石頭鋪就的街道,石頭砌壘的院墻,石頭碾子,石頭磨盤,石頭窯洞。河裏捲動著卵石,地邊堆放著碎石……這是石頭的世界,石頭的天地。
堅硬是故鄉的精神,故鄉的特質,但松軟溫馨的泥土,卻是她的本質,一如母親的懷抱。
一腳踏上她松軟而溫馨的土地,就有一種踏實的感覺從腳下升騰。
終於回來了!
但這裏的一切已不同於夢中,一切都變了樣。
沿著石砌的小街,行走在濕漉漉的雨中,沒有雨傘遮護,一任細雨打濕你的臉,你的頭,你的肩,你的上衣,你的腳。小街很短,走不了多久便到了頭。佇立在雨中,想尋找童年的影子,可眼前的景色,與心中的記憶,使你產生疑問,這是我走了半世的故鄉嗎?
侯詎望。
一張紅撲撲的臉從誰家門後閃出,粉紅的衣衫,漂亮的蝴蝶結,張望著雨中的人影。回頭去,卻是一扇緊閉的大門,門上斑駁的對聯依稀是數十年前的遺痕。小姑娘去了哪裏?她是我曾經心儀的美人嗎?她好嗎?她嫁到了哪裏?嫁給了誰?那人待她好嗎?
我永遠不會知道,因為我不會去破壞這已經平靜的心緒,不會毀壞這心中雕塑的神聖,也不會改變這已經寧靜的平衡。
我知道,時間的腳步碾碎了許多人的許多甜夢,我的夢無非是這無數夢中的一個而已,別無其他深意。夢的種子,會在現實的時空中開出無名的小花,一如這惆悵中立在深秋的野花,頂著風雨,鮮艷而寂寥地盛開。
牛羊的叫聲早已遠去,沒有雞鳴,也沒有狗吠,放牛人的鞭聲呢?誰在喊孩子回家吃飯吧,那麽急迫,那麽生硬,誰呢?母親嗎?細聽卻沒有聲音,只有雨聲越來越急,越來越大。
故鄉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是每一位遊子心中的牽掛,心中的聖地,心中的殿堂。故鄉是心中溫習一遍又一遍的功課,讀她千遍萬遍都不覺厭煩,見她千次萬次都看不夠,撫摸她千回萬回都親切如初。
這就是故鄉。
二
躺在村莊對面的山坡上,嗅著雨後泥土中散發出的清香,這是城裏多少年未曾感受過的氣息,溫馨而親切,舒爽而欣悅。故鄉的氣息,只有與她生活過的人才能辨別出來。草欣欣然,莊稼欣欣然,樹木欣欣然,飛過頭頂的鳥們欣欣然,一切皆欣欣然。這與自己的心情有關。當我們高興的時候,甚至連狂吠的野狗的叫聲,聽來都是悅耳的歡呼。我們常常被自己的心情左右著而不自知,以為是外面的境界左右著我們的心情,其實恰恰相反。
快樂是我回到了故鄉,快樂是我可以再次親近這裏的土地,快樂是我知道我的故鄉還是過去的故鄉——雖然她顯得蒼老而陌生。
多少年來,我們與腳下的土地在走遠。
我們好久沒有這樣呼吸過青草的氣息,牛糞的氣息,莊稼的氣息,泥土的氣息了。

今天,對,就是今天,你回來了,土地在你身上烙印的記憶重新接上了密碼,她說:是的,是的,你就是這片土地的兒子,你從這裏出生,你或許將來還要回到這裏。你有了一種異樣的情愫,有了一種葉落歸根的感覺,有了一種腳踏實地的沈靜和安詳。你感動,感動得熱淚盈眶,淚眼婆娑。
故鄉的氣息就是這樣。
青草的味道,是那種很好聞的味道,除了在山坡上,也在飼養棚裏。那裏成抱成抱的青草,切碎了,餵給那些出力的馬呀,牛呀,驢呀,它們熟悉這味道,它們是這味道的鑒別者,它們打著響鼻說:對了,就是這樣。
三
老槐樹見證了這裏的一切,年長者的離世,幼小者的成長,遊子的回歸,打工者的遠走他鄉。在這株老槐面前,一切都是秘密,一切又都不是秘密。
故鄉的秘密在村民的記憶裏,在老爺爺代代相傳的故事裏,在老奶奶一遍又一遍的童謠裏,在小夥子相互調侃的玩笑裏,在大姑娘回眸一笑的眼神裏。
然而,故鄉真的有秘密嗎?我開始懷疑,後來是肯定,再後來,我也有些迷茫了。有些東西,或許就是秘密,或許只有這塊土地的人才明白,或許走出這道山溝,別人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麽,做什麽,想怎樣了。
村街的夜是清涼的,微風輕拂將夜的味道送過來,那是怎樣的氣息呢?舒爽而新鮮。乘涼的人們端著海碗走出家門,那多是成年的男人,還有我們這些不更世事的小人兒,我們在默默地吃飯,默默地傾聽,或在街上東邊西邊瘋跑,反正,夜是我們的,是屬於這個寧靜安詳的小山村的。
這是生長故事的土地,這些故事就是這裏的秘密。
民間故事的起因有好多種原因,反正,一個話題被提起了,便引出了別人的故事。比如,劉秀「走國」吧——劉秀與這個小小的山村有何關系呢?似乎八竿子打不著吧?有人會告訴你,其實,劉秀來過這裏。話說當年,劉秀下凡,從天上來到人間,與二十八宿約定好,要到人間拯救衰敗的西漢政權,到了人間,約好保駕的大臣卻分布在各地,劉秀要靠兩只腳走路,尋找回這些失散的大臣,以便起事奪取政權呀。這樣就走到了我們這裏。
別人會問,何以證明呢?
那人會慢慢悠悠回答,隔山那邊的川幹,其實不叫川幹,而叫「酸泔」。當年劉秀走到那裏,時近中午,又渴又幹,走進一戶人家,說:老人家,給口水喝。老人猶豫了半天,說,先生,我們這裏缺水,想喝水卻是沒有,有漚酸菜的菜湯,客人將就喝兩口吧。劉秀接了老人的酸菜湯一喝,差點把牙酸掉。抹抹嘴,嘆口氣說:唉,好窮的「酸泔」呀!於是,川幹就這樣叫出來了。
有人不服氣:你見來?
那人依然不緊不慢:只有古來話,誰見過古來人。
話題從此轉到是否有古來人的神話上。
有人說——說話的是位老者:早年間,張家莊有個誰?「誰」是我說的,老人當時說的是張某某——有一年冬天往川幹送炭。路過一家門口,他告一塊兒趕腳的同道說,上一世,他就生活在這家人家,死後,投胎轉生到了張家莊。說完這話時間不長,他就肚子疼得走不了路啦,他趕緊拜菩薩,懺悔自己的罪過,過了一陣才好。從此,他再不敢亂說。到底他是胡說,還是真有轉生這回事,誰知道呢!
可不真有啊!另一個說:也是張家莊人,從小沒念過一天學,也沒離開村子出外跑過買賣,也沒人教過他,居然能講整本的【三國演義】【水滸】。
在這樣的文學啟蒙環境下,想不著迷文學也難。文學的根就是在這樣的夜幕中開始發芽,最後逐步生長起來的。如果說今天自己能夠寫一點讓人還稍微感點興趣的文字,是這片神秘的土地遺傳的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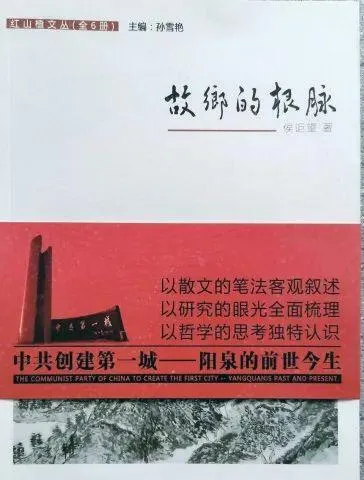
故鄉迷人的夏夜,就在故事裏進入夢鄉。其實故事不獨生長在夏夜,冬夜微弱的油燈下,同樣適宜故事的生長。漫長的冬夜,四周一片靜寂,連狗的叫聲都聽不到,雪落在房上,草垛上,門洞裏,井台上,窸窸窣窣,透過玻璃窗凍結的冰花,一亮一亮的雪片斜斜飄下來,美麗如童話。一家人圍坐在熱炕上,油燈的燈花一爆一爆跳躍著,歡快而溫馨。不是為了說話,不是為了叨咕,手裏剝著玉米粒,為給不善熬夜的小輩們一點精神,長輩便開始說故事。那依然是生長在這片土地的故事,比如藏山大王的故事,比如仇猶國君的故事。都是與腳下的大地有關的生存密碼。
真的,故鄉真的有好多民間故事,北面有「碧屏山」,又叫陸師嶂的,那裏有六位得道高僧從山中的六師洞中消逝了,至今不知所終;東面川幹的故事就不說了;西面張家莊也充滿了故事,南面的禁山裏,也有說不完的故事。只是,這個小小的山村,卻如謎一樣,哪年立村,誰人所建,其來多久,沒有誰能為我講清楚。
我徘徊在短短的村街上,望天空飛落的流星,童年的記憶就這樣復活起來,似乎滿街都是喧囂,滿街都是熱鬧,滿街都是生氣。
四
前兩年,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柏泉不僅僅是泉】,文中對自己的家鄉做過一些記述。柏泉過去稱「百泉」,因水泉多故。明版【盂縣誌】上說:「六祖師辿」「在縣北四十裏百泉山」。可見,那時的柏泉其實就是「百泉」。柏泉是由三個自然村組成的村莊,分別是紅崖底、張家莊、田家莊,當地人也有以「三柏泉」稱呼的。清朝的時候,三個村為一個村,對外就叫「柏泉」。新中國成立後,分成了三個行政村。其實三個村同處在一道山溝裏,就叫柏泉溝。從萇池鎮向北往藏山去,只數東邊的山溝,第一道大溝應該是東掌溝,那是萇池村的地界,再往北,另一道向東的深溝,就是柏泉溝,再下去就是藏山溝了。
柏泉也有一處有名的風景,就是「碧屏山」,也稱陸師嶂或「六師嶂」。明萬歷四十八年的一通古碑【柏泉村神山禁諭碑記】上說:「縣北離城四十裏,古剎玉帝廟有六師辿」。關於陸師嶂的傳說小時候就聽長輩們講過。我爺爺告訴我,從前,那裏住著六位僧人,後來,他們走進陸師嶂的一個山洞裏,洞很深,裏面能聽到平山人簸黑棗的聲音。後來,這六位就再沒有出來,傳說是成仙了。乾隆版【重修盂縣誌】的記載是:「六師嶂,山名,傳上世道士六人屍解處。一名碧屏,高逼霄漢。邑王珻記略雲,嶂出眾山之上,崖削如屏,遊客名碧屏山,而土人仍謂之六師嶂。傳有六羽士化於山之洞。洞極邃,束燎入,或二三裏不能窮,多燎滅而反。有廟構於嶂之腰,門繇裂石入,廟後倚深巖,池水幽暗,深不可測。」看來,成仙的是道人而非和尚。
王珻先生是盂縣清初著名的人物,曾登第康熙丙戌進士,後改庶常、翰林院檢討,做過十數年的晉陽書院山長。明代邑人張拳曾有【六師洞】詩一首:參破元機控玉鬃/三茅隱映碧蘿重//松巢鶴去煙霞滿/丹照人稀蔓草封//花謝石男緣雨瘦/臼殘雲母任泉舂//仙師去後無訊息/萬古青青數點峰。盂縣著名文人武全文先生在他【仇猶山水記】中,把碧屏山、李賓山和溫泉峽列為當時盂縣山水的前三名,謂之「三甲」,藏山不在其列。現在藏山之名,早已遠遠超越了碧屏山,成了盂縣甚至陽泉市的重要名勝,而近在咫尺的碧屏山,卻仍然沒有開發,處在一片荒涼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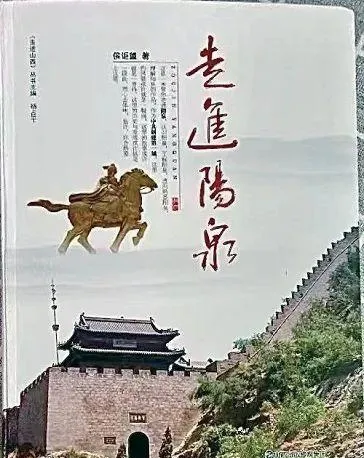
我在很小的時候,大約六七歲吧,曾經於陰歷四月十五藏山趕廟會的時候,路過那裏,與同行的叔叔、哥哥們做過一次遊覽。甚至找到了道士羽化的山洞,點著打火機進去了一節。倒也沒有見到什麽奇特的景致,只是洞裏淤積了許多泥土,使本來不是很高大寬泛的石洞逾亦憋窄。
準確說吧,我的真正的出生之地在田家莊。田家莊沒有一個姓田的人家,我後來考證,應該是城裏田家的莊戶地。田家者,最有可能的是盂縣北莊村的田嵩年。田嵩年,字季高,盂縣北關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歷任庶常、翰林院編修。他家有莊子地在我們村,也就不是什麽稀奇事。但對盂縣民俗頗有研究的我的弟弟,對此卻另有一番說詞:「田家莊不可能是田嵩年的莊子。侯家最初到田家莊種戶地的侯運泰老祖是清康熙中人,【重建藏山捲亭記】碑立於康熙五十一年,侯運泰是萇池村糾首,家譜上運泰和碑刻上運太應為同一人。據傳劉家比侯家早到的田家莊,而史家應該還在劉家之前,也就是說他們大概清朝以前就到田家莊居住了。張家莊的俊娃老人50年前就說過,侯家搬過來差不多300年了。所以田家莊不可能是清嘉慶時的莊子。」也許,他是對的吧,我也不想去管它了。
但這樣的歷史積澱,這樣的文化傳承,這樣的古跡名勝,對於開始做夢的山裏娃,那一定是一種慰藉、一種熏陶、一種滋養。
五
也許,我的文學夢是從1972年那個陽光明媚的上午開始的。那時我還是二年級的小學生。大約是5月份吧,天氣還不算太熱。我站在學校院子的正中偏南,望著陽光從東邊教室的屋頂,射向西邊老師辦公室兼宿舍的窗台,齊齊地在窗台上劃出一條線。
在那個時間段,我居然閃出一個奇怪的念頭,我想留住這一刻的時間。希望在若幹年之後,我還能記起那時的狀態:學校、教室、老師、同學,以及教室外墻上的標語和南邊教室門口剛剛盛開的粉色芍藥花。也奇怪,幾十年過去了,那一刻的情景居然被我記住了,而且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顯得模糊起來。
那是故鄉的一個特定場景。我想之所以難以忘記它,大概是因為故鄉是我們每個人記憶深處最清晰的畫面和旋律,是我們開始做夢的地方,是自己人生的出發地,更是我們每個人的根脈所系。
我的小學是在一所神房院裏。神房不同於廟宇、寺院,是供神聖臨時歇腳的地方。準確說,是藏山大王歇腳的地方。藏山大王就是趙氏孤兒趙武。我們當地有藏山大王崇拜。遇到旱災年景,鄰近村莊都要赴藏山廟祈雨。即便是好的年成,也是他老人家保佑的結果,每年要確定一個村莊做會,就是請他老人家到村裏巡遊,人民透過表演社火把戲,討他老人家歡心。
學校為復式教育,算術、語文、政治之外,諸如體育、音樂、繪畫都有課程安排。遇到節日,還要排練文藝節目,比如秧歌劇什麽的。我自己曾參演過一出秧歌劇【老兩口爭扁擔】。我在劇中飾演老漢。記得有兩句唱詞:星星忽閃天未明,老漢我早早起了身……說的是老兩口為了抗旱保苗,早早起床,爭扁擔挑水澆地。老漢以為自己起得早,結果老伴比他還早,兩人爭執不下,由隊長來評理矛盾才得以解決。這個劇帶有當時的時代特征,但每次演出,老百姓都興致很高,得到誇獎的滋味總是很甜美的。
那時我不但演劇,而且說快板,說評說(我們當地的一種曲藝形式)。文藝的實踐,使自己萌生了寫劇本,編快板、評說段子的念頭。這或許就是文學夢開始的時候。
這麽說吧,從小學開始,到初中、高中,再到中專,一路走來,自己都是文藝隊伍中的一員。骨幹說不上,但也偶有上佳表現。同時,在各個學習階段,在老師安排下,辦板報,寫通訊稿都無形鍛煉了自己。
直到後來背著老師和家人偷偷開始寫小說。那時投稿不用貼郵票,信封剪個角,讓郵遞員寄出去,投稿就完成了。每次投稿之後,接下來就是等待。在焦急等待中,做著各種美妙的猜想和期盼。當然,結果可想而知。一開始只有退稿和鉛印的退稿條,後來,偶爾也能接到一份編輯鋼筆書寫的退稿信。那時晚上做夢大都與投稿有關,不是夢到稿子丟了,就是夢到作品發表了。醒來,望著黑黢黢的窗戶,心中空空蕩蕩。枕邊卻有夢中落下的淚水。
如今已過花甲,這文學之夢依然沒有醒來。每天不寫點東西,就感到空落落的,似乎生活缺少了點什麽。後來,我想,這也是一種愛好。就和有的人喜歡唱歌跳舞,有的人喜歡旅遊攝影,也沒有什麽不好。既然是愛好,就讓他愛下去得了。總結這幾十年,我也有這麽個感悟:也就是人一定要有一種乃至幾種好的愛好,這樣生活才充實,才有意義;而愛好,又是一個人成功的原動力,只有打心底裏喜歡,才有繼續堅持下去的勇氣和韌勁。
當每天新的陽光灑滿窗台的時候,我依然會記起我的故鄉,以及與故鄉有關的山山水水、事事物物、男男女女,想起自己曾經開始做夢的地方,想起自己曾經做過的夢。
作家史鐵生說過:皈依在路上。我們躁動的心,只有在故鄉的土地上才能找到安寧,否則永遠在路上。其實,把心安放在故鄉的土地,何嘗不是另一種皈依,但其實,也還在路上——因為,故鄉也在前行。所以,故鄉便成為一種記憶,一種憧憬,一種奢望,一種心結。
走不出故鄉,一如走不出自己的心結,無論我們走千裏萬裏,無論我們走十年八年,故鄉永遠駐足在我們心裏。
走不出故鄉,或許是走不出自己心的皈依。
作者:侯詎望
名家簡介
侯詎望,1963年7月生,山西省盂縣人,現任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任山西陽泉市文聯、作協主席。出版有雜文隨筆集【學會忍耐】,中短篇小說集【致命誘惑】,散文集【路上】【我是誰】【走進陽泉】【故鄉的根脈】【心中的雪】等,電影劇本【伏擊】(合作)、【中共第一城】等。作品曾獲中國小說學會「中國當代小說」獎,【小說選刊】首屆全國小說筆會征文短篇小說一等獎、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趙樹理文學獎、山西省文藝評論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