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上海书城经过改造复归大众视野,重新开业当日众多老书迷涌入福州路上的「精神家园」,朋友圈里还见到几位媒体朋友拿着长枪短炮竞相直播,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书店空间沿革的讨论。恰巧,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则读者来函,这位读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县城中心开设了一家大型书店,无奈这是一家「无法看书」的书店,环境豪华,图书周边琳琅满目,可偏偏书籍皆被塑封,店员说拆开了就得买下,不由让人怅恨久之。似乎已经无需再议书及书店的尴尬现状了,许多人回望曾经的的阅读热潮,向我们不断讲述当年的荣光,但昨日的狂热已是手里的月光。

在当今这个时代,书、书店还能给人感动,予人慰藉吗?当拿起【送书人】这本小说的时候,内心是充满忐忑的。
作者卡斯滕·海恩在扉页的献词里如是写道:「献给所有的书商。即使在危机蔓延时,他们依然为我们提供着独特的食粮。」小说刻画了一个受雇于书店,不断为城镇居民推介书籍的「送书人」——卡尔·柯霍夫。在书店实习生眼中,这位格格不入的老年员工称得上时代的活化石,这家伙不看新闻,不听广播,也不读报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秩序的捍卫者。不去送书时,就躲在那个堆满了书的两平米里,那是他自我保护的精神空间。唯一可以让他兴奋的或许就是向不同的人推荐不同的书——「这本书,自从上市就一直在等您。」再挑剔的读者也被他说服,其他员工认为的「硬茬」在卡尔面前都十分服帖,他的渊博学识以及独到眼光让众人敬佩。
「反正我不看书,除非是被逼着看——也就是在学校里。要是书被改编成电影,那我宁可看看电影。」这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故事,书店小年轻的话很轻易地就拆穿了欧洲「全民阅读」的幻景。而目下的现实恐怕是连电影都激发不出大众的兴趣了,一部电影的叙事被人工剪辑、AI配音,最终变成3分钟的短视频,跳过那些冗长、无趣的蒙太奇、空镜头,所有的爆点、冲突轰炸着受众的神经,这样一比较,读书显然是太慢了也太乏味了。这不由让人想起英国地铁乘客争相读书的段子,不是因为他们爱看书,而是因为地铁里没有网络信号。这种调侃是一种科技进步下对于外国月亮的祛魅,更是一种对现代图景的白描。我们有多久没有读过书了?我们又有多久不曾在书店里打发时间了?如果卡尔失去了送书人的身份,那么他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塌缩到一个独居老人的逼仄情状,书是他连接他人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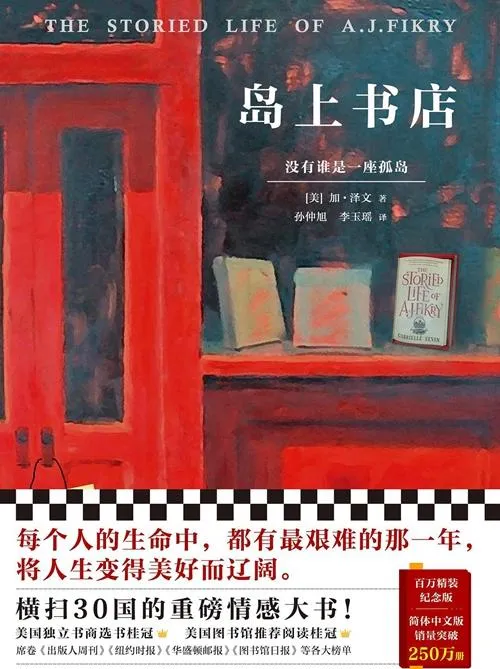
小说文本的通俗流畅,让我想起了另外两本大名鼎鼎的小说【岛上书店】和【查令十字街84号】,它们拥有近似的叙事内核,呈现在读者面前是的书、书店以及与书有关的人,让人沉浸其中不住回想的是人类与书过去的温存。【岛上书店】在亚马逊畅销榜霸榜的时代,网购尚未成风,一本【读者】或者【故事会】可以全班传阅,麦考林商城小画册可以翻来覆去地看,彼时的贫瘠也是彼时的充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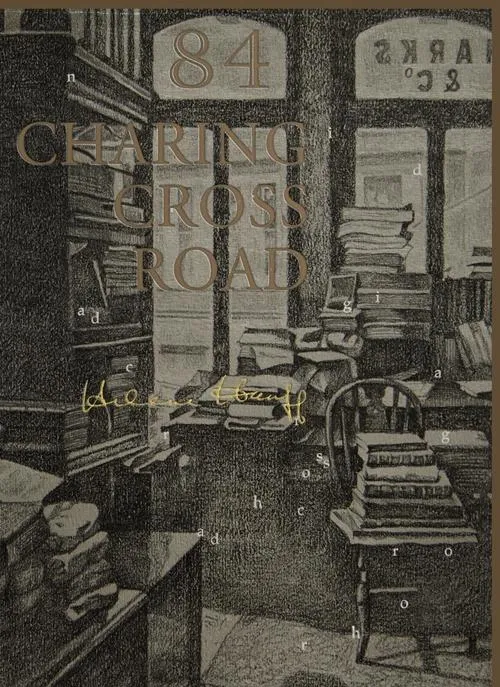
现在的科技主打一个「万物互联」,手机可以连接所有设备,房子、车子、票子都可以用一个终端解决问题,各大厂商比拼谁联得多,谁联得方便。问题是,和物的连接越来方便了,大家都在畅想带着VR眼镜利用虚拟现实走向未来,人与人的连接反而越来越难了。

「辞典,是横渡词汇海洋的船,人们乘坐辞典这艘船,搜集漂浮在漆黑海面上的点点星光。只为了能用最恰当的措辞,准确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传达给他人。如果没有辞典,我们只能伫立在这片浩瀚的大海前,驻足不前。」小说【编舟记】里,松本前辈的这段话犹如理想主义的星火,很文艺地向读者表述了编纂辞典的意义。但是仅有理想和认真的态度,依靠个人也是无法完成这种费时费力的伟业的。
与卡尔一样,同样是亲近书的主人公,马缔光也亦是一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听闻马缔要被调动到辞典部,原部门所有的人都不在乎,在出版社营业部这家伙没有丝毫的存在感,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员工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在豆瓣上,常看出版社友人们互相调笑,辛辛苦苦做了书,下班进了书店,买了同行卖不出去的「大作」,完成了一个出版社编辑「编书-购书」的完美闭环。爱书人本身就是如卡尔、马缔这般的「怪人」,为了一个善本可以忍饥挨饿,宁可住得局促也不愿意丢弃书籍。
同名电影【编舟记】中的马缔通过松田龙平的演绎更显内向与窘迫,他甚至无法与其他人产生交流的可能,面对心爱的姑娘也坚持用文言文写作情书表达爱意。他希图完成编纂【大渡海】这本辞典,而拯救他的也是辞典编纂本身。人试图用词语来定义世界,感受就是命名,然而再丰富的词藻也无法完满地诠释人,在【编舟记】这里,辞典是渡过浩瀚无穷的大海的扁舟,只要有渡(渡人或渡己)的需求,就必定存在想要达到的彼岸——他人的心灵,完成与他人的连接,证明自我的存在。
「词与词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保持着绝妙的平衡,形成一座摇摇欲坠的塔。」在制作一张张词例收集卡的过程中,马缔光也从一个个词汇中寻找到了一些涉及心灵的秘密,逐渐地开始与人发生联系,对于辞典编纂工作的真情投入,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同仁,耗时十多年终于完成了【大渡海】。小说作者三浦紫苑在文本中设置了大量的「彩蛋」,如果是一个爱书人的话,一定会对作者的巧思会心一笑,在这种精心设置的伏笔下涌动的是作者对于书的热爱。我不觉得【编舟记】的故事是一种抵抗叙事,它并没有大肆渲染新技术的威胁,在出版圈里压力是始终存在的,选题、定价、库存每一个概念都会给编辑造成切实的压力,但是【大渡海】这一项目的设置是为了顺应这个时代,编纂过程中的坎坷、不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主编松本对于马缔光也的期待那般,词语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人与人的连接或许可以由电子信号取代,但是如果有新的词句能够表达人的内心,我们就还有另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

如果这种可能是书的话,那么怀旧不啻为一种展望。在一些特定的历史场景下,书所蕴藏的不仅是一种抒情。小说【偷书贼】所讲述的故事较之于【送书人】更为极端,但也更为典型。笼罩在战争阴云下的人们通过偷书、念书的行为,维系着对于生活的希望。这类故事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薄伽丘的【十日谈】,人物设置与剧情安排都似曾相识,但是大多数读者还是会被同一套配方俘获。因为书在这里的象征仍旧会触碰到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柔软维度,在被科技包裹地越发严实的同时,心灵的衰减是不可逆的。不久前,Open AI公司发生的「内讧」,源自于一些AI专家对于新项目可能威胁人类的警惕,在名为商业利润和人类道德的天平两端,一些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或许也部分回答了,为什么【送书人】【偷书贼】这些有关于书籍的小说能够持续打动人心。
「这座城市是圆形的,穿行其中的人未必注意得到,但每只斑尾林鸽和麻雀肯定都一清二楚。」【送书人】里的卡尔·柯霍夫坚持为每一位「需要书」的人推荐适合他们的书籍,在一次次的送书、答疑的过程中,卡尔与读者之间产生着微妙的化学反应,72岁的他显然不再年轻,但他仍会止不住地揣测对方的兴趣、生活以及周遭的一切。「我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你可以设想,一根指针可能是可悲的,因为它始终沿着相同的轨迹转圈,周而复始。但相反的情况是,它很享受路径与目标的确定性、不会走错路的安全感,一直确保着有效和精准。」实在感与确定性,它既决定了卡尔工作的孤独,也给了他这个时代稀缺的安定与自在。这或许就是书的明天,以一种特有的稳定感留存在这个时代的角落里,等待着它的读者,等待着我们。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