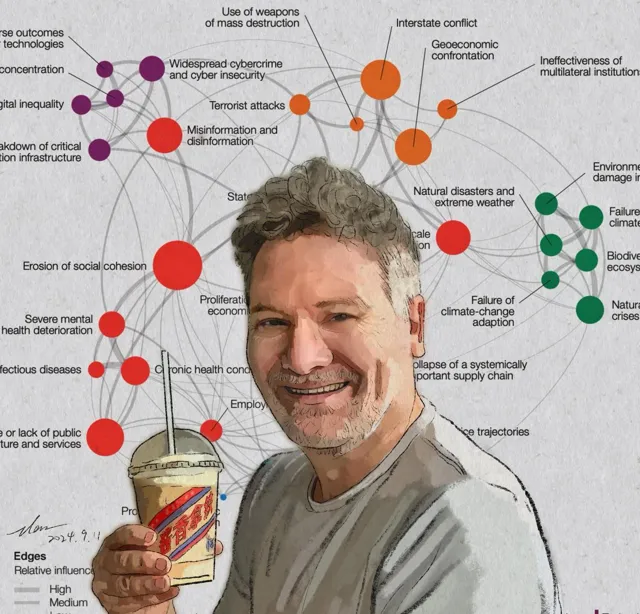
亞當·圖茲(章靜繪)
亞當·圖茲(Adam Tooze)是典型的政學雙棲動物。他長期致力於經濟史研究,尤以危機相關議題為重心。他於2001年出版的處女作【統計與德意誌國家,1900-1945:現代經濟知識的形成】(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考察了宏觀經濟知識的誕生,這些知識也推動了他在劍橋任教期間完成的第二本書【淪陷的代價:納粹經濟的形成與崩潰】(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2006)的敘事。2009年,他轉會至耶魯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其間以一戰時期的全球金融體系為主題,撰寫【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 2014),描述了美國經濟與軍事力量重塑世界的過程。
目前,圖茲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兼歐洲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他出版了【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21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時,他又推出了【停擺:新冠疫情如何撼動世界經濟】(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憑借對危機的研究,圖茲已成為全球決策圈的常客,不僅活躍於達沃斯和對沖基金峰會等場合,還參與拜登內閣的經濟顧問會議。
今年夏天,圖茲來大連參加第十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並在北京、上海講學。【上海書評】在上海專訪了圖茲,請他談談在這個多重危機時代如何治政治經濟之學。訪談分兩部份刊出,上篇主要討論理論與方法,涉及圖茲的前三本著作;下篇則聚焦現實議題,涵蓋他晚近的兩本著作和最新的氣候問題研究。
我聽了您在上海的兩場講座。按我理解,您的華師大講座雖然主要分析美國史,重點卻是批評所謂霸權接替(hegemonic succession)論。而您在復旦講座中對當下多重危機(polycrisis)情勢的勾勒,以及您參照的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所謂「通往未知世界的單程旅行」(a one-way trip into the unknown),則讓我聯想到本雅明和早期阿多諾的歷史哲學。這兩場講座的內核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可以說,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反對黑格爾式的辯證思維?
亞當·圖茲:
確實如你所說。這越來越成為我的一個基本主題。但如果我們拒絕任何順滑接替或辯證解決的觀念,那接下來要問的問題便是:你還剩下什麽結論?在【停擺】和【崩盤】這兩本書裏,我提出了一個持續的自由主義危機管理的前景。如果說多重危機的狀況是權力在當下所面臨的挑戰,那我的應對之道不是訴諸某種激烈的解決方案,而是著眼於長期的管理。
我想繼續追問的是:按您的思路,歷史分期在今天是否還是可能的?您曾說,【滔天洪水】講述的是美國主導的金融時代的開端,【崩盤】則是關於其終結,如今我們正進入一個新時代。那是否可以稱之為「多重危機時代」?對於今天的時代,該如何定義或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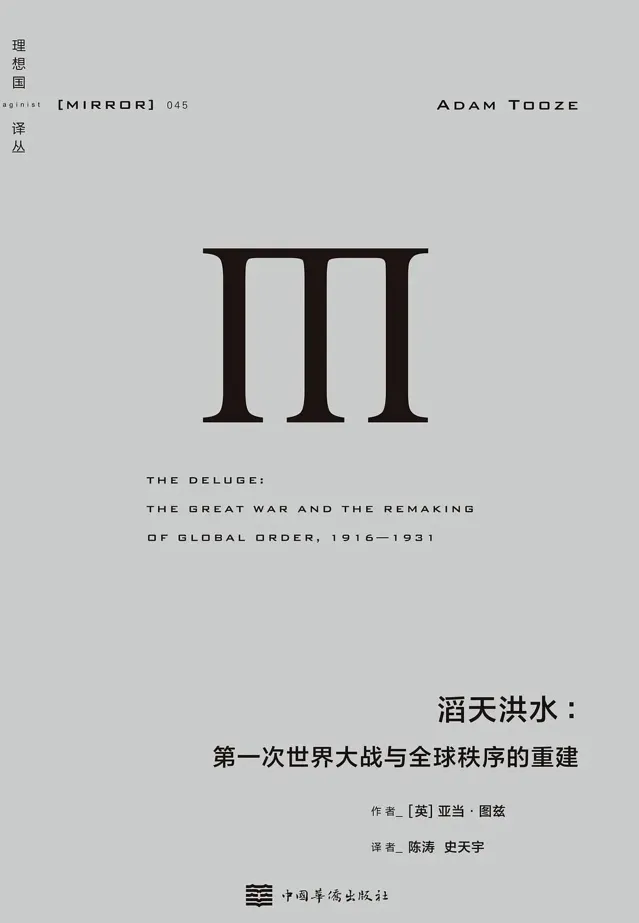
【滔天洪流: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英]亞當·圖茲著,陳濤、史天宇譯,理想國|中國華僑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744頁,1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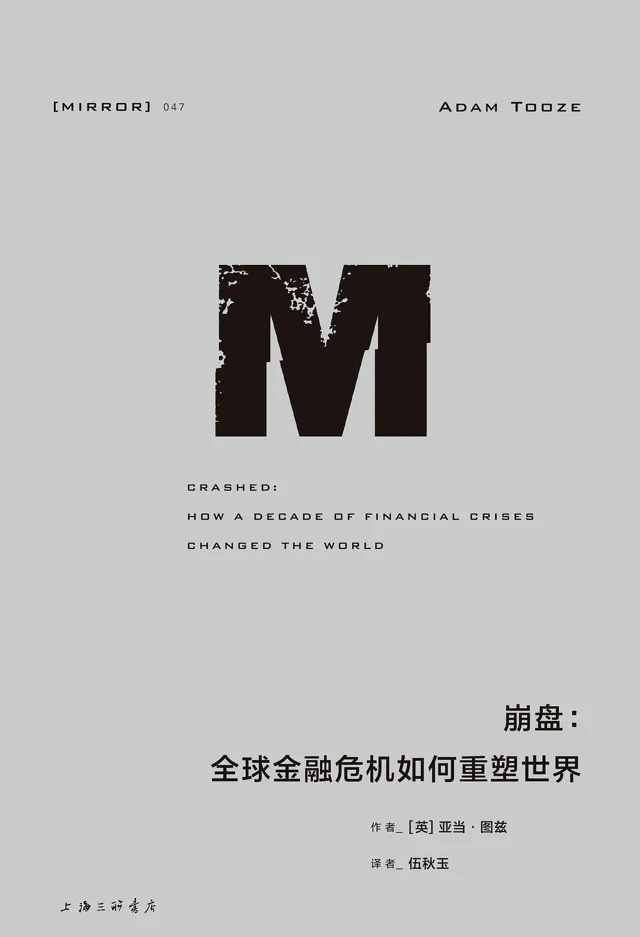
【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英]亞當·圖茲著,伍秋玉譯,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6月出版,788頁,148.00元
亞當·圖茲:
我認為「多重危機」這個概念,盡管它的輪廓有些模糊(顯然作為概念它有些隨意),應該能夠回應你的問題。因為它捕捉到了一個我們熟悉的權力模式——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權力模式的瓦解。但接下來,我並不特別喜歡那種典型的葛蘭西式的論斷,聲稱我們正處於一個過渡期(interregnum),舊的正在死去,新的尚不能誕生。隨著思考的深入,我越來越覺得這種「霸權-過渡期-霸權」的描述並不適合用來理解我們當前的時刻。這正是艾爾都塞所批判的葛蘭西的歷史主義:把歷史視為一個有機的總體,一個子宮,等待最終生出一個新時代。這種看法,包括阿裏吉(Giovanni Arrighi)的霸權序列說,盡管宣告了當前這個過渡期的無序,卻也安撫了人心:它暗示危機是可理解的,種種混亂可以化約為暫時的、周期性的、可預測的現象,因為有一個潛在機制在超歷史地(transhistorically)運作。我認為,所有這些都不能真正解釋我們現在的處境。
如果說還會出現一個新的普遍秩序,人們或授權以設想,它是圍繞氣候危機及其應對政策來組織的。諷刺的是,這似乎是我們實作新綜合(synthesis)的最大希望所在——至少這是我目前如此關註氣候問題的原因。某種意義上,它預示著恢復一個總體性的目標:在某個期限內,比如2050或2060年前,實作去碳化,讓氣候達到穩態。這是向舊時的高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復歸,但規模擴至全球。
對我來說,多重危機有助於打破技術官僚最後殘存的一絲自滿。當然,設想用氣候危機來組織技術官僚總體性有點奇怪,因為在許多方面,它指向的是失敗和災難,可能通往一個失控的未來。然而,正如2015年【巴黎協定】以及凈零(net-zero)政治的口號所想象的那樣,氣候危機確實充當了某種技術官僚的總體性的推手(technocratic totalizer),一切都可以圍繞它來安排。我曾在德國經濟和氣候保護部見過一份矩陣式的計劃圖,展示了政府為實作2030目標而制定的政策路線圖,涵蓋各個部門的具體行動。然而「多重危機」這個模糊的、面目不清的概念卻與之背道而馳。它提醒我們,我們的計劃可能會失敗,被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復雜動態力量所吞沒。
兩年前,您寫過一篇關於米爾斯海默的文章(John Mearsheimer and the Dark Origins of Realism),您對他的態度似乎很曖昧。多重危機論與他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有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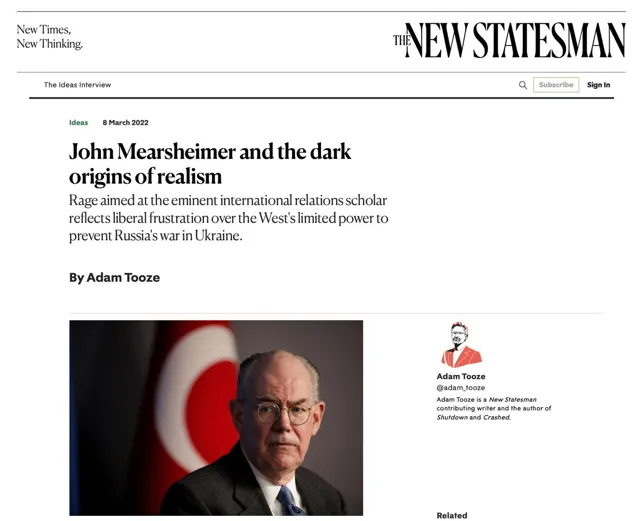
圖茲所寫【約翰·米爾斯海默與現實主義的黑暗起源】
亞當·圖茲:
我認為,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是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些全面變革行程中內生(endogenous)的一部份,它是多重危機的關鍵驅動因素。因此,我並不反對米爾斯海默關於與俄羅斯沖突不應令人感到意外的觀點。我覺得西方自由派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主張,表現出一種虛偽的震驚。普亭早在2007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就明確劃出了他的紅線。西方可能不贊成他的立場,但如果他的警告被無視,那隨之而來的後果也不應令人意外。
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緊張關系。這與普亭個人的意識形態無關,而是由重大的地緣政治對立所決定。這種對立因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而加劇,而這些收入本身又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產物。莫斯科試圖修正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在歐洲大陸上形成的巨大失衡,這一點不足為奇。簡言之,我會在米爾斯海默的地緣政治分析中補充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但我與他的分歧在於,他簡單地認為,診斷出緊張局勢的結構性原因,就足以解釋投身戰爭的決定。這在邏輯上並不成立。從智識上講,我認為這是一個偷換概念的做法。爆發沖突,付出混亂和大規模傷亡的代價,還需要其他解釋。在最深層次上,米爾斯海默未能嚴肅區分戰爭本身與地緣政治操作,因此他自命為終極現實主義者的說法也顯得站不住腳。對於一個聲稱對權力持現實(realistic)態度的思想體系來說,這是一個深刻的失敗。
我自己也教軍事史,會花很多時間來思考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沖突,尤其是二戰。如果你認為緊張的國際局勢本身足以解釋發動戰爭的決定,那說明你還沒想清楚戰爭是什麽。雖然這麽說對米爾斯海默可能有些苛刻,如果你看他的各種演講視訊,你可能會欣賞他充滿活力的表達風格、他的常識感,但你也會註意到他描述全球舞台上主角的方式過於簡化和片面。各方人物都是他口中的「硬漢」(tough hombres),這是他最喜歡用的美國俚語,原本是形容墨西哥土匪的。基本上,他將暴行歸結為強硬的人在做殘忍的事情,思考便止步於此。但這是在逃避解釋的責任,而這正是我對他不滿的地方。
米爾斯海默確實敢於直言不諱,常常以非常不討喜的觀點挑戰美國自由主義建制派。我欽佩他堅持要求我們考慮俄羅斯的立場,我同意俄羅斯的行事自有其邏輯,並非全然非理性的。我也贊賞他承認烏克蘭是這一政策失控中的最終受害者。我不認為烏克蘭的利益在面對俄羅斯反對、與西方結盟的過程中得到了最好的維護,他們為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在關鍵時刻,米爾斯海默的論證鏈條是如此薄弱。
您在寫作中經常提到拉圖爾(Bruno Latour)和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能談談他們對您的影響嗎?您在研究中,特別是探討多重危機的概念時,是如何協調他們二者的差異和局限的?拉圖爾對宏觀層面的建構持懷疑態度,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方法,來平衡這種懷疑主義與對現代性及其危機進行更廣泛解釋的需求?——如果這種需求確實存在的話。
亞當·圖茲:
誠然,我是時代的產物。我是一個深受「第二現代性」(second modernity)或「反思性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以及混雜性(hybridity)思想影響的X世代思想者。1986年,烏爾裏希·貝克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問世,正值車諾比事件發生。1987年,拉圖爾的【科學在行動】(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出版,1991年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出版。概括來說,貝克描述了一個反思性的第二現代性,但用的卻是第一現代性社會學的智識工具,而拉圖爾則將這一事業進一步激前進演化,質疑社會科學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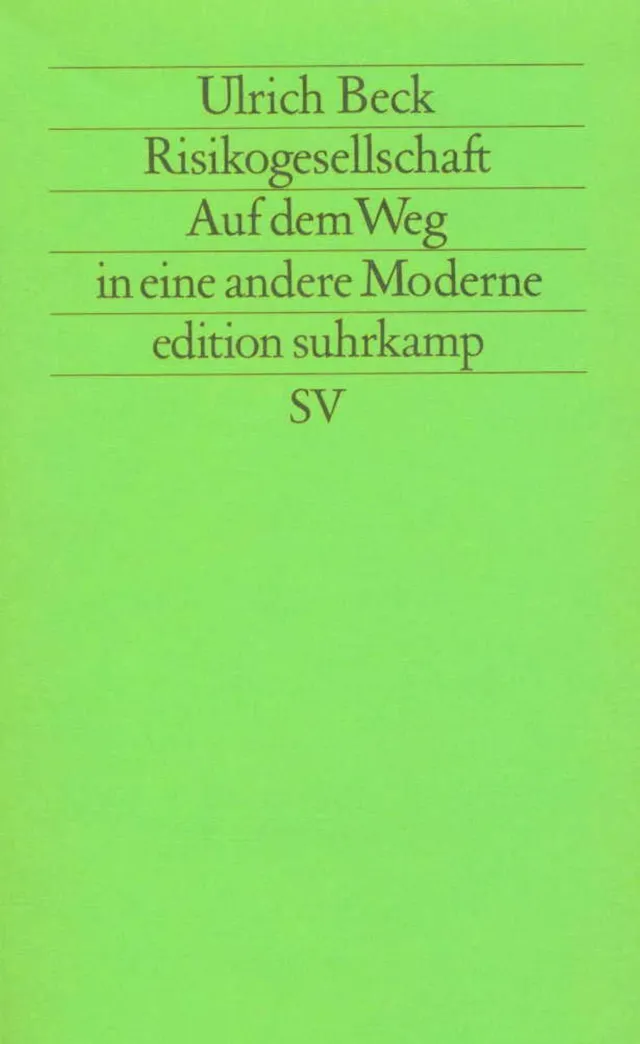
烏爾裏希·貝克著【風險社會】
我非常欣賞貝克關於世界的宏大視野,他認為當今世界由二階、三階的風險所塑造,而這些風險是由我們在一階效應上的成功所致。然而,我認為貝克的問題在於,他在【風險社會】中對社會學及其如何運作的理解有點粗糙,他呈現了某種相對靜態的視角,把社會視為既定存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的社會系統有一套自己執行的邏輯。這是一種簡單的歷史階段論:我們告別第一現代性,隨後進入第二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由此我轉向了拉圖爾的概念。拉圖爾的裝配(assemblage)理論,以及他對社會、經濟的理解,認為它們是透過社會技術系統、科技結構和裝置、計算中心(centre of calculation)交互作用構建起來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加動態和靈活的視角。我關於經濟統計史的處女作某種程度上便是試圖用拉圖爾的方式來描述現代經濟學,尤其是宏觀經濟學的出現。

拉圖爾著【我們從未現代過】
不過,拉圖爾也有自身的局限。拉氏社會科學的建構方法對我很有啟發,但他沒有提供一個全面的關於現代性的論述,沒有描述宏觀層面的社會行程。比如在【我們從未現代過】,拉圖爾暗示,現代制度下不斷增多的混雜體(hybrids)推動了社會發展的加速,但他並沒有描述這種加速本身,更不用說對其進行量化了。他關於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開端見解深刻,但由於他對「大詞」的懷疑態度,這些見解並沒有轉化為對長期歷史發展的描繪。然而,【我們從未現代過】的敘事,卻暗示存在一個關於這個「從未現代」的系統如何發展、加速、放大、擴張自身的故事。這一隱而未明的歷史模型,在拉圖爾的政治理論中表現得更加清晰。他最終的政治訴求是放慢現代性的步伐,讓(自然與社會的)混雜體變得可見,從而減緩我們改變世界的速度。只不過拉圖爾本人的理論並沒有深描前述的歷史動態。
在我思考多重危機的概念時,這些問題再次浮現在我腦海。我追求的一個目標是,將不斷加劇的危機和不確定性視為內生的結果。然而,當我們把內生性(endogenity)與外生性(exogenity)相對,就意味著必須在內外之間作出明確的區分。而此時,如果采用拉圖爾的視角,我們便不得不問:當我們說某個行程是內生的,某個行程是外生的,我們所依賴的那個系統、那個整體(holism)究竟是什麽?用拉圖爾式的語言來說,假設存在一個宏觀領域,其中有各種內生驅動的行程,這本身就是一種構建。拉圖爾拒絕這樣的宏觀-微觀框架,並敦促我們對此保持警覺。
目前我唯一能給出的答案,是訴諸一種你可稱之為「碎片化的」(fragmentary)整體性或「未封閉的」「部份的」整體性,用來定位(situation)各種危機癥候,繼而宣布我們面臨一個多重危機的局面。所以我可以討論人畜共患疾病的突變、二氧化碳的累積、地緣政治軍備競賽的升級。但我並沒有,也可以說我在某種程度上拒絕,甚至如一些人所言是在回避,透過一個單一且嚴密的邏輯,提供對現代化、增長或其背後歷史行程的宏觀敘述。坦白說,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想通了」,你就沒有真正面對多重危機。我想,這是拉圖爾傳統在我身上留下的張力。
您怎麽看定量的方法?在您的推特貼文、時事簡報(newsletters)和著作裏,各種表格、曲線圖屢見不鮮。您的處女作【統計與德意誌國家】,可被視為某種知識考古學研究,考察了兩次世界大戰間經濟統計數據方面的創新。您認為數據和現實是什麽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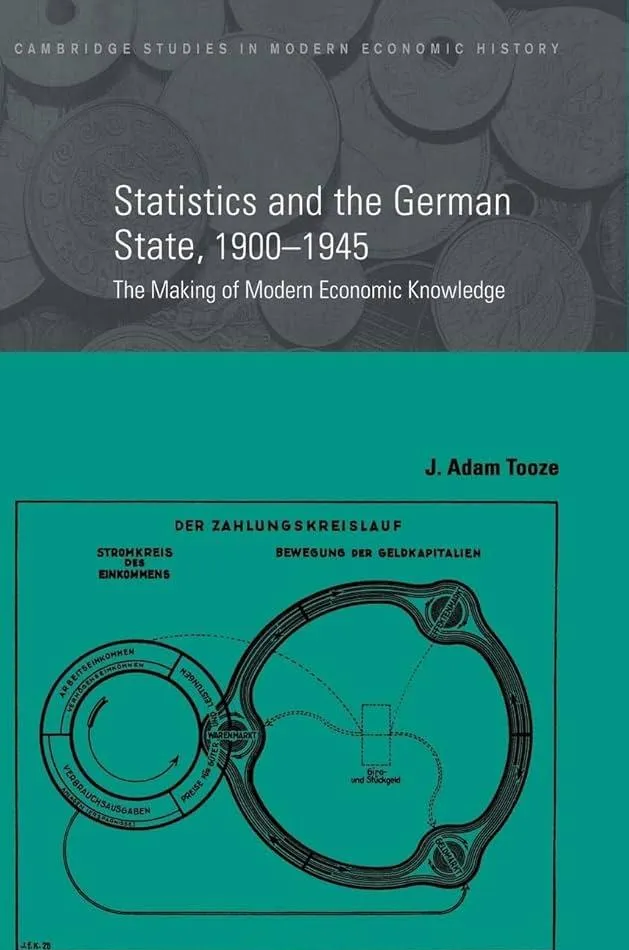
圖茲著【統計與德意誌國家】
亞當·圖茲:
這裏確實可以追溯到我的第一本書,它基於我的博士論文,聚焦於統計學史,並且如剛才所說,明確采用了拉圖爾式方法。在這本書中,我試圖解釋宏觀經濟——一個由GDP數據、通脹統計、國際收支、失業率描繪的世界——是如何被構建的。這個知識矩陣,是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時刻,由一個特定的行動者網路,及其內部特定的權力配置生產出來的?
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前兩本書截然不同。第一本書描述了宏觀經濟知識矩陣的出現。這一矩陣促使德國內閣會議的日程安排必須緊隨特定經濟數據的釋出,因為在知道GDP數據或失業率水平之前,開會毫無意義。整個決策的時間表、政治權衡的形成,都有賴於這一知識裝置,而它也是政府實際管理的工具。在【淪陷的代價】一書中,我則利用當時決策者已經掌握的這套知識體系,鋪陳了納粹政權政治經濟的大敘事。盡管第二本書廣受關註,並奠定了我的聲譽,但推動其敘事的,正是第一本書討論的國民經濟物件這一知識基礎。在【淪陷的代價】中,我一方面試圖解釋生產的物質性,它被GDP數據這一具體形式所捕捉,另一方面也分析了這些數據的呈現與解讀所帶來的政治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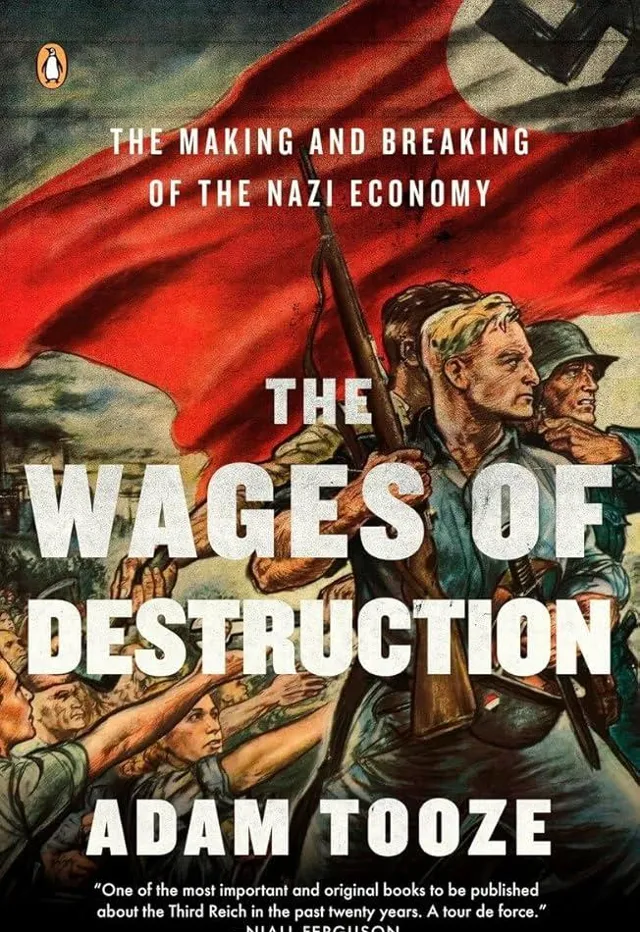
圖茲著【淪陷的代價】
例如,1938年在柏林的德國規劃機構內部舉行了一些會議,官員們感覺德國在與其他西方列強的經濟競爭中逐漸落後。他們會討論原因,然後有人會拿出一個經購買力平價調整(purchasing power parity-adjusted)後的GDP數據,顯示德國仍然遠遠落後於英法。因此,在這些權力的計算中心內部,圍繞如何再現(represent),以及表征(representations)如何捕捉物質力量的變化,存在著反復的權衡與爭論。
考察數據是如何產生的,並不是為了揭穿這些數據僅僅是被「構建」或「想象」出來的。這同樣適用於我對美國權力的分析。統計數據既非現實的映像,也不等同於它們所描述的東西。它們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以與現實的聯系為基礎,為我們捕捉現實。它們就像汽車的速度計,或老式自由車上測速的小輪。數據之所以能告訴我們經濟現實的狀況,是因為它們與現實存在機械關聯,它們內嵌於現實之中,是現實的一部份。我認為,權力與知識都不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或瞬間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力量。它們並非繼承而來,而是被不斷制造出來的。身為分析者、媒體人或其他社會角色,我們都浸淫在同一個制造(making)的過程中——事物的制造、事物表征的制造、作為表征的事物的制造。
不知道您會不會願意談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寫的那篇關於您的文章?您曾提到,您在劍橋開一門討論歷史終結的課時,受到了安德森研究方法的啟發。然而,他2019年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發了一篇長達四十七頁的文章,評論【淪陷的代價】【滔天洪水】【崩盤】(他視之為三部曲),並提出了若幹批評,我認為要點有三:第一,在他看來,您對美國霸權的理解存在時代錯誤,尤其體現在您有關納粹對美態度的描述。第二,他批評了他所謂您的「情境性和策略性(situational and tactical)方法」,認為這種方法「讓讀者被事件的洪流裹挾」,卻「放棄了為所討論物件的起源提供結構性(structural)解釋」。第三,他將這種方法與您的自由主義立場聯系起來,暗示您之所以不願做結構性批判,源於您對現存秩序的接受。您曾說打算寫文章回應安德森,但最終沒有動筆。因此我仍然好奇,您現在會如何回應他?

佩裏·安德森評論圖茲的長文
亞當·圖茲:
他對我作品的評論中,最讓我感到困惑,但最終卻是最具建設性(generative)的部份,莫過於他開篇提到的一點:他將我的左翼自由主義與他所謂的情境分析聯系在一起。他用這個說法來暗示,因為自由主義者與現狀串通一氣,所以他們的分析總停留在表面,無法觸及深層的結構性條件。他想表達的是,如果自由主義思想能夠關註到這些結構性條件,它就會意識到激進變革的必要性,反之亦然。投身激進變革的事業,將會為更深入地理解歷史結構和行程開辟道路。對於這種左翼自負,我們並不陌生。
與此形成對照,我的方法——因為我是自由主義者,所以在他看來我的方法只能是情境化的或基於特定場合的(occasional)——只會抓住特殊的時刻。他聲稱我的書都是「置身事中」(in medias res, into the midst of things,直譯為「在事件的中心」,作為文學敘事技巧,可作「直入本題」)的寫法。在他看來,我是一個在結構方面有問題的左翼自由主義者,並將此視為我思想上的缺陷——一個空白、一個盲點。我的回應是,我確實在智識上對結構有疑問,但這不是我的弱點或簡單的失誤。正如我們之前關於多重危機、拉圖爾、貝克的討論所表明的,我有一個必然不完整,但依然包容廣泛的歷史解釋,來說明為什麽在當下這個時刻,結構於我們並非清晰可見。它必然要在事中形成。我想問安德森的是:怎麽會有一個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人,認為自己並非置身事中地思考與行動?唯物主義者如何想象自己不處於事件的洪流中?我們被拋入歷史,居於歷史之中——這不是一種選擇,也不是什麽方法論立場,而是我們的命運;這是一個存在的條件。
坦率地說,我認為他的立場是一種退化的西方學院馬克思主義的體現,想象自己站在某座高塔,俯瞰世界,自以為理解歷史的深層結構。這或多或少是不置身事中的,而是以一種做作的隱居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我更傾向於摒棄這種自負,去擁有、擁抱、面對、介入每個人的處境:即在系統中,在世界中。我們是這個世界的內生部份。就此而言,問題也就變成了,在特定時刻,哪些結構是與我們的分析相關的。這又是拉圖爾的招數:你告訴我你的危機是什麽、背景是什麽,我會告訴你你是誰、你在哪——反之亦然。
與安德森不同,我不認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被一些智識經典——不論是左翼的還是其他立場的——書寫完畢,我們只需照本宣科,延其敘述於當下即可。我相信,隨著現代歷史的跌宕起伏與瞬息萬變,探索周遭世界運作的挑戰將不斷被再次激發。我不會從「我已經知道結構是什麽」這樣的前提出發,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歷史仍在以戲劇性的方式展開,不斷產生新的現實和知識形態,顛覆我們以往的認知。因此,我並非什麽左翼自由主義的投降派,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立場比安德森的更自省、更貼近現實,說實話,也更激進。
有一點很關鍵,雖然安德森能撥冗讀我的書無疑是我的榮幸,而且他把我中間三本書作為三部曲來讀也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他沒有讀過我的第一本書。所以他並不真正理解我想要做什麽。在他讀過的這三本書裏,【滔天洪水】是最艱深、最嚴苛的一本,它對列寧的分析是復雜的、非傳統的,這讓安德森感到被冒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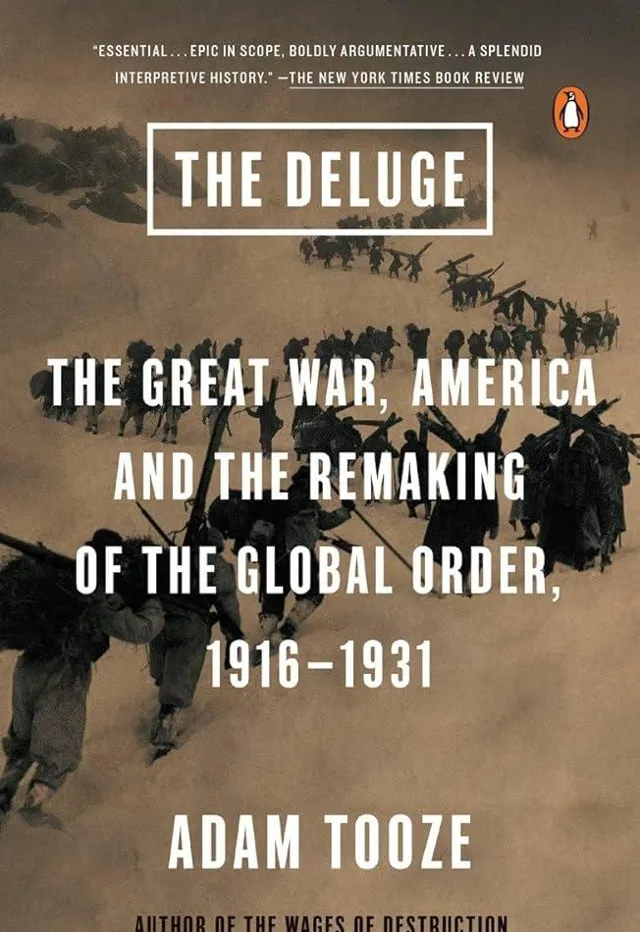
圖茲著【滔天洪流】
另一方面,安德森似乎沒有理解【滔天洪水】和【淪陷的代價】裏關於全球政治經濟的論點。他把對全球力量平衡的理解看得太輕,這種理解並非植根於所謂對美國權力的膚淺依戀。他暗示我與美國有某種浪漫聯系,卻完全忽視了我分析的根基。重要的是,我的分析結合了史帝芬·布羅德伯裏(Stephen Broadberry)的生產力分析、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經合組織(OECD)GDP數據集、大衛·埃傑頓(David Edgerton)的英國經濟研究。安德森對這些全然不顧,而這並非偶然。安德森的整個人生軌跡都圍繞著對二十世紀英國權力的特定講述而展開,而埃傑頓和我則打破了這種講述。從經濟的角度看,二十世紀德國的歷史總隱含著英國的歷史,反之亦然。安德森對此置若罔聞。不客氣地講,他對歐洲政治經濟的理解還滯留在上世紀六七十代,以及那個時期英國的衰退敘事中。這正是體現我們對「結構」的理解隨歷史變遷而發生變化的一個例子。安德森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出版的經濟史研究視而不見,而這些研究從根本上覆寫了英國衰退的舊有敘事,並糾正了納粹德國是工業強國的過時觀念,後者便是我在【淪陷的代價】裏所做的工作。
最終,我之所以沒有轉而寫一篇學術長文來回應安德森,主要原因不是我對他過時且並不深刻的歷史批判感到不耐煩,而是因為在有件事上他是對的。他的批判,勝過其他一切,促使我有意識地、堅持不懈地專註於在事中思考並開展智識和政治行動。因此,我所從事的絕不是沈寂的政治,而是對各種事務的深度介入。這包括:(1)撰寫【停擺】這樣的即時歷史,它基於2020至2021年間的數十場即時公開會議;(2)技術專家層面的行動,例如參與「反對無意義產出缺口運動」(Campaign against Nonsense Output Gaps),檢討歐洲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央行政策,最終促成某些數據計算方式的改變;(3)更宏觀層面的幹預,由【崩盤】而被紀念碑化的2008年危機敘事,成為2021年初拜登政府發起的第二輪大規模刺激計劃的靈感之一。所以,當學院左派問「你的政治呢」,我非常清楚我的政治在哪裏。我想反問的是:你們的行動在哪?這種介入伴隨著巨大的責任。拜登的經濟刺激實驗可能不會順利收場。盡管宏觀經濟數據非常亮眼,且「軟著陸」看似有望實作,但賴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可能會被證明是對的,而哈裏斯也可能敗選,因為公眾對通貨膨脹的不滿被錯誤地歸咎於拜登。但承擔這種責任,正是置身事中、參與賽局、試圖改變討論焦點的必然結果。
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左派歷史學界,人們很容易陷入無休止地重新推演經典革命時期歷史棋局的誘惑——共產國際、兩黨合作、威瑪共和國決策……凡此種種。寫【滔天洪水】的時候,我自己也沈迷於這樣的歷史遊戲。在這次重演中,我扮演了一個執拗的信奉肯恩斯主義的左翼自由派,毫不畏懼承擔暴力的責任。如今,我為自己也卷入歷史穿越遊戲感到後悔。並非因為我選擇了一個不同於安德森認可的立場,而是因為我參與了這場遊戲,從而為他的批判大開方便之門。我讓自己從當下更為緊迫的領域滑入了左派學術象牙塔中那個時間扭曲的「當下」——在那裏,現在是1924年,而1924年就是現在。我陷入了一場關於一段已不再屬於我們的歷史的無謂爭論。我逐漸感覺到,這其實是一種逃避。如果我們正處在一個革命時刻,那又另當別論。但我們顯然不是。沈溺於一個歷史的迪士尼樂園,在其中扮演列寧、托洛斯基、威爾森,幻想自己當時會是誰,又會做什麽,這對理解當前政治幾乎毫無幫助。這不過是遊戲歷史,是男孩子在電腦上玩的東西。我們該長大了。眼下世界,利害糾結,局勢太過緊迫。我們必須盡己所能,活在當下,全然置身事中。我想,困難恰恰在於如何凝神於眼前,身處局中,全情投入。因為有懷舊角色扮演等因素牽絆,這並非易事。

圖茲今年開設的微信公眾號「圖說政經Chartbook」
澎湃新聞記者 丁雄飛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