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養的幾坨貓一直沒什麽存在感,只有吃飯和睡覺時候才知道這幾坨是我爺爺家的,基本不用管,鏡頭感很好,有人用手機對著,自己就盯著鏡頭保持一個動作,直到手機拿開。
一坨是我爺爺遛彎時候撿的,另外幾坨是跟著來的,一點都不認生,敲院門如果時間趕巧,能收獲一堆狗叫聲,那狗叫的嗓子都劈叉了,喝幾口水繼續叫,還會看見幾個不同顏色的貓貓頭。
最開始來的這只明顯有地位,到點了沒飯會敲窗戶,剩下幾坨都老老實實的在墻角排排坐。
貓好像都是這樣,收養了一坨,不久之後就會長出很多坨。
有時候爺爺會用幾個雞蛋殼裝上剩飯,貓貓們就一貓一殼的吃,雖然吃得少,依然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圓起來。
養的大黃狗很盡心,有人來,只要不認識,就叫的特別歡實,並且試圖攻擊來的人,但是你真走到它旁邊,它馬上躲進自己的窩裏,從小窗戶裏伸出嘴巴繼續朝你叫,沒有事的時候經常去撩騷大黃牛,把大黃牛吃的玉米桿撅折了再送回去,偶爾拿牛角磨牙,牛脾氣好的簡直沒脾氣。
大黃狗試圖建立自己在院子裏的領導地位,被大鵝叼了耳朵,被大公雞追的躲在窩裏使勁汪汪,就是不出來,只有鴨子不太對付得了它,卻懾於大鵝的兇猛,終於還是回到了騷擾好脾氣的大黃牛的老路上。
大約是看在都姓黃的份上,黃牛對它有著無限的耐心。
後來爺爺年紀大了,照顧不了那麽多動物,大黃牛被賣那天,大黃狗追著車一直跑到了村口。
大黃還是那個「脾氣不好」的大黃,只是偶爾還會去牛圈轉兩圈。
它可能不知道大黃牛去了哪裏,以為就像往常那樣去了很遠的地方吃草,吃飽了就回來了。也可能知道大黃牛回不來了,去送送自己的老夥計。
等到爺爺搬到了城裏,大黃因為老向別人叫被送到了姑姑家,在那裏,它依然盡心盡力的看門。
再後來呀,它就死在了姑姑家。
狗生不長,卻品盡世間悲歡離合。
那些貓貓們因為搬家,也不知去了哪裏。
大概又找到了新的家庭,在某個陽光明媚的午後,蹲在一個抽旱煙的老人腳邊,聽著收音機裏咿咿呀呀的戲劇,愜意而慵懶的瞇著眼睛,看著日子不緊不慢的從眼前流過。
其實大黃到死都是只很可愛的狗,和那幾坨貓貓一樣。
只是它不太適應城裏的生活。
老房子還在,房檐寫著備戰備荒,原來那個不管顏色還是聲音都很熱鬧的院子現在什麽都沒有了。
只剩一顆核桃樹還在自由自在的生長,我四姨奶,一個一輩子神神叨叨的老太太說看見過一條大蛇在樹上曬鱗片。
說來有趣,這個神神叨叨的老太太在我小時候好像就長那個樣子,矮矮胖胖的。
我爸說,傻子不老。
我深以為然。
我長得挺著急,大約不是個傻子。
四姨奶家養了一只狼狗,每天固定點去鄰居家門口拉屎,後來被鄰居發現,一棒子打的嗷嗷叫,然後繼續偷偷去鄰居家門口拉屎。
可能鄰居家門口風水好,通便?

爺爺在姑姑家,這兩條狗都是他撿回來的。
也不知道為啥他老能撿到貓狗。
估計是自己偷偷買的,又怕家裏人說。
大黃狗不管什麽時候看見他都會把尾巴搖成電風扇。
爺爺九十啦。
每天騎電動車三四十裏去鎮上玩兒。
得了新冠,白肺,好了之後不讓他出門,坐在門口生氣。
「病都好了還不讓出門玩,還讓不讓人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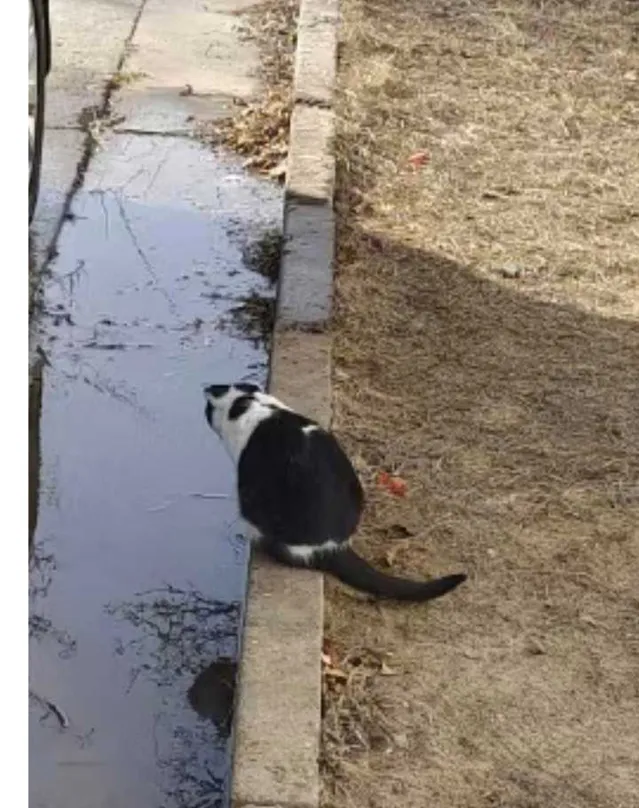
我媳婦單位的水管、水桶、水坑邊上經常長貓,一長就是好幾團。
經常去辦公室視察。
好奇心和報復心極重。
她辦公室大姐剛養的仙人球,這個芝麻糯米團子就伸爪兒去摸,被紮疼了,勃然大怒,和仙人球一場大戰,一邊被紮的嗷嗷叫一邊使勁拍仙人球。
最終仙人球只剩個球,它兩個前爪兒被辦公室妹子綁上了繃帶,那段日子走起路來貓貓祟祟的。
我原來養過一只兔子。

沒事兒就帶它出去,拔草給它吃。
後來某天,好奇心爆表的保安大爺終於忍不住了。
「小夥子,你這狗什麽品種?怎麽還吃草?」
原來喜歡爬高,後來有一次被摔的半天才緩過來,從此再也不爬了。
自己知道自己的窩在幾樓,玩夠了會自己爬樓梯上樓。
後來工作原因,沒法帶它走,就送給一個請我吃冰棍的小姑娘了。
算起來,那個性格開朗大方的小女孩也該出落成個漂亮且優秀的大姑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