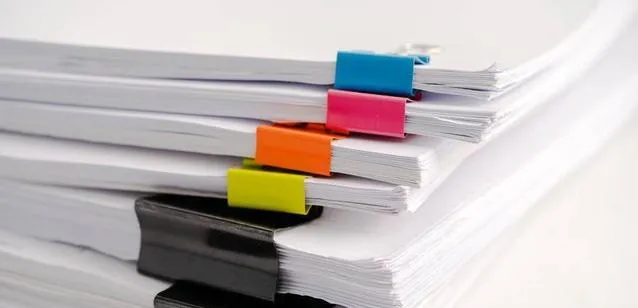
據央視網,國務院總理李強12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修正草案)】,審議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條例(草案)】和【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修訂草案)】。
會議強調,要推動各項法律法規落細落實,認真做好宣傳解讀工作,積極回應群眾和企業關切,有效釋放穩定預期、改善營商環境的積極訊號。
何為經營者集中?標準做了哪些修訂?
本次國常會透過的【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修訂草案)】(下稱「【規定】」)是為了明確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而制定的配套檔。
何為經營者集中?【反壟斷法】第25條規定,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三種情形:一是經營者合並;二是經營者透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三是經營者透過合約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
而【反壟斷法】也明確規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是壟斷行為。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
【規定】自2008年8月起實施,曾根據2018年9月18日【國務院關於修改部份行政法規的決定】進行了修訂。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介紹,【規定】在預防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22年6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表決透過了【關於修改<反壟斷法>的決定】,修改後的反壟斷法從2022年8月1日起開始施行。隨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釋出了包括【規定】在內的6份反壟斷法配套檔征求意見稿。
其中,【規定】修訂主要內容包括:
一是提高營業額標準,對全球合計營業額、中國境內合計營業額和單方中國境內營業額的要求,由現行100億元人民幣(幣種下同)、20億元和4億元分別提高到120億元、40億元和8億元,低於此標準的經營者集中原則上無需申報,提升了經營者集中審查的科學性和精準性,降低了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最佳化申報標準,對於在中國境內營業額超過1000億元的企業開展經營者集中,符合一定條件的,納入審查範圍。
三是配套【反壟斷法】修訂,對未達申報標準但符合【反壟斷法】相關情形的集中進行相應規定。
為何修訂【標準】?將為市場帶來哪些紅利?
談及此次【標準】修訂的原因,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盧義傑律師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表示,應從法律與經濟兩個層面分析原因:既為了與中國反壟斷的監管傳統一以貫之,又體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下反壟斷的新要求。
在法律層面,2022年,在學界有「經濟憲法」之稱的【反壟斷法】進行了立法14年以來的首次修改,首次立法明確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並對完善數位經濟監管、加大壟斷行為處罰力度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制度安排。根據【反壟斷法】有關條文,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由國務院規定,因此,在修法的背景下,是否需要隨之修訂新的【標準】,自然成為需要研究的議題。
在經濟層面,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市場容量大,企業數量多,市場競爭中出現了一些新現象。在此背景下,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難以與經濟發展形勢相適應。如果申報標準過低,可能造成一些本沒必要納入申報範圍的正常市場交易活動受到影響,波及市場秩序;如果申報標準過高,又無法實作防止限制競爭、排除競爭的反壟斷功能,不利於實作監管職能。因此,制定科學合理的申報標準顯得非常重要。
談及修訂對市場會帶來哪些紅利?盧義傑表示,【標準】一是更加符合市場發展的現實情況,回應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新情況、新隱患;二是便於反壟斷執法機關更準確把握規則,讓市場主體更有預期,從而增強投資信心,有利於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新標準規定,交易一方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營業額超過1000億元的企業,當另一方經營者的市值或估值符合一定條件的,也納入審查範圍。這其實是敏銳地將「扼殺式並購」或「掐尖式並購」納入監管範圍,對數位經濟領域特別是創新者是一大利好。過去一段時期,大型公司對初創企業或新興平台進行並購的現象時而引起業界關註,在數位經濟領域尤為明顯。這種並購雖然可以實作大型公司多元化、擴張性的商業布局,但有時也導致消費者某些場景下選擇平台的權利被限制,同時使被收購企業、其他競爭者在市場上不斷處於劣勢,影響技術發展和行業生態。
盧義傑特別指出,【標準】也與2022年1月國務院【「十四五」市場監管現代化規劃】是一脈相承的,有利於引導平台經濟有序競爭,加強源頭治理、過程治理,改善民生、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市場環境。
未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亦可能構成壟斷,【規定】初步補足了此處短板
【規定】修訂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細化對未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案件啟動反壟斷審查的前提條件。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劉旭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修訂前的【規定】也要求,按照規定程式收集的事實和證據表明該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依法進行調查。但是,過去15年裏該條款一直沒有細化,其中提及的「規定程式」長期沒有明確,導致該條款一直沒有被公開適用過。
劉旭舉例分析道,2015年滴滴和快的合並,2016年滴滴收購優步中國業務,相關當事人都主張沒有達到【規定】第三條規定的申報標準,但客觀上導致當時網約車市場集中度顯著增高,滴滴實作一家獨大的市場格局。但是,因為對未達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審查程式或者前提條件不明確,所以反壟斷執法機構至今也沒有能夠公開調查結果。
劉旭表示,根據【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2019)】 記載,「湖南爾康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收購河南九勢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案」是目前已知的,過去15年多裏,僅有的一個雖然未達到申報標準,但因為涉嫌嚴重限制競爭而被阻卻實施的經營者集中案件。但該案的特殊性在於參與經營者集中的兩家企業剛好同時在被反壟斷執法機構調查它們共同實施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但是,絕大多數未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案件都不會同時涉嫌違反【反壟斷法】實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或者壟斷協定。所以,這樣的案例幾乎不可復制。
因此,一方面為了避免相對狹小的相關市場領域,因為沒有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導致市場集中度過高,促成或鞏固市場支配地位,嚴重損害相關市場有效競爭;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具有顛覆性技術創新能力、或者商業模式創新能力的初創企業被既有企業透過未達到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納入囊中,嚴重妨礙有效競爭或者潛在競爭動搖其市場支配地位,就很有必要透過及時細化未達申報標準但也需要啟動反壟斷審查的機制。
劉旭分析稱,這次修訂【規定】就是為了初步補足這個短板。未來,也不排除市監總局進一步制定細則,細化相關審查程式,或者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制定相關反壟斷執法指南、合規指南,便於執法者和經營者評估哪些行業的哪些型別並購,可能會在未達到申報標準的情況,依舊有可能被禁止或者附加限制性條件批準。
劉旭預計,根據新修訂的【規定】,在數據經濟、人工智慧、智慧城市、智慧農業、環保、新能源技術、新材料、生物制藥、遠端醫療、腦科學、動植物育種等新興行業很有可能會出現不少未達到申報標準,但需要考察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經營者集中案件,防範扼殺式並購削弱初創企業創新動力和成長性。
「這樣可以避免因為一些私募基金追求短期投資收益,而過早地把具有潛力的初創企業的單一控制權或共同控制權,出售給可能扼殺創新或者限制競爭的大型企業,不利於維護中國的市場競爭環境、創新環境的永續發展,不利於相關產業鏈的完整性和國際競爭力。」劉旭稱。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