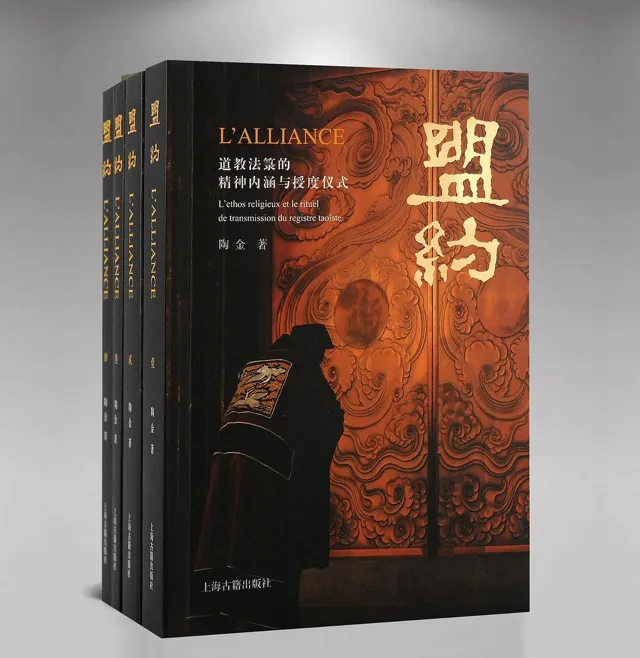
【盟約:道教法箓的精神內涵與授度儀式】,陶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1627頁,198.00元
2022年盛夏,烈陽炙烤著的聖地茅山看不到一縷縹緲雲霞,在熱氣中扭曲的絲絲灰煙讓人疑心是山火的前奏。受陶金邀請,我趕赴茅山參加江蘇省道學院建設方案的論證活動。就在此次行程中,獲悉他的【盟約:道教法箓的精神內涵與授度儀式】即將出版。基於對此書大致內容和作者基本理念的了解,此書成為2023年度我最期待的道教論著。拿到這部書的一刻,超乎意料的不僅是書的體量(一千六百多頁),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書中的內容和觀點如此復雜纏結,突出的價值與可能的疑慮撕扯著我對這部著作的整體認識。
這部著作分為四冊,側重均有不同。第一冊包括【前言】和【前夜】【盟約】兩章(本段和下一段裏的【盟約】均指第二章,而非書名)。【前言】中,作者簡要介紹此書秉持的理念,提出諸如人本位、道本位、師本位、民本位的撰述立場。從後文的情況來看,作者確實將「四本位」貫徹始終——人的「主觀能動性」、突出的崇道和「insider」立場、道要師受的關鍵價值以及對早期盟威道「平民宗教」的推重等,被反復提及,並以此為線索搭構起一套理想中的道教「神學」(如果這個詞還可以將就使用的話)和實踐模型。【前言】中的這些想法格外清晰,使我們了解到此書的創作目的並不完全滿足於呈現道教某個歷史切面的真實情況,而是希圖在部份道教文獻的基礎上,從宗教學和教義建設的角度構擬出優秀的道教義理原型(或模型),並將這樣的理想原型引入當下焦慮萬分的道教義理建設運動。【前夜】主要介紹商周兩漢時期中國傳統信仰要點;【盟約】首先解說先秦冊命等盟約儀式,緊接著展開對漢末盟威道盟約的討論,並對盟威道的重要義理主題進行分析和串聯。
盡管【前夜】和【盟約】對盟威道「前史」的介紹並沒有太多新見,行文和組織方面也顯得有些啰嗦,但卻並非可有可無的部份。作者耗費兩百多頁篇幅(占全書八分之一強)來交代問題,自然有其考慮。揣測作者的心思並不那麽難,一者當然是強調道教從文化源頭來看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份,打根上來說就屬於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不是常被儒家攻擊的「異端」;二者是試圖指出道教的「源頭」並不僅僅是玄虛的老莊思想,並嘗試將道教的思考和信仰實踐落實到更多更具體的來源上;三者則透過梳理和比較闡明早期道教的教義和組織模式部份來源於對世俗官方的模仿,因此帶有很明確的時代烙印,同時又揭示道教在面對社會危機時提出與官方不同、且富有創造性和實驗性的應對辦法——這些辦法的內核則是作者強調的盟威道的宗教精神。【盟約】中用了近三百頁篇幅介紹早期盟威道的盟約活動和基本義理,總結出盟威道「神不飲食、師不受錢」等「清約」精神。在作者看來,傳說中大道與張天師立盟、天師與川中百鬼立盟、天師和祭酒與道民立盟,構成了盟威道盟約的幾個層次,所有盟約的本質都是大道「下教」的重演,盟約的特征則可以總結為區別於朝廷血食祭祀的「清約」大道。【盟約】這部份內容中最富有創造性的地方,在於作者將盟威道的若幹核心義理要素「串聯」成一個相互聯系、彼此貫通的理論框架,教義詮釋由此獲得很強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教義的極端復雜性(有時甚至是矛盾性),使得將早期盟威道義理系統化的工作在思想史研究中並不多見,所取得的效果也不能令人滿意。由是,作者對盟威道教義的組織和編排便顯得難能可貴。其不僅形成一定的學術價值,更重要的或許是對當代道教教義建設所可能帶來的啟發。當然,這樣的教義串聯並非毫無疑問,突出缺陷和問題稍後集中分析。
【盟約】的第二冊就是第三章【法箓】。一如其名,這一接近五百頁的篇章主要就是在討論早期道教的法箓問題。法箓,對於當前道教研究者而言絕不陌生,但不少人卻仍將之與「符」混淆起來,流行一時的「符箓(派)」的說法長期誤導大眾認知。道符,一般表現為文字與象征符號結合的圖形,以之為「合約」(類似虎符)調動神靈和大道之力。法箓,一般是寫畫有大道兵將的長卷或冊子,在儀式中授予修道者。依法擁有法箓的修道者,有調動和役使箓上兵將的權力,這些原則上是由道氣所化的大道吏兵則會受命為修道者提供傳章送表、驅邪斬煞等服務。符、箓之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在這一章中,作者著重介紹盟威道(正一道)法箓系統(包括券契)的組成和演化經歷,在此基礎上闡釋圍繞受箓活動展開的教團組織模式和人神關系。早期盟威道教團中的法箓分為多個等級,受箓的過程伴隨著教民的成長、成年、婚配和擔任教內職務。因此,理論上講,法箓既在人神關系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很多溝通神靈世界的儀式活動只有在箓中吏兵的輔助下才能完成,同時,層級分明的法箓體系也構成了盟威道教團的基本組織框架。作者對法箓在神學和組織層面的雙重意義均做以詳細介紹,細致地闡明法箓在道教義理中的關鍵意義。【法箓】一章除重點介紹正一盟威箓外,也對出現較晚的靈寶和上清法箓進行了梳理和討論,其間還反對了我的一個觀點。我曾認為,東晉南朝的上清和靈寶傳統主要以「經教」為核心,「法箓」並非其必須,故僅在道教整合運動中臨時創作法箓以「充數」。我所依據的證據是目前能看到的上清和靈寶「法箓」,在形式上與標準的正一盟威箓差異明顯,不算是神兵神將的名箓。但本書作者指出,能夠役使法箓吏兵是從事道教儀式的基礎,上清和靈寶兩家(尤其靈寶)大概能意識到法箓在行法和儀式方面的意義,故相對較早就開始有意識地創作自家法箓。簡言之,我的觀點是上清和靈寶素來不重視法箓,但陶金的觀點則是二者對這一道教要素也頗為重視。透過本書第三章的詳細分析,可發現陶金的反對和糾錯大概更有道理。
這部書的第三冊由【授度】和【余論】組成,是四冊裏最薄的一本,但卻是全書論證鏈條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如上文所述,本書第一冊主要研究盟威道義理源流和框架,第二冊重點放在對占據義理中心的法箓的剖析,而第三冊則主要討論傳授法箓等要素的授度儀式。三冊書稿組成的「義理框架-中心法箓-授度儀式」的結構,層層遞進、彼此貫通。有關道教儀式的討論,原本是國內道教學研究中最薄弱的領域之一,但透過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勞格文(John Lagerwey)、陳耀庭、呂鵬誌等海內外老中青數代人的努力,道教儀式已逐漸成為熱門話題,以至於對年輕學者而言,論道教而不及齋醮道法、煉度召遣便可能被貼上「不預流」的標簽。盡管專門研究道教儀式的學者群體仍不算太大,但這個領域卻已不再像曾經那麽「冷門」。道理很簡單,「熱門」內卷嚴重後,「冷門」自然會成長為新的熱點。這一章對正一授度儀式的內容、儀式結構、符號象征進行分析,除很好地梳理出授度儀式的框架和模型外,更對儀式中所蘊含的「玄理」進行剖析。這一章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二十節「升度儀式與義理考察」。「生無道位,死為下鬼」,既然道士生前恩受法箓獲得「道位」,預定了仙界的入場券,那麽身故之後自當舉辦與俗有別的對應儀式,完成羽化登仙的最終步驟。這一節指出道士死後升度儀與生前授度儀之間存在對應關系,並以2021年3月11日,依閭山法為著名海外漢學家兼道士施舟人舉辦的「三界解釋召職登仙醮」為例,細致地描述了一例升度儀式的完整面貌。這段內容讓我們在緬懷前賢的同時,收獲了對道教儀式的深刻理解。
對我個人而言,全書的第四冊可能「最有用」。盡管作者僅將之作為【附錄】掛在最後,但這部份內容給出的受箓文書、儀式以及有關宋元道教轉變、法職體系要素的討論,均以具體案例輔助著前文對正一道法箓盟約的論述。附錄中,不論是江西修水的【都功箓】、甘肅民勤的【坐靖參傳】儀式,還是流傳至今的宋以後三種法箓傳度文憑,都以新材料的性質吸引了我的眼球。書中有關宋元道教轉變要點的討論,作者梳理出近世以來,道教授度體系中模仿漢官和宋官的兩種體系的調和過程。正如我們所熟知的那樣,這樣的調和在各種版本的【天壇玉格】中表現最為集中,作者對這部文獻的分析和使用非常充分。附錄二,有關從三山(龍虎山、茅山、閣皂山)並立、到「三山混一」、再到龍虎山以「萬法宗壇」的名義統轄道法的過程的分析,值得關註。其中對涵蓋越來越廣、成分越來越復雜的「正一道教」的歷史脈絡的整體把握很有指導意義。附錄中有關當代道教田野研究「學術倫理」問題的強調,提出了一個值得廣泛關註的問題。或許是由於擁有insider身份的原因,作者對道教的熱情比一般道教學者強烈很多,由此也對道教研究中可能涉及的倫理問題(尤其是可能對道教帶來傷害的現象)頗為敏感。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道教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宗教,學術研究對當代道教內部必須守護的秘傳要素的不當公開,可能會傷害信仰者的宗教感情,同時也可能造成擾亂當代宗教生態的後果。事實上,這樣的違背學術倫理的研究行為,不僅會對道教產生傷害,對學術研究的持續發展也並不像看上去那麽有利。公開「秘密」最初確實會令我們因收獲新材料而欣喜,但反復如是,恐怕學者將很難取得信仰者的信任——信仰者像「防賊」一樣提防披荊斬棘行走在田野中的學者,深藏密寶,不再外借。顯然,這不是一幅令人期待的愉悅畫面。或許學術研究確實是無疆界的,但「宣傳」恐怕還是要考慮到最基本的原則。
以上擇要介紹【盟約】的內容組成,接下來從個人閱讀感受出發,就這部著作的價值和疑問稍作闡述。本書最大的學術意義自然是完整地梳理了正一道的盟約和法箓制度,並對這些制度的教義玄理進行系統性闡發,在此基礎上隱約形成了一個以原始盟威道「清約」為核心的道教教義框架模型。本書無疑是目前最具整體思維的同型別著作,具備承前啟後的學術意義。作者資料性和思想性並重的取向,田野工作與文獻考察相互印證的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推崇的研究和撰述模式。書中將盟威道若幹原理與猶太教進行比較的做法,也令人耳目一新。以往的道教比較研究,常常將佛教置於比較的另一端,佛道比較雖常以「找不同」來呈現二者特色,但更多精力則放在用「找相同」來展現二者可能存在的交涉歷史。作者以猶太教替換佛教成為道教的比較物件,透過「找相同」的辦法,將猶太教研究中一些已經獲得較好處理的主題挪用為道教研究的問題意識,從而呈現盟威道及其義理的重要價值。對比項不同,發現自然也不同。唯需說明的是,佛-道比較與猶-道比較的出發點和希圖解決的問題不同,各有優勢,沒必要厚此薄彼。
對影像的充分呈現,也是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以建築設計師為本職的作者,對影像和美術具備異常的興趣和感觸。書中大量的影像,不僅來源於對既有材料的截取,更有不少來自於作者及其朋友的創作。影像與文字交相輝映,形成獨特的視覺系統,給閱讀增加很大的樂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一些道教文書和影像比較長,對這些影像的表現非常考驗出版社編輯的技術水平。手頭這部書中穿插折疊的長圖,兼顧了美觀與實用。然而,在制圖方面或許也存在兩個美中不足的地方:第一,彩圖部份出現過分靠近中縫的現象,給影像內側部份的閱覽造成困擾;第二,書中一些圖示可有可無,甚至毫無必要。如述及中國古代掌控姓名便可控制人、鬼的信仰時,作者給出動畫片【千與千尋】中湯婆婆將主人公名字部份收入掌中從而獲得掌控和支配主人公權力的案例以及圖片(同時還給出動畫片【夏目友人帳】中主人公掌握鬼怪名錄的情況作為另一個案例)。前後文對名、錄(箓)的解釋已足夠清楚,沒必要使用這樣的材料輔助論證。如此論述,可能增加閱讀樂趣,但卻與全書的整體格調不和,有失嚴肅,弄巧成拙。彩圖裏已切開的心裏美蘿蔔,大概與【千與千尋】劇照達到了異曲同工的負面效果。瑕不掩瑜,這些小問題不能掩蓋整套書影像系統的精美考究。
這部著作優點不少,但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疑問。從個人的立場和學識出發,我對書中的某些觀點表示理解,但卻無法達成認同——文章像河,終於流淌到「吃瓜群眾」喜聞樂見的河段。
我對這套書最大的疑問主要是有關盟威道義理「玄解」的一些內容,尤其是對作者總結盟威道義理的方法和解釋向度心存疑惑。這個問題,往根上說,涉及研究立場(insider-outsider)和思想研究中的「照著講」和「接著講」的爭論。有關盟威道義理系統的構建,集中體現在第一冊後半和第二冊中。作者在構建義理系統時,對材料的選擇比較自由,時間跨度有時也比較大。如此建構起來的盟威道義理系統,很難說真的符合盟威道最初的現實情況,其可能只是作者透過取擇材料外加合理想象制造出來的「理想化盟威道樣態」。但作者對這個理想化的樣態非常熱衷,常以之作為「標準」來衡量後世道教現象是否墮落腐壞。下面以書中花費大量篇幅著重探討的鶴鳴山盟約和「清約」精神為例,簡單談談上述問題。
作者對傳說中發生在鶴鳴山的張道陵從老君受道事件(簡稱鶴鳴山盟約)頗為關註,將之作為盟威道「盟約」的起始。道教內部材料給出的鶴鳴山盟約發生在漢安元年(142)五月一日,對一般學者而言,會暫時擱置事件本身的「真假」不論(甚至簡單地將之視為張魯政權創造的傳說),而將精力放在考察傳說出現的時間、背景和後續影響上;但對道教信仰者而言,這一事件卻是不可置疑的真相,大道「下教」張道陵的情況如教內文獻描述的一般無二、真實不虛。作者對鶴鳴山盟約的解讀充滿新意,但立場卻顯得有些遊移。簡單來說,作者既認為這場鶴鳴山盟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將之作為大道下教的重要案例反復強調,但同時又對之做出更為內在的解讀,稱:「鶴鳴山盟約並非發生於身外,是天師心中的一次靈光的閃耀,而這種難以名狀的密契體驗需要領會,並轉化為人類可以理解的資訊」(245頁)。類似的說法,在書中反復出現——「鶴鳴山石室內所發生的事件雖然可以被稱作‘建立盟約’與‘傳授道法’,但其內在實質則是天師在冥通之中所獲得的全身心的感知與領悟,所謂的老君、道氣,與其說來自身外,倒不如說緣自身中一種極為內在的宗教體驗」(333頁)。由於將鶴鳴山盟約理解為天師內心的「靈光閃耀」,此次「老君-張道陵」之間的傳授便被理解為「人類自性覺醒在歷史中的具體表現」(第1頁),同時這樣的靈光閃耀也可以在天師之外的後人心中獲得重復——「不僅顯現在天師的心神之中,且還可重復迸發於我們後人的心神之中」(237頁)。這樣的理解,既與將鶴鳴山盟約作為真實仙道事件的教內解說不同,也與一般的學術理解相異。從根本上來說,這樣的認識是推測性的,得不到現有文獻的有力支持。但與此同時,這樣的推測也因缺少依據而無法被證偽。無法被證實和證偽的問題,大概就不再屬於常規文史哲領域討論的範疇,而應當被理解為對道教神學的創造性理解。有關於此,真誠地講,我可以理解作者對鶴鳴山盟約及其意義的解讀,並覺得這樣的解讀對教義建設而言很有啟發價值,但在個人的學術立場上卻很難完全給予認同和接受。從學術立場上看,我們似乎僅能確定這個盟約是曹魏或更早一點出現的盟威道傳說,而並不能由這樣的傳說推測大約一百前年所謂鶴鳴山盟約的真實情況——如果不是徹底而冒失地否定其真實性的話。
接著來看「清約」。作者將早期盟威道的核心價值總結為「清約」精神。這個清約精神不局限於常常被提起的「神不飲食,師不受錢」原則,書中對早期盟威道優越性的集中表述可以被視作對「清約」精神的總結:「盟威道是一個面向平民大眾,試圖打破年齡、性別、階層、種族界限,以道氣使人類共命的宗教信仰與實踐體系,其具有以道德為先導的理性精神,以及以此賦予人類自由意誌的自由精神。盟威道的教法並不與塵世中的生活脫節,但其著眼點則在於終極的生命超越。」(834頁)作者總結的以「清約」為核心的盟威道義理閃耀著超越時代的光芒,但正如前文所述,作者總結義理的方法與常規學術意圖呈現歷史切面的旨趣非常不同。透過較為開放的選擇和串聯道教材料,作者組織起一套看似自洽的義理系統,但這個體系可能無法完全貼敷歷史上任何時間點的盟威道真實情況。這樣的教義組織辦法當然也有啟發性,尤其是對道教教義建設和道教信仰者而言充滿著難以抗拒吸重力,但卻也不是以「求真求實」為目的的常規學術的訴求。嚴格地講,書中以「清約」精神為中心編織起的盟威道義理系統,是作者用巧妙的構思創造出的理想模型。這樣的教義研究,不能算是「歷史學的」和「文獻學的」(照著講),但卻很有點「哲學的」味道(接著講)。常規學術的「求真」,與作者所追求的「求善」之間的張力,由此得到凸顯。理想的「清約」光芒萬丈,書中甚至產生類似「本質主義」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將是否符合「清約」視作衡量道教進步還是墮落的重要標準。例如,盟威道中,功能性「內箓」(如斬妖捉鬼等專門功能)的產生可能要晚於所有道民都可逐漸獲受的「外箓」,作者對這些「內箓」的批評顯得頗為苛刻:「‘內箓’‘外箓’之說,實際違背了盟威道教團最初的平等主義宗教精神。由此,‘內箓’的出現,應該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六朝時期,教團內部的日漸階層化,以及祭酒的職業化。新的‘內箓’應運而出,被置於‘外箓’之上,旨在賦予祭酒更高的神權與身份。因此,所謂的內、外法箓之別,實際是少數的祭酒用意將自身淩駕於多數道民的一種途徑。」(566頁)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也很難定論。如果站在insider的立場上,會認為內箓的功能真實不虛,這些內箓跟外箓一樣都是「大道的點化」,而不是壞心腸的祭酒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虛偽創作,因此不會去考慮是否涉及平等和霸權的問題;而站在outsider的立場上,不論內箓、外箓,都無法證明盟威道是力求平等的教團,教團內部的等級一直存在,只是等級之間可以透過立功立德來實作跨越。這樣的層級躍升,普遍存在於世俗社會的軍功等爵和官階制度中,但我們卻不會承認古代社會中的此類制度和等級安排體現了豐富的平等主義精神。本書第三冊最後部份,對張天師「整合形象」的想象,也與「清約」精神相呼應。凡是符合「清約」精神或作者總結的早期盟威道特征的張天師傳說形象,最終都成為重組張天師整合特征的材料;反之,不符合者則被認為是後出的傳說故事,是對天師真實形象的歪曲。這樣的「復原」非常有趣,但卻陷入了迴圈論證的圈套,有思想價值,但可能沒有多少學術意義。
以鶴鳴山盟約和清約精神為例,可以較為直觀地看到作者對盟威道教義的解讀與一般學術理解之間的差異。作者給出的義理系統建構,或許不是為了尋找某個道教史切面的真容,而是希望呈現一幅濾鏡下的盛世美顏,為我們提供盟威道最優美的模樣。遊走在「虛實之際」的做法,有時可能是非歷史的、非思想史,甚至還是非文獻的,但卻是這部書貫穿始終的一種特色。這樣的教義解讀方式或許將成為本書最可能被駁難的問題。但需要註意的是,非常規學術的解讀,不意味著就是「無意義」的思考。從文字中時常顯現和切換的insider-outsider雙重立場上不難發現,作者在進行盟威道義理建構時,重點本來就是在一定的文獻規矩內為道教教義賡續找到一條守正創新、繼往開來的思路。這樣的現世關懷,使本書的教義建構更多地指向「神學」而非「歷史學」。當我們理解了作者撰述的旨趣時,也就能明白此書義理解讀的價值所在,不至於耳提面命地「站在學術高度」上對之進行刻薄批判。以文史哲的嚴肅方法給書中梳理出的教義系統一一「糾錯」,既沒必要,又無聊透頂。作者本就意不在此,那又何必以我之繩墨尺度他的規矩?當然,就筆者個人的閱讀和思考而言,我當然能夠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也認同此番解讀的理論意義,但傳統的學術價值觀(尤其是歷史學和思想史立場)深刻地固化了我的思維,使我始終不太能接受這樣的處理範式。求同存異,各取所需,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不失為一種明智而開朗的應對辦法。
除上述較為宏觀的問題外,我對書中的一些史料解讀也心存疑惑,這裏不妨簡單舉幾個例子。呈現早期盟威道情況的道教文獻【大道家令戒】,稱老君傳授張天師,「造出正一盟威之道,與天地券要」。一般我會將「天地券要」理解為一類券契,與「正一盟威之道」並列,都是老君「造出」的內容。但作者則將之理解為「是指在天地的鑒證下,老君與天師分券立約」(235頁)。有關這個問題,經過與作者激烈的半公開討論,我仍很難理解相應觀點,而作者也無法接受我過於平庸的解讀。又如南朝高道陸修靜在提及盟威道錄籍時稱:「道科宅錄,此是民之副籍。」作者認為,「副籍」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相對於地方官戶曹手中掌握的‘錄籍’而言,一種是相對於天曹手中所掌握的‘命籍’而言。」作為神靈的「守宅之官」按照這個副籍守護家戶。作者推論,「如果(副籍)只是一份如‘戶口簿’一樣的物品,很難具有神聖的效力使得‘守宅之官’蒞臨」,故懷疑這是一種「契券」(532頁)。但陸修靜對「副籍」的解說,指出「籍主皆賫錄詣本治,更相承錄,以註正命籍」,則這裏的「副籍」,似乎更應該理解為戶主(籍主)手裏保存的、寫明自家戶口情況的「籍簿」,其「副」應當是與「領戶化民」的道教祭酒(不是地方官)手中保存的集體錄籍相對而言。副籍或可平實地理解為守宅神靈執行保護義務的依據,而不必解釋為調動神靈的「券契」。從「去神秘化」的角度來進行解讀,我懷疑之所以強調提供神靈守護與副籍記述掛鉤,可能是為了保障民戶及時報備人口變動資訊的信仰和行政策略,以使祭酒更加有效地掌握「領戶化民」的權力。
再如,著名的【老子想爾註】中稱:「腹者,道囊,氣常欲實。」作者對「氣常欲實」的解釋是「道氣在主觀上意欲進入人體」(705頁)。但我卻懷疑這句話是典型的倒裝句式,「氣」不是主語,「常欲」也不是「氣」的意圖——正常語序應該是「常欲氣實」,意思是最好一直用氣充實肚子。類似的倒裝句式並不罕見,若堅持按照字面順序理解,則不知【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裏服氣導引時的「衣帶常欲寬」當作何解。對於「氣」「道」等關鍵概念的過分敏感,可能導致鉆入「玄義」牛角尖的錯誤結果。還如,作者認為將正一、靈寶、上清理解為「相互對立、各自獨立的三支教派」,是「以西方宗教的教派主義來對中國宗教進行歪解,其本質上是對經典的粗淺誤讀」。事實上,上清和靈寶「乃是在各自的理路之下,對自身盟威道信仰的提升與處境化調適」(895頁)。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上清和靈寶確實出現於盟威道已經存在的社會和信仰環境中,由此接觸和接受盟威道的某些理念非常正常。但我個人認為,「青出於藍而不是藍」,刻板地將三家並立,甚至認為存在連綿不絕的「上清派」「靈寶派」,絕不是與歷史相符的認識,但三者之間的重大差異(甚至是本質差異)也不能因此而被抹殺。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傳統的奉行者(或者說背後教團)確實存在交叉,但卻並不完全相同。將強調三者差異的理解說成是「對經典的粗淺誤讀」,是從一個極端跳躍到另一個極端的過猶不及,不無意氣用事的感覺。
除此之外,作者對北魏道士寇謙之有關正一道都功版「遷還本治」的理解的反對,看上去也不無過分演繹的嫌疑(822頁及之後,相關內容略微有點繁復,讀者可自行翻閱)。基本上,我個人還是傾向接受寇謙之提供的更加平實的解釋——即「遷還本治」還是指天師降曹後,流散在外的教民未來有機會回到原本的二十四治(或二十八治)治區,而不是在講這些教民死後升入仙界的「大治」的事。至於書中有關南北朝時期多次出現的傳授張道陵道法的「新出老君(老鬼)」(一般認為等同於太上老君)的玄妙解釋,「大道既然永恒,何言‘新出’?老君既‘老’,又何以言‘新’?這些看似自我矛盾的表述實際正反映出了大道的本質:太易」雲雲(307頁),新穎無比,但也超出了我所能接受的底線。類似情況還有不少,這裏不再一一鋪述。整體來說,作者對道教文獻和現象的部份解讀,趨向於挖掘奇妙、玄奧的義理,確實富有創造性和啟發性,但對於我這樣缺少想象力的頑固頭腦而言,卻造成了領悟上的嚴重困擾。
觀點之外,可能是因為寫得太快,也可能是因為書稿太厚校對不易,錯別字、遣詞不恰、句法錯誤稍微有些常見。這樣的錯誤不僅影響閱讀體驗,有時還會誤導讀者對作者意思的理解。如書中提到放馬灘秦簡「丹還陽」這個材料,作者稱這「本質上是一份秦昭襄王三十八年由地方縣丞向秦國禦史上呈的公文」(101頁)。但學界普遍認為這個材料的「本質」是一篇誌怪故事,只是呈現為公文的形式。經過與作者的直接交流,作者也承認「丹還陽」實際是誌怪。「本質」這樣不當詞語的使用,幾乎讓人以為作者對這份材料的性質存在誤解。此類問題重印時應當一並改善。
總體而言,這部著作具備較高的學術意義和啟發性,但也存在一些可以繼續商榷的問題。而不論是價值還是問題,都足以引發廣泛的關註和持續的討論——價值和爭議並存,是優秀著作的典型標誌之一。與作者的多年私交不能抵消我對此書材料解析和歷史描述方面的疑慮;同時,這些疑慮,甚至不滿也無法阻止我對書中描述道教義理架構時的勇敢睿智以及作者之於道教的熱誠表達贊美和肯定。一篇萬把字的書評,無法完整地完成對這部兩寸來厚的著作的分析。接下來一段時間,對本書的討論或許會形成熱潮,這有可能成為辨明正一道教演化過程若幹重點問題的良好契機。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互相參看,興許會在爭議之中收獲意外的發現。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