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上海書城經過改造復歸大眾視野,重新開業當日眾多老書迷湧入福州路上的「精神家園」,朋友圈裏還見到幾位媒體朋友拿著長槍短炮競相直播,也引發了公眾對於書店空間沿革的討論。恰巧,我在【三聯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則讀者來函,這位讀者表示自己所在的縣城中心開設了一家大型書店,無奈這是一家「無法看書」的書店,環境豪華,圖書周邊琳瑯滿目,可偏偏書籍皆被塑封,店員說拆開了就得買下,不由讓人悵恨久之。似乎已經無需再議書及書店的尷尬現狀了,許多人回望曾經的的閱讀熱潮,向我們不斷講述當年的榮光,但昨日的狂熱已是手裏的月光。

在當今這個時代,書、書店還能給人感動,予人慰藉嗎?當拿起【送書人】這本小說的時候,內心是充滿忐忑的。
作者卡斯滕·海恩在扉頁的獻詞裏如是寫道:「獻給所有的書商。即使在危機蔓延時,他們依然為我們提供著獨特的食糧。」小說刻畫了一個受雇於書店,不斷為城鎮居民推介書籍的「送書人」——卡爾·柯霍夫。在書店實習生眼中,這位格格不入的老年員工稱得上時代的活化石,這家夥不看新聞,不聽廣播,也不讀報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舊秩序的捍衛者。不去送書時,就躲在那個堆滿了書的兩平米裏,那是他自我保護的精神空間。唯一可以讓他興奮的或許就是向不同的人推薦不同的書——「這本書,自從上市就一直在等您。」再挑剔的讀者也被他說服,其他員工認為的「硬茬」在卡爾面前都十分服帖,他的淵博學識以及獨到眼光讓眾人敬佩。
「反正我不看書,除非是被逼著看——也就是在學校裏。要是書被改編成電影,那我寧可看看電影。」這不是一個孤芳自賞的故事,書店小年輕的話很輕易地就拆穿了歐洲「全民閱讀」的幻景。而目下的現實恐怕是連電影都激發不出大眾的興趣了,一部電影的敘事被人工剪輯、AI配音,最終變成3分鐘的短視訊,跳過那些冗長、無趣的蒙太奇、空鏡頭,所有的爆點、沖突轟炸著受眾的神經,這樣一比較,讀書顯然是太慢了也太乏味了。這不由讓人想起英國地鐵乘客爭相讀書的段子,不是因為他們愛看書,而是因為地鐵裏沒有網路訊號。這種調侃是一種科技進步下對於外國月亮的祛魅,更是一種對現代圖景的白描。我們有多久沒有讀過書了?我們又有多久不曾在書店裏打發時間了?如果卡爾失去了送書人的身份,那麽他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將塌縮到一個獨居老人的逼仄情狀,書是他連線他人的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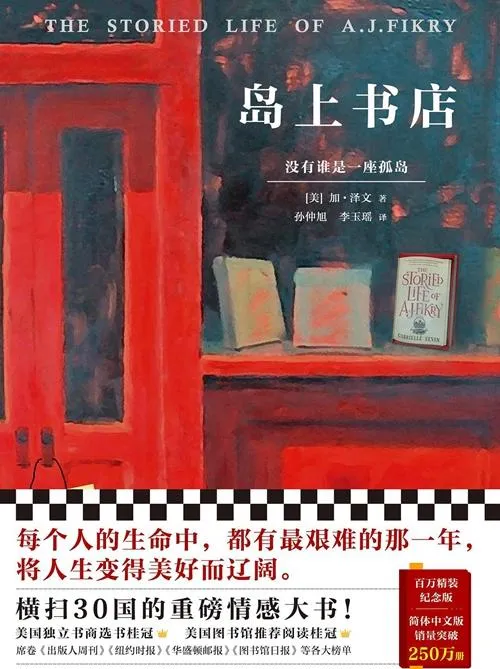
小說文本的通俗流暢,讓我想起了另外兩本大名鼎鼎的小說【島上書店】和【查令十字街84號】,它們擁有近似的敘事內核,呈現在讀者面前是的書、書店以及與書有關的人,讓人沈浸其中不住回想的是人類與書過去的溫存。【島上書店】在亞馬遜暢銷榜霸榜的時代,網購尚未成風,一本【讀者】或者【故事會】可以全班傳閱,麥考林商城小畫冊可以翻來覆去地看,彼時的貧瘠也是彼時的充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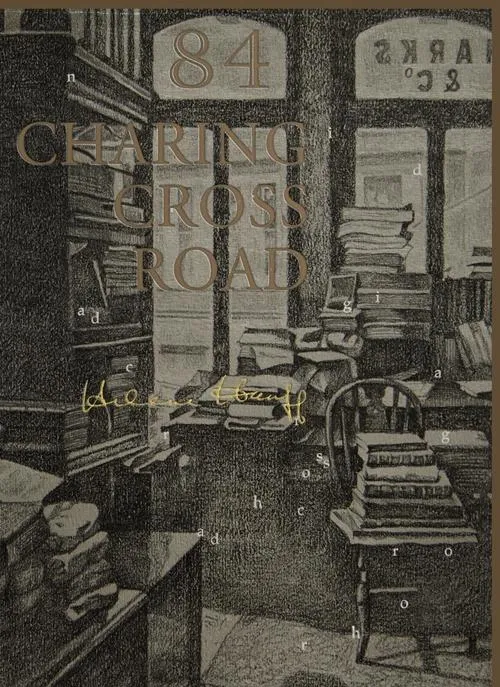
現在的科技主打一個「萬物互聯」,手機可以連線所有裝置,房子、車子、票子都可以用一個終端解決問題,各大廠商比拼誰聯得多,誰聯得方便。問題是,和物的連線越來方便了,大家都在暢想帶著VR眼鏡利用虛擬現實走向未來,人與人的連線反而越來越難了。

「辭典,是橫渡詞匯海洋的船,人們乘坐辭典這艘船,搜集漂浮在漆黑海面上的點點星光。只為了能用最恰當的措辭,準確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傳達給他人。如果沒有辭典,我們只能佇立在這片浩瀚的大海前,駐足不前。」小說【編舟記】裏,松本前輩的這段話猶如理想主義的星火,很文藝地向讀者表述了編纂辭典的意義。但是僅有理想和認真的態度,依靠個人也是無法完成這種費時費力的偉業的。
與卡爾一樣,同樣是親近書的主人公,馬締光也亦是一個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人。聽聞馬締要被調動到辭典部,原部門所有的人都不在乎,在出版社營業部這家夥沒有絲毫的存在感,不能帶來任何經濟效益的員工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在豆瓣上,常看出版社友人們互相調笑,辛辛苦苦做了書,下班進了書店,買了同行賣不出去的「大作」,完成了一個出版社編輯「編書-購書」的完美閉環。愛書人本身就是如卡爾、馬締這般的「怪人」,為了一個善本可以忍饑挨餓,寧可住得局促也不願意丟棄書籍。
同名電影【編舟記】中的馬締透過松田龍平的演繹更顯內向與窘迫,他甚至無法與其他人產生交流的可能,面對心愛的姑娘也堅持用文言文寫作情書表達愛意。他希圖完成編纂【大渡海】這本辭典,而拯救他的也是辭典編纂本身。人試圖用詞語來定義世界,感受就是命名,然而再豐富的詞藻也無法完滿地詮釋人,在【編舟記】這裏,辭典是渡過浩瀚無窮的大海的扁舟,只要有渡(渡人或渡己)的需求,就必定存在想要達到的彼岸——他人的心靈,完成與他人的連線,證明自我的存在。
「詞與詞之間相互補充、相互支撐,保持著絕妙的平衡,形成一座搖搖欲墜的塔。」在制作一張張詞例收集卡的過程中,馬締光也從一個個詞匯中尋找到了一些涉及心靈的秘密,逐漸地開始與人發生聯系,對於辭典編纂工作的真情投入,感染了越來越多的同仁,耗時十多年終於完成了【大渡海】。小說作者三浦紫苑在文本中設定了大量的「彩蛋」,如果是一個愛書人的話,一定會對作者的巧思會心一笑,在這種精心設定的伏筆下湧動的是作者對於書的熱愛。我不覺得【編舟記】的故事是一種抵抗敘事,它並沒有大肆渲染新技術的威脅,在出版圈裏壓力是始終存在的,選題、定價、庫存每一個概念都會給編輯造成切實的壓力,但是【大渡海】這一計畫的設定是為了順應這個時代,編纂過程中的坎坷、不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主編松本對於馬締光也的期待那般,詞語也是在不斷前進演化的。人與人的連線或授權以由電子訊號取代,但是如果有新的詞句能夠表達人的內心,我們就還有另一種選擇、另一種可能。

如果這種可能是書的話,那麽懷舊不啻為一種展望。在一些特定的歷史場景下,書所蘊藏的不僅是一種抒情。小說【偷書賊】所講述的故事較之於【送書人】更為極端,但也更為典型。籠罩在戰爭陰雲下的人們透過偷書、念書的行為,維系著對於生活的希望。這類故事的起源或授權以追溯到薄伽丘的【十日談】,人物設定與劇情安排都似曾相識,但是大多數讀者還是會被同一套配方俘獲。因為書在這裏的象征仍舊會觸碰到人類精神世界中的柔軟維度,在被科技包裹地越發嚴實的同時,心靈的衰減是不可逆的。不久前,Open AI公司發生的「內訌」,源自於一些AI專家對於新計畫可能威脅人類的警惕,在名為商業利潤和人類道德的天平兩端,一些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這或許也部份回答了,為什麽【送書人】【偷書賊】這些有關於書籍的小說能夠持續打動人心。
「這座城市是圓形的,穿行其中的人未必註意得到,但每只斑尾林鴿和麻雀肯定都一清二楚。」【送書人】裏的卡爾·柯霍夫堅持為每一位「需要書」的人推薦適合他們的書籍,在一次次的送書、答疑的過程中,卡爾與讀者之間產生著微妙的化學反應,72歲的他顯然不再年輕,但他仍會止不住地揣測對方的興趣、生活以及周遭的一切。「我就像鐘表的指標一樣。你可以設想,一根指標可能是可悲的,因為它始終沿著相同的軌跡轉圈,周而復始。但相反的情況是,它很享受路徑與目標的確定性、不會走錯路的安全感,一直確保著有效和精準。」實在感與確定性,它既決定了卡爾工作的孤獨,也給了他這個時代稀缺的安定與自在。這或許就是書的明天,以一種特有的穩定感留存在這個時代的角落裏,等待著它的讀者,等待著我們。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