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以談話治療為主,分析被治療者意識之下的「無意識」,使其心中郁結得以破除。
抑郁癥兩端:哀悼與憂郁
如果不是病,那麽抑郁癥對於精神分析來說是什麽?創始人佛洛伊德將自我意識的結構分為這樣幾個層次:前意識、意識、潛意識與無意識。盡管在他之後如榮格、克雷因、拉康、溫尼科特等精神分析學家處,這一結構已然發生諸多變化,但一些基本原理相通:意識(包括潛意識)是我們能夠把握到的所想事物,它如同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海平面下則是巨大的無意識,即明明是我們所想,但無法直接把握到的事物。無意識真正決定著我們的精神與行為,其更多是一種原始沖動和本能,不符合社會標準,因而在日常生活被壓抑下去。而有一些溢位的無意識仍然能夠透過夢話、囈語等形式折射出來,這便是潛意識。精神分析更為重視對無意識的探索,並積極利用談話、分析下意識的行為及囈語等探索無意識,以破解一些行為產生的真正原因。於是,對於精神分析來說,抑郁癥並非一種病,而是無意識對精神的塑造,只不過這種塑造以一種病態的行為呈現。
何以是病態?利德請我們回到佛洛伊德在1915年發表的文章【哀悼與憂郁】:「抑郁」這一狀態太過籠統,它有著各種臨床形式,有人沈默寡言而有人狂躁不堪(如雙相情感障礙),而佛洛伊德希望獲得一種具備普遍性的結論。他使用「哀悼」與「憂郁」兩種癥狀來介入研究——抑郁癥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及沮喪,對外界世界喪失興趣、喪失愛的能力,抑制自身行為並且常出現自我評價降低及自我譴責,而這與哀悼十分類似。佛洛伊德筆下的哀悼並非一種社會意識,而是一種失去他人或某物之後的私人情緒。當重要的人離世,我們也會感到痛苦不堪,常常出現音容猶在的幻覺,甚至會出現【甄嬛傳】中「宛宛類卿」式舉動。佛洛伊德認為,哀悼是一種人們對喪失的反應。由於心愛之人或心愛之物的失去,人們投射愛慕並產生行為驅力的「力比多」此時喪失了方向,因而人會出現極大痛苦。但是,哀悼行為是有助於身心健康,或者說是「正常」的。這是因為,哀悼者知道自己喪失的是什麽,他的一系列痛苦,不僅是在表達對失去之人及物的愛慕和情感依賴,同時也是在表達對其失去的莊嚴宣告。我們最終會承認這個人或物的不在,並且積極利用某種象征化的手段將其「留在體外」,以使得殘留的力比多仍然繼續向外投射,不會在自我之處郁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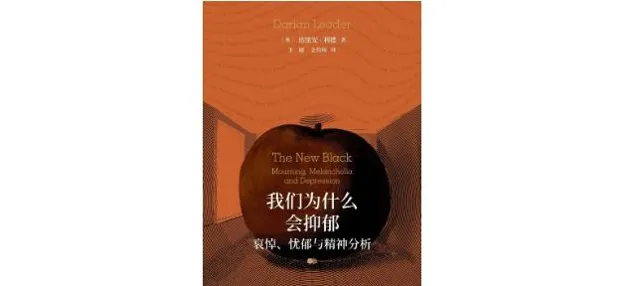
因此,利德也提及了哀悼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用零散的元素羅列,來表達對失去之人或物的殘存之愛。毋需參照書中的諸多藝術案例,我們使用一則通俗的例子,歌手譚維維在【我是歌手】演唱的歌曲【烏蘭巴托的夜】。這是一首悼念亡父的歌曲,以A段進入,悠揚的曲風描述著烏蘭巴托草原的夜色,父親的形象被象征化為草原的夜色,成為曠野的風。而B段則以濃情奔放的方式直言對失去父親的悲慟。兩段交錯進行,經歷數次B段的怒嚎式哀悼後,最終回歸至A段結束,也即哀悼的結束。在此,外物的象征既成為能夠隨時開啟哀悼思緒的入口,卻又成為停止哀悼的出口,如同草原夜色既成為了父親形象永久的象征化,又表達了對父親逝去的承認及看開:哀悼沒有一直停留在怒嚎所隱喻的內心痛苦中,而是最終留在了寧謐草原上,留給曠野的風。
那麽憂郁呢?與哀悼相反,憂郁者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麽。或者說,他否認自己失去了。失去的感覺被歸於無意識,其仍然向著被失去之人或物發射力比多卻沒有方向,於是,哀悼的物件轉向自己。憂郁者對自我評價的降低及自我責備,恰恰是對那個失去人的責備,責備他們離開自己、讓自己憤怒或傷感。佛洛伊德在這裏提到了「自戀」(narcissism):憂郁氣質的人往往與過度自我迷戀有著關聯。這是因為具有自戀人格的人更容易將力比多投射到自己身上來,哀悼的物件成為自己。這就產生著一種巨大的矛盾——美國學者朱迪斯·巴特勒在【心靈的誕生:憂郁、矛盾、憤怒】一文中一針見血點出,自戀實際上是每個人都具有的特質,我們自己必然會愛自己。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對自我的訴求總是擁有一種補償性機制,即我們會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會補償在他者身上訴求時得不到的東西。但當我們將物件的哀悼轉向自我時,自我又同時成為了一個失去的、無法補償的存在,這就在矛盾中造成了對自我的巨大折磨。我們會拷問自己「我到底算個什麽」,繼而耽溺在種種負面情緒中、困囿在精神內耗裏,並且無法走出自我的牢籠。抑郁癥誕生了。
利德舉出了一則令我們驚詫之余又覺得理所應當的案例:一個年輕人和女友墜入愛河,並決定結婚。當他正準備將自己的戀愛經歷和結婚決定分享給家人朋友時,意外發生了,女友出車禍意外而死。他尋求哀悼,可是,無論當他向親友傾訴,還是去探望女友的家人,他的處境都無比尷尬——在自己這一側,沒有人認識他的女友,而在另一側,沒有人認識他。「女友」這一身份,對年輕人來說變得無比虛無縹緲,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哀悼誰,這也就理所應當引出我們剛剛說出的話:「我到底算什麽?」無法向外投射的力比多引向了自己,對女友的哀悼變成了憂郁,而他也就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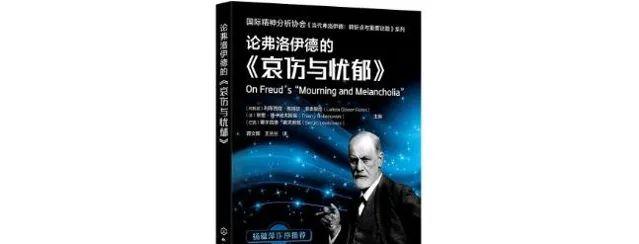
由此可見,哀悼與憂郁的區分在於是否有一個明確的「他者」,一個令人知曉的失去物件。當這個物件是明確的,我們就可以正常將失去的痛苦向外部投射,並透過象征化過程使其轉移到其他物件上,緩解這種痛苦。而當我們不清楚這一物件是什麽時,我們就只能將痛苦轉向自己,在自我心中產生巨大郁結。不過,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佛洛伊德的【哀傷與憂郁】經歷過諸多紛爭與反對,而對於兩種行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更加深入和明晰。
哀悼的重心,是消除憂郁
對佛洛伊德表現出激烈反對的包括精神分析學家亞伯拉罕與克雷因。兩者的共同觀點在於,其認為佛洛伊德將哀悼的過程看得過於簡單了。我們對一個人的感情沒有單純的愛,也沒有單純的恨。愛恨總是交織在一起,當我們對逝者責備其為何狠心拋下我們離開時,內心也總存在著「你可總算走了」的部份。
不存在純粹的愛或恨,克雷因在【哀悼及其與躁狂性抑郁狀態的關系】一文中提出了這種嬰兒時期便存在的原初情形。佛洛伊德曾經根據人的心理滿足的不同部位分為幾個階段,在嬰兒時期是口腔期,即吮吸母乳得到滿足,後來是肛門期,即收縮肛門得到滿足。再後來性器官逐漸成熟,心理滿足依次經歷性蕾期、潛伏期和生殖期。克雷因認為,嬰兒的抑郁情感在口腔期末端,也就是斷奶前後達到高峰。對於嬰兒來說,母親的乳房與乳汁代表了愛、善意與安全感,也是自己全部的欲望來源。一旦失去了乳房,他會感到悲傷,哀嘆這樣一個自己所愛之物、一個「好」客體的失去。但同時,嬰兒又意識到,乳房的失去可能恰恰因為自己曾經將其視為一個「壞」客體——他會用力吮吸、撕咬、用哭泣獲得乳汁等,正是他曾經這些恨的情緒使得自己最終失去了它。於是,嬰兒開始自責。克雷因將這一時刻稱為「抑郁位態」,在這裏嬰兒分清了好與壞、愛與恨的一體兩面,並且同時誕生了哀悼與憂郁兩種情緒。

也即是說,從嬰兒開始,我們便實際意識到哀悼總是伴隨著憂郁,二者成為一個連續體。一個常見的例子是,當面對一個重要之人的逝去,哪怕他的死亡與我們並無直接關聯,我們也大概也會考慮「如果他怎樣怎樣說不定就不會去世」,這實際上引發了對自我的譴責。既如此,哀悼與抑郁便不再位於正常與病態的兩端,哀悼的任務也不是讓力比多繼續向外部物件投射,而是在哀悼與抑郁都產生之後,消除其中的抑郁成分,修補自我譴責,以使得人的精神回歸正常。口腔期到肛門期便反映了這一過程。拉康對此做出了絕妙的闡釋。他認為,兒童的心理滿足之所以會轉移到肛門,是因為這表現了他正常融入了社會,融入了被他所稱為的「象征秩序」中:兒童的肛門能夠主動控制收縮,能夠在合適時機進行排便,能夠自己擦屁股,這表示其能夠像一個社會中的正常人一樣生活。而這種活動,能夠獲得母親的認可與表揚。
拉康道明了對憂郁的修補所存在的社會維度。實際上,拉康在佛洛伊德的基礎上將人的心理結構劃分為一種三元的拓撲結構:想象界、象征界、實在界。在嬰兒時期,我們幾乎只與母親產生單向關系,我們認為自己是目前全部的欲望物件,母親也是自己全部的欲望物件。這實際是一種想象的關系,我們的精神中也存在著這種想象的部份。我們的心理更多依存於象征界中,即集體所構建出的一套由象征符號所構成的象征秩序,在這裏每人每物都擁有自己的象征名稱,社會的正常秩序也依賴於此運轉。然而,總有一些東西,比如死亡、災禍、無常,是象征秩序無法解釋的「不可能之物」,這些黑洞也就構成了實在界。我們努力用象征秩序掩蓋實在界的存在,而最重要的便是對實在界來臨之時,為這些不可能之物在象征界中尋找一個位置,使其可以被象征秩序解釋。
處於肛門期的兒童便是如此,當他意識到自己失去母親的愛時,這次來自實在界的攻擊使其不得不做出反應,他需要重新為失去的、愛自己的母親尋找一個象征界位置,並與其重新建立聯系,以便解釋母親依舊愛自己。就在肛門活動中,兒童透過使自己融入象征秩序中獲得了母親的認可,這也就使得「愛自己的母親」重新在象征界中占據了一個位置,而內心的憂郁也就被修復了。

而這也就是哀悼的基本機制:我們可以理解,哀悼並非只是佛洛伊德意義上個人的思緒,它更是一種社會儀式,我們用哀悼的方式應對一個人的逝去或物的消失。而這樣的活動歸根結底是為「逝者死亡」這一實在界的入侵進行象征式的遮掩,我們需要假裝逝者「與我們同在」。透過一系列儀式性活動,葬禮、墓碑、紀念,逝者在多人參與及承認下,以另一個位置被固定下來,因此實際造成了未曾離去的假象。隨著我們慢慢接受這個新的位置是代表「逝去」的,我們對他們不再報以愛,哀悼也就逐漸結束。在此,我們不厭其煩提及拉康對佛洛伊德一則案例的重新解讀:一個父親為自己夭折孩子守靈,夜晚做夢時,孩子拉著父親的手說「父親你把我燒著了」,父親驚醒發現蠟燭倒下,燃燒了孩子衣服一角。對於佛洛伊德來說,夢折射出父親對孩子的擔憂和復活的願望,但對於拉康來說,這顯示出父親心中被象征界所掩蓋的孩子死亡的真正事實。孩子的葬禮其實是對假裝孩子未曾離去的認可,為孩子構建出新的象征界位置。然而,夢卻赤裸裸揭開了這層假象,讓父親的自我譴責,也即憂郁之思徹底暴露出來——你怎麽把我燒著了呢?
因此,當我們認定失去之人或物尚且「存在」時,我們就不會產生憂郁,也就阻止了抑郁的產生。我們可以總結說,要想避免抑郁,就要讓哀悼順利發生和進行。反之,抑郁的誕生,其實就是哀悼過程無法正常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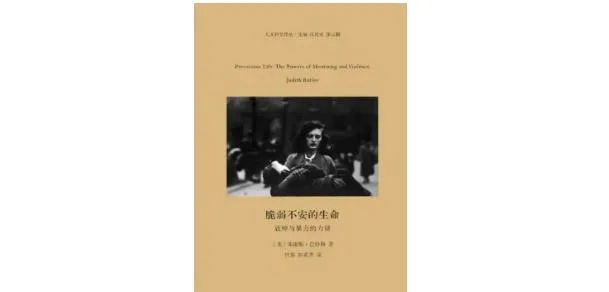
抑郁是如何誕生的
利德總結了四個哀悼工作順利開展的要素。其一是需要引入一個框架來標記象征性的、人為的空間,譬如去殯儀館參加葬禮。其二,我們需要一種對喪失之人或物已經離去的集體承認,這是讓我們在象征界中為其構建新位置的前提。其三,為失去之人或物構建新的位置,這讓其從我們內心中原有位置剝離,同時進入到一個「仍與我們同在」的新位置,以便我們不會產生憂郁。其四,我們逐漸放棄我們曾經為他們而有的形象,這昭示著悼念過程的結束。當然,我們不應忘記在第一部份提出的,整個過程開展的前提是我們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麽。但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不會完全順利,任何一個環節的受阻,都會導致憂郁的產生,而抑郁也就隨之而來。
不過歸根結底,憂郁或抑郁顯示出與社會象征秩序的脫離,如同巴特勒所言,憂郁者將自身轉入純粹的精神世界,從而拋棄了社會世界。而這就讓我們對抑郁癥患者更為難以了解。利德提出,至少有兩點原因阻礙我們窺察抑郁癥患者。其一是抑郁癥患者的精神分裂。由於他們並不承認逝者的離去,他們有可能棲居在一個「與逝者共存」的精神世界中,而現實世界則會變得愈加模糊與虛幻。抑郁癥患者搞不清楚這兩個世界,隨之帶來的則是更大的痛苦。而另一方面,由於與現實世界脫節,這使得他們無法以符合象征秩序規範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處境,而這往往也就是抑郁癥患者諸多行為呈現出不符合常理的「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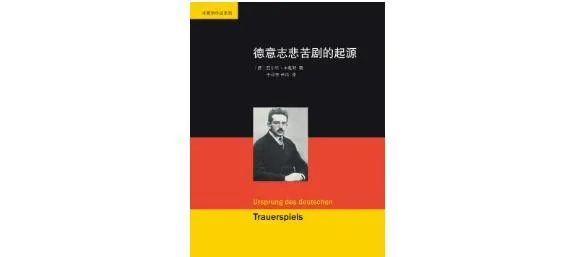
而這裏就彰顯出文學藝術在抑郁癥治療中的作用——文學藝術對資訊詩性的表達,往往能夠將不可能之物言說出來。「憂郁的主題需要用詩意來表達」,利德如此總結。我們能夠聯想到不少孤獨而頗具憂郁氣質的天才在文學藝術長河中的驚人創造,甚至華瑟·本雅明也在其著名的【德意誌悲苦劇的起源】中考察了憂郁氣質與德國民族及德國悲苦劇之間的關系,並試圖重新挖掘它們在思想史中的意義。對於佛洛伊德來說,在【文明及其不滿】一文中,他將藝術作為人類文明幾乎的唯一解藥,因為文明本身起源於對無意識的壓制,而這不但導致了抑郁癥等心靈疾癥的產生,也導致了諸多心理本身的負面效應。而我們訴諸的最終方式並非藥物治療,而正是藝術這一詩意的表達方式。
到此為止,我們完成對本書線索的梳理,也完成了對抑郁癥成因的解讀。不過,仍然需要提醒的是,我們只是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探索抑郁癥,給予其新的視角與新的闡發,並對不斷向著生理疾病方向發展抑郁癥治療策略進行撥亂。我們遠遠沒有掌握抑郁癥所有的真理性內容,或者說,我們對此仍舊知之甚少。當我們在閱讀這篇文章時,我們本身已經站在一種俯視的視角,似乎洋洋得意破解抑郁癥的奧秘。但實際這並沒有發生。相反,我們要不斷提醒自己,抑郁癥患者還在遭遇著巨大的痛苦,而這些痛苦比我們在文中展示的、比我們能預料到的,還要巨大得多。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選自【我們為什麽會抑郁:哀悼、憂郁與精神分析】。撰文:王楷文、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評周刊授權不得轉載。









